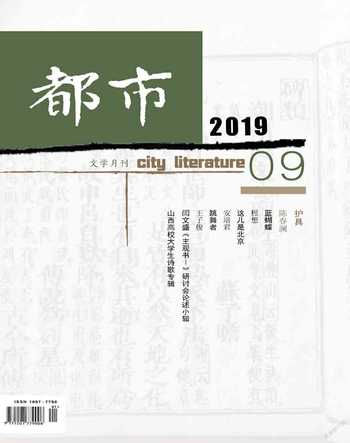散文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2019-09-10鲁顺民
鲁顺民
我跟文盛的交往年头特别长,他首批的散文很多都发表在我们刊物上。今天的主题是“散文的可能性”,实际上应该改为“闫文盛散文———散文的不可能性”,他的散文,无论是作为编辑刚开始看,还是后来出书后作为读者看,总给人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提心吊胆什么呢?他离你惯常的阅读,或者距离惯常的散文样式很远,他笔下的事物、人物、情绪,几乎都不可能构成惯常散文的元素,即便你读完,仍然心有余悸———刚才读的是不是散文,是不是文章?这种怀疑一直存在。哪怕是今天洋洋洒洒八十万字也好,十多万字也好的《主观书》出笼。
这种阅读经验距离你的阅读期待实际上也很远,说白了,看闫文盛的散文,总有一种“别扭”的感觉。好好写着人,突然这个人消失了,满篇说的是他跟这个人交往时候自己的心态和自己的情绪、情感,是真的在写人吗?好好写着一件事,突然这件事情神龙见首不见尾,无始无终,然后作家的情绪占了上风;好好写一种情绪,以为是有什么感悟,其实也不是,他在那里追问。追问又质问,追问并不是寻求某种故事意义上的真相或者结果,而是寻求哲学意义上的答案或者质询。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闫文盛的散文。
首先,他的散文具有高度的私人化倾向,与其说,他通过散文表达,是想与这个世界进行对话,给眼前事物以全新的命名,倒不如说,他一直在跟自己对话,独白,自我剖白。这个大家都能够体会到,正因为如此,他的散文显得比较散漫,因为在写下一篇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打算让哪一个人看。
其次,纵观闫文盛写作,他一直在破坏,在冒犯,在违章。在前六七年,哪一期缺稿子,就想起文盛扑闪扑闪美丽的大眼睛,就让他赶紧拿来稿子,很密集地发过一两年。刚开始是小说,后来就写散文了。但他的小说是“别扭”的,是异于标准小说的,然后又是散文,仍然是别扭的,异于常规散文的。但他做得很好,为什么呢?他最早是写诗的,写诗的人特别可怕,屁大點的事,他能写得那么复杂,无论是山也好,水也好,哪怕是一瞬间的心情也好,可以搅动得空间很大,写诗已经很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诗人放下写诗的笔去写文章。那几年他写小说写得风生水起,眼看要达到我期待的目标,他突然不写,然后大量写散文,写他的《主观书》。诗人写散文,写小说者不乏其例,这样的人混迹于小说家散文家行列,是下决心拿人饭碗。
《主观书》刚开始,我也曾经说过,我说你不要这样来写,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可是《主观书》一旦集结成集之后,拿到手里,虽然好多发表过,但还是吃了一惊,就像造句一样,一旦排比,就出现一种气势,呈现出一种面目。读他的《主观书》,我想起了本雅明,想起了佩索阿,更想起了卡夫卡,他老是跟我谈论起这些外国作家。他在谈论这些外国作家的时候,我刚开始很担心,我说你不懂外语,最好不要说这些话,而且我劝他学点外语,读点原著。但是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突然考上研究生了。
可能大家不知道,文盛是一个学习能力特别强的人,在初中的时候学习就很好,初中一毕业,当年就考上了中专,是山西省水利学校,他是学水工的。一个搞理工科的人很不服气,就搞了文学,而且还是写作的研究生,就像跨过好几个朝代,突然迈入现代一样,常常让你吃惊。他的这种人生状态也几乎是一种不可能。不可能,是因为不可复制。
还有,六七年中间,我频繁到各地去,在各个省见不同群体的文学朋友,他们老跟我讲文盛的散文,我刚开始没有觉得怎么样,后来说的人越来越多,有女性,当然更多的是男性,有实力派作家,也有新锐文学新秀,我已经觉得文盛的散文写得好,没想到他这样好,影响如此之大。大家可以看看《主观书》后面那些评论家给他的评论,那些评论都很客观,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评论。
但作为编辑,常常约文盛的稿子,首先还是喜欢他的表达,就是他的语言。精到,老到,结实,准确,很少有人谈起过他的语言。翻阅《主观书》,不管你对文章怎么看,你不得不佩服他对叙述、结构的把控能力,这种把控能力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作家具备的基本功。可惜的是,许多作家并不具备这个基本功,甚至鄙弃这种基本功训练。我常常把有无此种训练与能力,视作一个作家有无创造力的一种气质。文盛是有这个气质的。
细想一想,一个写作者,民间叫写家。写家的本事,就是靠叙述来创造现实世界不可能性之外的一种可能世界,从而赢得“作家”的称号。文盛显然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