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 火
2019-09-10罗俊士
罗俊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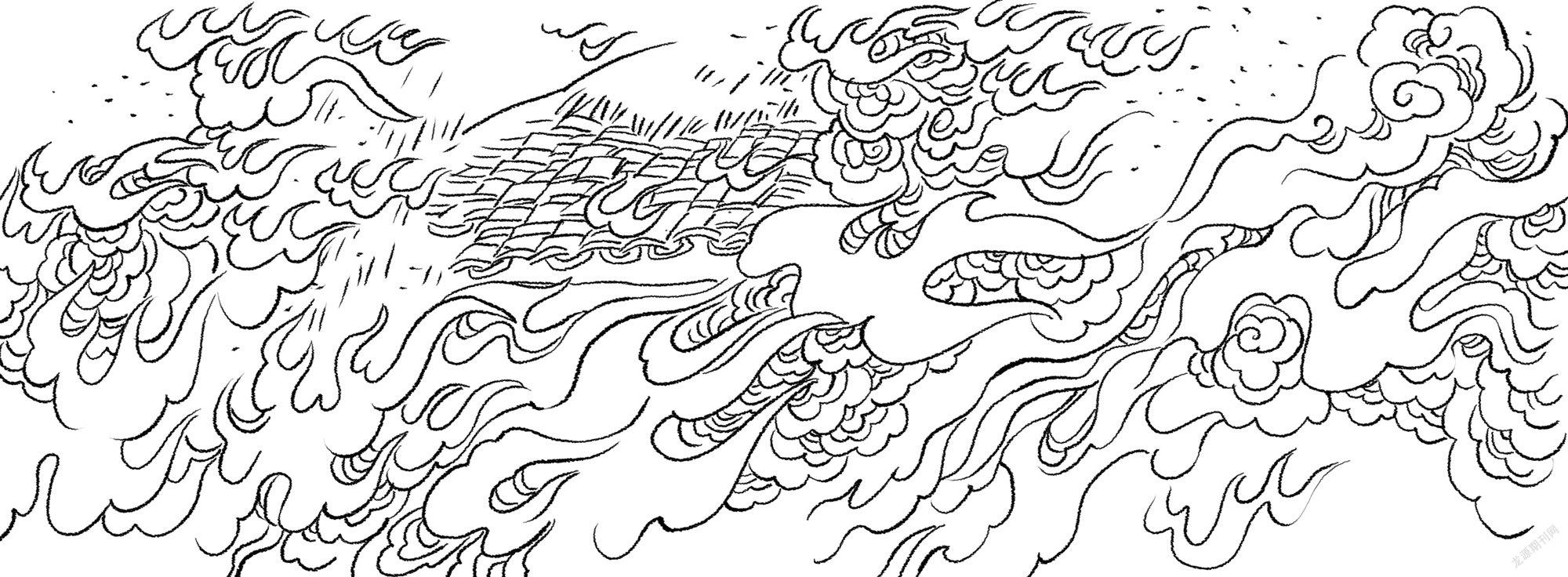
1972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家东院堂屋那副对扇榆木屋门吱嘎一声响,随之闯进一股浓浓的柴油味,已经睡熟的弟弟被呛到,打了个喷嚏,翻翻身,皱皱眉继续睡,打着小呼噜。
我和爷爷住在西院两小间平房里,屋当地有个生铁火盆,几根木棍已经烧透,弥漫着淡淡的烟雾,仍不失暖意。如果不是我爹在东院可着喉咙吼叫,我肯定会一觉睡到大天亮。
我爹上工的地方是公社农机站设在我村的分站,有人戏称他二牌站长,其实只是个看场子的。堤北有块鸡刨地,种不成庄稼,分站就设在那里,距我家百来米。站长量才使用,因了我爹的正直。分站只有两辆专门犁地的东方红,我爹白天黑夜守场子,守的也就是几桶柴油。这晚,四位机手和炊事员老张头儿都请假回家了,我爹见缝插针,用管钳拧开桶盖,倒出大半红瓦盆柴油,端回家时,我娘正在摸黑纳鞋垫。
“把灯点上,这不,有灯油了!”我爹边说话,边去灶台摸那盒泊头火柴。
我爹不知道柴油里面有着汽油的成分,他见过老张头儿用柴油添灯。相比起煤油,柴油冒烟多些,灯捻得勤挑勤拨,但挡不住照亮,总比黑灯瞎火强吧。我爹嚓一下划着火柴,就听,轰!红瓦盆里腾起的烈焰直冲屋顶。红瓦盆距离土炕只有半步,我爹顾不得细想,出手捉住红瓦盆就往屋外扔,速度那才叫快,绝对不超过三秒。
院子里顿时成了火海。
冲门屋地上有火苗伸长着饿狼似的舌头四处乱舔,我娘疯子般跳下炕,抓过一把笤帚拼命扫打。
我爹急红了眼,一瞬间变身为跳远天才,嗖!跃过火海,蹿至南围墙根。
“快来人呀!老红脸家失火啦!老麦的家失火啦!罗书汀家失火啦!快来人呀!……”我爹一遍一遍重复,把嗓子都喊哑了。
我和爷爷听到喊声,麻利地起床、开门,往东院冲,却冲不进去,蒲草盖顶的过道棚已被烧塌,火焰熊熊,南边的柴火垛腾起的烈焰更甚,有一丈多高。这要怪我娘的莽撞,是她把院子里的火泼大了,过道棚和柴火垛才很快被引燃的。她把屋地上的火苗扫灭后,转而一瓢一瓢从门旮旯水缸内舀水往院里泼,还骂我弟弟:“死孩子!拿碗舀呀!”隔着冲天烈焰,我在院外也能清楚地听到我娘近于绝望的号叫。
爷爷到底是经历过战争的人,见多识广,忙喊:“不要!快别往院里泼水!油火,越泼越大!”随之命令我:“回西院拿铁锨,挖土压火!”
村邻拥来不少,麻雀群似的土块噗噗噗往院里以及着火的柴草垛上飞,闪着银色光亮的清水哗哗哗直往烛天的火焰头上浇,铁锨和水桶的碰撞声与众人的嘈杂声混合,异常热闹。——火势太猛,无济于事。
这场火真大,可以用“蔚为壮观”一词形容。火焰旋风般拗着勁儿往上蹿,夜空红通通的,仿佛谁用朱笔在墨黑的底衬上涂抹了一层滚烫的血。突然下起了雪,雪花飒飒飘落,如美丽圣洁的白蝴蝶;柴灰翩翩飞舞,若数不清的黑蝴蝶,竞相辉映,搞得人眼花缭乱。待到人群拥进院子时,那个高达屋脊的柴火垛仅剩齐腰高一堆灰烬。
为积攒那些柴火,我和弟弟逮空就去堤脚捡落枝,用箩头回来,剁成段扔垛上,还有从落潮的南河滩里捡回的烂木板、烂椽子等,还有从堤北干涸数百年的老河滩里割回的茅草、蒲草、连根草、铁线草、抓地秧草等,还有在大堤两旁用竹筢搂回的无数筐柳叶以及从别处搂到的杨叶、槐叶、桃叶、杏叶、梨叶、椿叶、枣叶等(这里有必要补充一句,好多树叶落下时仍然绿着,因为霜降的缘故),还有大人从自留地弄回或从生产队大方地里捡回的棉花棵、辣椒秧、花生秧、红薯秧、高粱秸秆以及麦秸,麦秸好引火。
奇怪的是,雪只下了十几分钟便戛然而止,仿佛被大火逼退的。
“咋回事?”有人问。
“到底咋回事?”人们七嘴八舌。
我爹蔫头耷脑,圪蹴在南墙根,一言不发。
我心里空荡得直想跳高,因为不明就里,也随众人嚷嚷起来:“爹,您是不是得罪人啦?”
“少说撑耳眼儿话,能当哑巴卖了你?”我爹抽身进屋,咣当!那副对扇榆木屋门被狠劲儿关上了。
那场火烧掉的不只是一垛柴火,还烧掉了我爹引以为自豪的英名——其实并非正直,而是“斜硬”。次日上午,我爹没去分站,也没人来叫他。下午,他两手燎泡,顶着一头焦灼的卷发去应卯,被老张头儿奚落了几句,俩人差点儿干架。
第三天清晨,刮起了带呼哨的北风,气温骤降,屋内水缸里结了一指厚的冰,哈气从嘴里鼻孔里钻出来,好像人人本领遽增,学会了喷云吐雾。
吃罢早饭,我在村外转来转去,哪儿都光秃秃的。地里的秸秆入冬前就全部拉走铡碎集中到生产队的大粪堆里了;大堤两旁枝枝杈杈悬挂着的叶子早掉光了,被竹筢搂拾得干干净净;堤南河滩里和堤北老河滩里沙丘成群,像无数秃头和尚在念经。
中午,弟弟从张村社中放学回来,缩成一团,带几分孩子气地说:“上学路上不咋冷,光顾快走了,还出汗哪。到学校,教室里生有煤火,捅几下,小火焰呼呼跳跃,像春天野地里鲜艳的花朵。一进家就冷,像掉进了冰窖。”
我爹瞪他一眼:“像……像你娘个蒜臼,上鸡巴几天学,学会拽了!”
弟弟嘟了嘴,爬到炕上扯条棉被裹紧自个儿,不再吱声。
字典里对“失火”二字是这样解释的:因不慎酿成的火灾。生活中,有多少灾祸不是不慎酿成的呢?
爷爷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说:“也许吧。”
[责任编辑 王彦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