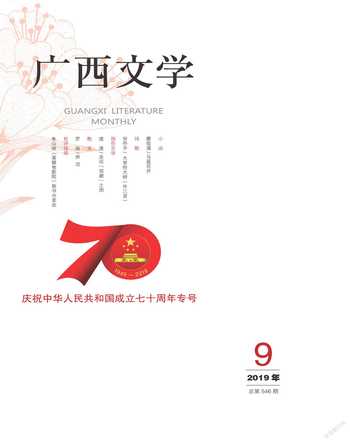远和近的苍茫
2019-09-10罗晓玲
罗晓玲 瑶族,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创作培训班学员。作品发表于《民族文学》 《诗刊》 《散文选刊》 《飞天》 《广西文学》 《四川文学》等,出版个人诗集《月光照在黛瓦上》。
一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每次从县城出发去往扶贫小村的路上,我都会想马丁·路德·金这句话。就像夜行人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一样,在扶贫的这条路上,我特别喜欢用这位牧师的话来给自己打气。
每次驱车摇晃在坑坑洼洼的村路上时,整个人的肌肉都是紧绷的,然而当底盘还是不可避免地被重刮时,身上的肉就像被剜走了一块似的无比心疼。“再这么下去,”一起扶贫的伙伴说,“别人没脱贫,自己都贫了。”每次我们埋头填那些表格时,就像扑在一堆乱草丛里寻找丢失的一根同等大小的线,把自己弄得眼花缭乱。现在,我在一个偏远的贫困户逼仄昏暗的房子里,使劲把扶贫手册上原来的数据擦掉,再填上新的数据,水田、旱地、人口、民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雨露”计划、工资收入……数据是不稳定的,为了保持手册的整洁,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学会了用涂改笔和修改液。我们可以不懂得自己家属的具体收入,但我们必须了解自己贫困户的收入,甚至我们了解贫困户要胜于了解我们自己。
不记得是第几次填写和修改数据了。许多时候,简单的数据并不足以应付千变万化的人间万象,比如谁家卖谷子有收入了,得加上产业收入,谁家媳妇儿又生了个娃,扶贫手册上得改,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得考虑“雨露”计划了。县级手机扶贫系统得改,区级扶贫系统得改,官方国扶系统里跟着改,一个数据的修改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繁杂的感觉是令人烦躁和抓狂的,因为不停地做着,又总做不完,还不觉得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一不懂“春天粪堆密,秋后粮铺地”的农事,更不懂除草杀虫、种瓜点豆、抹芽收谷。面对家徒四壁的贫困,面对流泪无助的眼神,我们娇嫩的五指仿佛就只会填些简单的数据。我经常觉得这样的工作很迷茫,因为它的“纸上谈兵”,因为它的不确定性,让过程变得漫长而绵弱无力。
仿佛一个人独自穿越在茫茫大漠之中,黄沙漫漫,风尘卷卷,没有尽头。
沙漠?要不是因扶贫工作,我的脚步早已行走在千里之外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在敦煌鸣沙山,站在少女胴体般极具诱惑的弧线下,看着一座座黄灿灿的沙丘在天空下绵延起伏。它们释放着浩瀚、苍凉、雄浑的气息,让我目瞪口呆甚至忘记呼吸。我仿佛看到了两千年前的张骞领着驼队缓缓行进在茫茫的丝路之上,又仿佛看到了玄奘法师手持禅杖,背负行囊艰难地徒步在西天取经的漫漫沙尘中。这是迥异于家乡小桥流水的别样景致,这是我在南方小镇一直心驰神往的诗和远方。
但现在,我们不得不为了这场战役困囿在穷乡僻壤里,放弃各种公休假日,加班加点,在别人的贫困里修炼自己的意志。在这場与贫困相抗衡的事业面前,连“诗和远方”这样的词说出来,都带着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色彩。可是看着朋友圈晒着旖旎的湖光山色,谈论着度假中的各种奇闻轶事,甚至有人晒出了我所熟悉的敦煌美景时,那些使劲按压下去的记忆仿佛死去的野草在春风的撩拨下又一一复活。
二
月牙泉在鸣沙山群峰环抱下,如一弯新月镶嵌在沙漠里。这是漫漫大漠中独有的一处山水奇观,是茫茫沙海里难得的一方生命绿洲。我沉醉于这处被称为沙漠奇迹的绝世风景里。
鸣沙山有一座用于滑行的主沙丘,这座沙丘与月牙泉遥相对望,可以俯瞰整个月牙泉全景。这座沙丘应该有五六十米高。在沙山倾斜的脊背上,两根钢硬笔直的铁丝线被平行地拉上山顶。在两根丝线的中间,横绑上一根根拳头大的圆木。这样,游客们就可以踩着圆木,不必那么吃力地爬到几十米的高处,看对面那片罕见的沙漠绿洲,又可以从山上坐着滑板急驰而下,享受沙上逐浪带来的刺激感觉。
沙山唯一的索道上,向上攀爬的游客已经被索道串成了一条线。我们小心翼翼地踩着圆木一级一级地往上走。圆木不到一人肩宽,我们轻装上阵,仍不可避免地会踩偏到沙粒中去,整个身体随即跟着塌陷,再拔出来时,身上的力气像被沙漠无形地吸进了不少,人又虚弱了些。再往上走几十步,人就快虚脱了。
身边不远处,有游客从几十米高的沙丘上飞速滑下,惊叫声此起彼伏。
才上到沙山三分之一,我就已经气喘吁吁,喉咙像要喷火。从包里取出水灌了几口,那些水一到身体里,就立即被蒸发了。周身被炽热的光包裹着,剧烈的运动,让心脏加速着跳动,整个人有些透不过气来。很累。我甚至想从索道原路退回。可是一回头,后面跟着的旅客已经站满了长长的索道。原路返回是不可能了,只能往前走。
前面的行人突然停了下来,整支队伍也跟着停了下来。我听见周围的人粗重的喘气声,他们散发的热气,正加升着周身的温度,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
“咦,怎么不走了?”后面有旅客嚷嚷,我想他们与我一样,目的已经不止于只想征服这座沙山,而是想快点结束这场艰难的攀爬。
声音是从后面传来的,一个接一个,每个人的眼睛越过前面的人,往队伍的更前面找原因。我也往前看去,发现就在与我相隔的几个人前面,一位背着十来块“滑板”的搬运工停在原地,气喘吁吁。
滑板是用实木做的,每块滑板做成舟状,中间凹空,两端微翘,这样的结构,正好能容纳一个人坐在里面,就像乘坐一叶扁舟,从沙丘上急速地滑下。每块滑板重量自然不轻,我数了数,他的背上一共八块,左右手还各拿着一块。一根胶带把他的身体和滑板捆在了一起。他的背已被压弯成九十度,远看很像乌龟驮着一具重重的壳。我看不到他的脸,只看到蓝色上衣露出滑板的部分干枯而凌乱。他前面的游客继续往上走着,与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他身后的游客,被他的停滞堵在后面,像一条淤塞的河流。
三
九十度,奶奶的脊背也已经弯成了九十度,像一把老旧的镰刀,把八十多年的光阴全数收割在了她银白色的鬓角上。此时她轻轻的一声咳嗽,把我唤回了那间幽暗的屋子。
“天燃汽”要改为“天燃气”,驻村干部前两天对我说。他们经常进村入户检查我们的手册有没有填对,扶贫政策有没有上墙。一次次强调,再一次次检查,不厌其烦。
有这个必要吗?我常常想,就为了改这个字和增加本月的工资收入,我们又耗了大半天的时间在村里。我找修改液,无奈修改液用完了。我懊恼地用橡皮把“汽”字擦去,结果用力过猛,“汽”字被我擦出了一个洞,我只好找了一张空白纸,从边缘撕下破洞大小,涂上胶水,将那一小块白纸从后面小心地粘上去,然后等着那个被修补的纸洞干爽过来。
三伏天,天气闷热,旧式的房子不通风,只有一台落地扇在转动。扇叶在昏暗的光线里旋出白光,我的扶贫手册被吹得“嘩哗”直响。
整个房子里只有奶奶陪着我,她稀疏的白发被风扇扇出的风吹起又落下。她坐在我身边的木凳上,一边看着我写,一边偶尔跟我说几句话。她等着我把册子写好,好在手册上按下手印。她从不问那些本子上写着什么,她相信我。但她不是我的帮扶对象,她的三儿子跟四儿子才是。奶奶跟大儿子过,大儿子、三儿子、四儿子都是贫困户,只有二儿子不是。几个儿子的扶贫手册都放在她住的大儿子家,三儿子跟四儿子都在外地打工,所以我下村只能找她。我也是她家为数不多的造访者。来的次数多了,从客气到稔熟,最后,她就把我当亲人了。而一段时间不来,我心里也会惦记着她,担心她孤身一人,日子过得好不好。
“妹,我去做饭,你在这儿吃饭。”她的话还没有落地,人已经起身到厨房去了。
我说:“奶奶,不用麻烦了,我一会儿就走,同事们还在等着我一起回县城呢。”
“吃了饭再走,”奶奶的声音从厨房里飘出来。她一岁多的时候,被人从大瑶山里抱了出来,送给了现在的这家主人。她在这个家渐渐出落成一个俊俏的女子,为新家招郎上门,生儿育女,在几亩地上耕种了一生。她几乎没出过县城,不识字,对于扶贫这个事,完全听我的,但在吃饭这件事上无比固执,无论是不是吃饭时间,无论我有没有吃过饭,她都要去给我做饭,仿佛除了吃饭,她再也找不到什么方式回馈我的劳动,并且意图与我多相处一会儿。我拦不住她,只好由着她了。
厨房里已经传出了做饭的声音。菜刀剁在砧板上,这敲击声那么熟悉,又让我的思绪回到了搬运工身上那些相互碰撞的滑板上。
四
一分钟、两分钟,时间仿佛凝固了,那位搬运工还没有歇过气。后面越来越多的游客不明就里地抱怨起来。有些游客宁可离开索道踩入沙土一步一步地向上走,也不愿意待在原地被太阳炙烤。那位搬运工终究是听到了一些抱怨的,他提了提气,开始艰难地挪动脚步。
除了那堆滑板,他的身上别无他物。没有水,也没有遮阳的帽子,只有一副橙红色的防沙脚套醒目地套在双脚上。他是无法挺直身子的,一旦抬起身子,木板的重量会将他的身子往后带,整个人都会仰翻过去。他只能弓着腰将左右手上的板子立起来,支撑着身体保持平衡,好喘口气。等缓过气来,才又开始一步一步地往沙山顶上艰难地攀爬。上到沙山近三分之二的时候,沉重的负荷逼迫他又歇息了一次。我看见他每迈开一步,脚都在颤抖——这是体力透支后的肢体正常反应。这一次歇息的时间更长,喘息更重。
又过了漫长的十多分钟,我们跟在搬运工的后面,终于攀上了山顶。
终于可以在沙山顶上坐下,欣赏美丽的月牙泉,还有对面沙丘的景致。远处往沙丘上攀爬的人流,在巨浪般高耸的沙丘上,像飙浪的人飘移在浪尖。
我拿出相机开始拍照,这绝美的沙漠风光我要把它尽收眼底。一个身影闯进了我的镜头。是他,蓝色的衣服,下端干枯而凌乱。我第一次看清了他:黑褐色的瘦脸,鹰钩鼻,典型的维吾尔族人特征。他已将身上的滑板卸下交给老板,踩着软软的沙土,挺直腰板一步一步地走下山去。
他搬运上去的滑板,很快转到了游客的身上。那些游客交了滑翔费,坐在滑板里,只一会儿工夫,就从他身边迅疾地滑过去,发出一阵阵刺激又满足的尖叫。而他使尽全力搬上去的滑板,已经先于他回到原来的地方,等着他再次叠起运往山顶,再次重复艰辛的攀爬。这情景突然让我想到了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每天努力地推着一块大石上山,到第二天,石头又回到原处,他又要重推。上帝将此作为无尽的折磨对他施以惩罚。但西西弗斯内心并没有为所受的惩罚所累,反而从自己推动大石的身影里,看到了自己健美的身姿,他陶醉于其中。最后,因困境中对美的领悟超过了困顿本身,西西弗斯被上帝赦免了苦刑。
我不知道这些搬运工们,是不是也有着西西弗斯的乐观。也许他们正为生存而忍受劳苦,也许正为从中拿到了劳动报酬而欣慰。
下山的时候,我看见那位搬运工的同伴们,每隔一段距离,也像蜗牛一样,背着重重的“壳”,往山顶爬去。
五
厨房里的菜香飘了出来,把我的思绪又带回了这间屋子。以往如果时间允许,手册填完,我会去帮奶奶做菜,但现在,我还得打电话先把他们的工资弄清楚填好了再说。
我曾从同村人的口中得知,奶奶嫁的是一个十足的恶棍,在世时坑蒙拐骗无恶不作,但地方却拿他没有办法,而奶奶的命运,可想而知,她经常被丈夫打得鼻青脸肿,甚至在田地里劳作都会被暴怒的丈夫打昏过去。这样的人生,她是如何走过了六十年?
幸运的是那位恶棍丈夫几年前去世了,奶奶终于有了平静的生活。按照政策,我知道奶奶有高龄补贴,再加上几个儿子不时寄些钱回来给她,她的日子过得还不算太差。
要询问收入了。拨通奶奶四儿子的电话,电话响了许久没人接听。再次拨过去,终于接通了,但声音是四嫂的。
“四嫂,四哥在上班呀?”我问。四哥跟四嫂都在广东打工,但四嫂身体差,只是陪着四哥在工地上做一些简单的工作,给他做做饭,缝缝洗洗,基本没什么收入。四哥则是帮人做泥水工,这种不需要任何文凭,只需要力气的苦力工,村里好多男人在做,以至于城里的人每每教训自己的孩子,都会拿这种工作说事儿:“现在不努力,以后你们就出去当泥水工!”
“妹,你四哥在市里住院十多天了,大城市医院花费太高,我们回到了市医院。”四嫂有点语无伦次,声音有点沙哑。
“啊,怎么不早说,严重吗?”一种不祥之兆涌了上来。我听到奶奶切菜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我赶紧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语气。很明显,为了不让奶奶知道,又为了更好地医治,四嫂她们选择了回市里。
“医生说是喉癌,现在他说不出话。”我听见四嫂在电话那边哽咽起来。
我跟奶奶说屋里信号不好,拿着电话走出了那间幽暗的屋子。
“確定了吗?是……早期还是中期?”我问。我觉得自己的手在颤抖,我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事会戏剧般地发生在我身上。之前的日子虽不富裕,可毕竟是风平浪静无灾无难。
“确诊了,是早期,过两天就动手术取瘤子。”四嫂说。我能想象她此刻正用无法选择的坚强支撑着无比虚弱的身体。
“四嫂,没事,我知道有人得这个病但发现得早,化疗得好,还能存活好多年的。好好治疗,会有希望的。”我用故作轻松的语气安慰着她。
奶奶的屋前是一条长长的巷子,另一边通向村大道,我正往奶奶房子的相反方向走,我害怕那些不祥的词语被她听见。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悲剧再次叠加到她悲苦的命运中来,会不会击垮她的余生。
这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奇迹般地想起扶贫培训时学过的关于大病补助的政策,“四嫂,贫困户住院享受先看病后结账的优惠,你跟医院说一下,先不用交费。”
她说:“但是要把贫困户资料发过来。”显然她已经懂得利用这个政策了。
我松了口气。手册上写着他们的文凭是“半文盲”,但庆幸的是他们还不至于没有一点头脑。我也终于可以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带资料去市里帮他们理顺关系,比如安抚,给他们弄个众筹,等等。想到以前每次做扶贫培训,一直觉得那些什么大病啊低保啊跟我的帮扶对象没有关系,没想到现在却派上用场了——当然,这种用场不用也罢。
“嫂子,我们这边的贫困户能享受百分之九十的大病报销额度,也就是你花了十万块钱医病,自己只用出一万。”我压抑住内心的慌乱,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安抚她。四嫂那边的语气果然镇定了很多。
放下电话,身体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头。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每天填的那个手册是那么重要,那个大病救助政策是那么好,它可以让贫困户享受先治疗后付费的优待,还可以报销解决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如果说绝症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是个灭顶之灾,那么天文数字一样的医疗费,能直接毁灭他们最后一丝对生命的希望。而搬走了医疗费用这座大山,对一个患重病的贫困户来说作用仅次于重生一次。
我转过身,奶奶已经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
她看我的眼睛深而寂寞,那是用八十年的人生悲苦穿凿的生命隧道,所有的悲痛都已经融进那些幽深的隧道里变得无影无踪。
我牵奶奶的手回到屋里。我跟她说四哥的病能治,她没说什么。
她的菜已经做好了,碗筷已经摆上了桌。
“下次来给我打电话,我多做点菜。”奶奶说,声音有点儿颤。我知道她按压着内心的悲痛,只是不想给我太多的担心。看得出她每次都舍不得我走,每次我走的时候,她都将我的手拽得紧紧的,亲自送我走出巷子,好像生怕我不会再回到这座老房子里。那些反复修改的数据,那些总弄不明白的农业问题,一次次地牵引着我出现在这里,成了奶奶孤寂中的陪伴。而奶奶的渴求,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被需要,这种感觉一次次安抚着我在扶贫工作中的烦躁与无奈。现在,那些被我认为不切实际的东西,像一根线,把我牵到了奶奶家里,现在,它又像一盏指路的明灯,正为处于绝望和黑暗中的人送去一束坚定的光芒,让他们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远方沙漠中的搬运工此时也还在费力地攀爬吧,想起他们,我就想起鸣沙山对面的沙丘上,零星生长的一丛丛的沙柳,据说这种植物为了能在缺水的沙漠中生存,把根深深地扎在沙土之中,长达几十米,直到伸向有水源的地方。为了沙土外的那一段青葱,它们的一生都在扎向无尽的黑暗并从中索取生存的意义。
这样的生命是值得礼赞的,这样的民族和人民,有理由走向美好。而这样的美好,需要我们从中搭建一座桥,引领他们走向光明和更幸福的彼岸,我们的工作意义正在于此。
匆匆地扒了几口奶奶做的饭菜,合上扶贫手册,我与奶奶告别走出了村子。
落日的余晖缓缓西沉,远处山脉的轮廓渐次模糊,从山那边吹来的风夹着清新的草叶香气,让人情不自禁地舒了口气。村口,我们的车子卷起细细的尘土,又一次消失在回城的路上,坦然或焦躁,仿佛也在一并消失。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