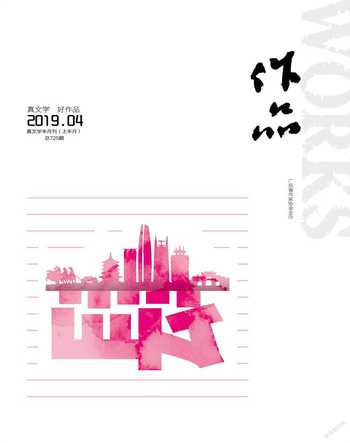广东作家研究之鲍十小集鲍十:在大陆的南端思念北方的家乡
2019-09-10申霞艳
申霞艳
鲍十温厚、内敛,话不多,一点也不像我想象中的东北男人,喝酒的时候并不起哄,偶尔嘿嘿笑笑,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你知道他心思明亮。他有自己的幽默方式,有次参加花城杂志赴零丁洋采风,一条小狗意外地跳上了我们的船,鲍十当即就决定收养。狗慢慢长大了,我们问他到底是什么狗,他答:中华田园犬。挺唬人的,赶紧找度娘,整个编辑部笑坏了。
鲍十是东北乡村的忠实书写者,他对那片土地上的民风民俗、历史掌故,对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以及村子的权力关系等有着切身的感受。文如其人,鲍十的作品素朴、明净,散发着干草收藏的太阳气息。他是一位本色派作家,忠诚于生活,忠诚于内心,乡村生活构筑了他的人生底色。他渴望写出快速变化时代不变的那一面,写出人内心深处执着的情感和信念,他歌颂地老天荒的爱、善和温情。鲍十默默耕耘了很多年,中篇《纪念》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这使他成了著名编剧。后来陆陆续续有好几个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但鲍十坚守着小说的园地,编剧的经验只是小说的补充,在创作中他有意回避影视的光环,从不骄傲。他曾经说:一个作家不仅要看他写了什么,还要看他没有写什么,写与不写之间便是一个作家的写作立场。这句话深得我心,“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当今尤为难得。
鲍十的人生经历了从最北的哈尔滨到南方广州的重大迁移,眼界和思想认识的不断变化使他的创作不断走向成熟、老到。他书写乡村爱情的纯真,刻画乡村人的质朴、人的情感世界的波澜壮阔,他也讲述人生的无常、历史的残酷、现实的艰难。书写乡村,漫长的城市生活同样是无法回避的,关键是作家对待城市的态度,是正面强攻还是旁敲侧击?是欢欣鼓舞还是喜忧参半?鲍十将城市虚化处理,作为一种远景来书写,一种与乡村相对应的存在。生活温馨美好的面和历史斑驳幽暗面夹杂交错,仿佛以多色彩编织的立体锦缎。他想让作品给人以温暖,却从不用廉价的虚假想象来麻醉读者。
改革开放四十年,城乡差距十分显著,城市被视为文明、先进、科技、未来的代名词,而提起农村,仿佛有一种难为情的情绪,一方面,乡村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和精神联系,另一方面,愚昧、落后、无知、盲目等贬义词似乎总是和农村有着“亲缘”关系。农村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没有获得足够的机遇和资源,但在现当代文学史中却是被书写得最充分和最为成功的,漫长的农业文明为作家积淀了丰富的书写资源,二十世纪的文学遗产最强劲的部分恰恰是乡土文学,那些千百年来被土地捆绑的农民、那些无法言说自身的劳动者得以发声,沉默的农民站到了舞台中央。鲍十就是沿着鲁迅精神的延长线创作的,主要写记忆中沉默的农民以及身边的知识分子。
大城市的兴盛让许多农民离乡背井来到城市,在广大的新城市人的精神内部藏着一个沉默的“乡土中国”,有着无数不为人知的远方。鲍十用细致的笔将记忆中的乡土社会描画出来,在那些偏僻而寒冷的屯中,住着各式各样默默无闻的亲人,他们微小如尘,默念着小小的心事:故乡的山、云、水、树,莫不让人动心。那些为逐梦远走他方的知识分子在喧闹的都市中依然心怀故乡。鲍十的乡土书写试图给我们留下一点不那么宏大、不那么亮丽却非常真实的心灵图景。
鲍十的写作立意高,推崇汪曾祺,写东北的乡村着眼于民风、民俗和民情,他将情感融入土地中,这在当代作家对乡土的书写中是别具一格的。正如陈培浩评论鲍十的《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中总结道:“面对‘乡土故乡’的逝去,中国当代作家提供了几种不同的书写路径:其一是莫言式的‘赋魅’;其二是阎连科式的‘批判民族寓言’;其三是格非式的‘精神还乡’(《望春风》);另有一种则是乡土的见证立传。”汪曾祺属于最后这一种,他写高邮的风物、人情、民俗,皆带有一种文化色彩,温情脉脉。鲍十乡土写作中延续了汪曾祺的书写路径,素朴的底色中灵韵闪烁,就像沙漠中突遇“泉眼无声惜细流”。鲍十小说中的乡亲多多少少还保留萧红《呼兰河传》中的麻木,鲍十没有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去批判乡亲,他甚至不让其人物承载太多意义,也不以高蹈的道德去指责农民。鲍十时时反省自己,将自己放进去,仿佛身临其境,故能以开阔的胸怀去同情人世、人心。
鲍十的新作《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是他多年写作的结晶,标题彰显他对写作手艺部分的敬意。毕加索曾说:“我花了一辈子时间学习像儿童一样画画。”我觉得鲍十同样怀了毕加索这种谦卑之心,文风素朴却又有着儿童眼睛的新鲜。每篇故事篇幅短小精练,很少使用形容词,仿佛是一个初学者在一笔一画地摹写,没有丝毫的造作。面对小人物的悲欢、痛苦遭际和悲剧命运,作家没有批判,没有拔高,他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与人物站在一起。他渴望写出他认为的真实,至于联想和评判,他留给读者。
鲍十笔下的爱情纯净而深厚,一如广袤的东北平原。在《我的父亲母亲》中父母的爱情跨越了陈旧的门第观,“父亲”被打成右派,经历了一系列运动,“母亲”却无怨无悔,“父亲”平反后也没有嫌弃“母亲”,他们不离不弃,过着平淡而真实的生活。这与中国文学男主角高中、平反、进城就抛弃糟糠之妻的主调背道而驰。同样动人心弦的还有《痴迷》,他讲述一位乡村医生的爱情悲剧。“神医”华先生终生未娶,一生爱着与他青梅竹马却含恨而死的乡村少女,一直通过幻觉与其相聚、诉说衷肠。这种爱情在今天恰如痴人说梦,但置于静物画般的东北乡村则令人信服。在《痴迷》彰显了鲍十内心对纯粹的深深渴望。
鲍十对乡村农人在经济发展大潮中的命运遭际有着深切的关注与同情。在《好运之年》讲述郑中贵与高春望进城的不同遭遇,展示农民在城市中立足的艰难,身心交困,没有技能的女性更易被城市吞噬。城市化的代价不仅体现在漂泊的打工者身上,还表现在现代城市文明对乡村的侵袭,乡村的古风正在改变。
2003年,鲍十从哈尔滨调入广州任《广州文艺》主编。这是他人生一个重大的转变,从祖国的最北处迁移到最南端,这对他的生活和写作均构成挑战。鲍十努力融入广州的生活,他翻阅文献、走访四方,创作出具有广东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如《冼阿芳的事》《岛叙事》《天空下的岛》等书写海岛生活的小说引起了文坛较大的关注。海岛带有农业文明时代“桃花源”的理想气质,同时融合了岭南文化开放包容的特点。岭南毗邻海洋,与西方世界有漫长的来往,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人类的交往史,形成了海洋文化包容、博大、开放的特质。在《岛叙事》中书写南方小岛百年来的变迁,传统习俗岌岌可危,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非常尖锐。在《天空下的岛》中的磐石岛恰如“桃花源”,又具有与“桃花源”不同的开放性。磐石可以看成鲍十艰难寻找到的“理想国”,任凭海水海风的侵袭而安稳不动。主人公卢韬口最终被海岛接纳,暗示作为外地人的鲍十内心深处对广州、对岭南文化的认同。
南方的岛和北方的屯,共同构筑了鲍十的文学天地。从东北平原到磐石岛,既是鲍十叙事空间的变化,也是他文化认同的变化,通过捕捉变化中的常为重建当代价值共识提供参照。基于这种信念,鲍十更相信田野调查,他为写作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和采访工作。
鲍十身居闹市,心立边缘,从记忆中的东北平原和海岛等边缘处来理解中国、理解现代,发现被潮流、时尚所遮蔽的真实。在这个喧嚣的消费时代留住历史的记忆,他画下城市化进程中的渐行漸远的乡村缩影。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