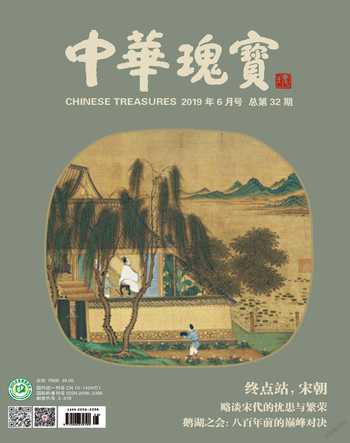包公是怎样“炼成”的
2019-09-10朱万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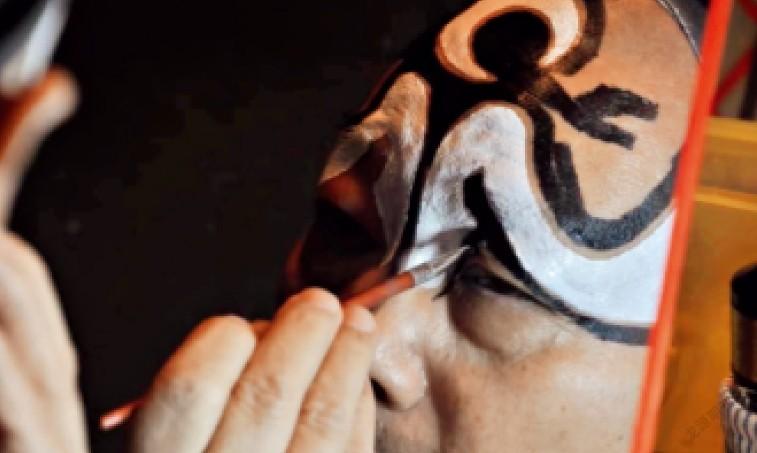

胡适在《三侠五义》序言中写道:“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胡适所言的确是事实,包公这个人物汇集了很多的断案折狱的故事,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但是,作为“箭垛”的包公不是一朝一日完成的,也不是一个朝代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正是通过世代累积的造型,包公才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元:清廉正直 为民做主
元代杂剧中有包公戏21种,现存11种。元代包公题材之所以兴盛,有着社会的和文艺趣味的双重原因。
在元代,一方面,漢人、南人(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地位低下,政治待遇不平等;另一方面,吏治非常腐败,官员大肆搜刮百姓,或者在断理官司时借机盘剥,进而导致冤案叠出。因此,百姓迫切希望有包公这样的清官为他们做主理冤。
同时,元代城市经济活跃繁荣,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元代的大都和苏州、杭州,都是繁华都市,市民需要通俗文艺娱乐自己,于是出现了各种文艺样式汇集的瓦舍勾栏。市民对于通俗文艺的审美趣味不同于文人士大夫,他们对于公案故事很感兴趣,所以当时说唱文学里就有“说公案”一类。新兴的元杂剧中的公案戏也适合他们的审美兴趣。
元代包公形象有自己的特点:清廉正直,为民做主。如《蝴蝶梦》《陈州粜米》等作品中的包公,都同情弱者,站在下层社会老百姓一边,与权豪势要乃至显贵重臣做斗争,并富有斗争经验和断案智慧。
关汉卿的杂剧《鲁斋郎》写了一个包公处斩鲁斋郎的故事。剧中的鲁斋郎是位权豪势要,虽无官职,却“嫌官小不做”,因为有皇帝可依恃,恶行累累,却无人能制服。他先是抢夺了银匠李四的妻子,后又看上郑州六案都孔目(宋时管理簿籍的官吏)张珪貌美的妻子,将她强行占有,并把玩腻的李四妻子赏给了张珪,害得李、张两家妻离子散。包公虽然“官封龙图阁待制,正授开封府尹”,却不能直接将鲁斋郎斩于市曹,只好运用智巧,把“鲁斋郎”的名字减去笔画,写成“鱼齐即”,模糊上奏皇帝,获判“斩”字。将鲁斋郎斩首之后,包公又添上笔画,写成“鲁斋郎”上奏,皇帝也只好无奈地认同了鲁斋郎被斩首的事实。
李潜夫的杂剧《灰栏记》中,包公从人情物理推断出争夺儿子的真假母亲,更具有东方智慧的意义。在《盆儿鬼》《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等作品中,包公已具有“日断阳,夜断阴”的本领。这些作品虽然不乏迷信色彩,但却是生产力不够发达、侦破疑难案件的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的必然想象,包公被神化的过程蕴含着老百姓的理想和期望。
明:富民间智慧 故事大繁荣
明代的包公故事比元代的更为丰富。现存的作品有成化说唱词话中的八种包公故事刊本,短篇小说集《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中篇小说《五鼠闹东京》等。明代的包公戏共10种,现存6种,另有留存一出的《包公坐水牢》。
明代是包公故事大繁荣的阶段,民间艺人编撰了大量新的包公故事,流传至今的“狸猫换太子”“包公铡陈世美”“包公的身世”等故事都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其流传的特点有三:一是走向市井和民间。如果说元代的包公戏出自专业的杂剧作家,尚有文人色彩,那么明代的包公故事绝大部分出自民间艺人和出版商之手,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二是传播形式多样化。在元代,包公故事只是元杂剧的题材;到了明代,戏曲、小说、说唱文学里都有包公题材的作品。三是新编故事大量出现。例如,在元杂剧里,包公的身世故事很简单,到明代就有了极大的丰富。有的故事如“五鼠闹东京”在清代则被吸收到《包公案》(即《三侠五义》)中。
明代包公形象也有了新的特点,身世更加传奇化和神化。如说唱词话《包待制出身源流》中记述,包公出生时相貌非常丑陋,致使父母把他丢弃,幸赖长嫂将他捡回并抚养成人,又请先生教他读书。他参加科举考试后,因为惧怕父母责怪,赶快回家割麦子,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考中。被任命为定远县知县,公差来迎接他上任时,他还在田里割麦子。他不仅能“日断阳,夜断阴”,而且有了“桃木棒”“桃木枷”,专用于断理阴间的案子。
明代包公斗争对手地位更高,斗争精神更坚决。他的对手不再像元杂剧里的权豪势要,而是如曹国舅、温丞相、赵王之类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另一方面,他也因为断出皇太后的冤案,从而有了李太后的扶持。其断案方式更加富有民间色彩的智慧,包公真正成为“东方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如《龙图公案》中的《三娘子》的故事,被现代法学研究者引为犯罪心理学的例证。赵信与周义是生意合伙人,两人相约往京城买布,定下了艄公张潮的船只。次日一早,赵信先到渡口,张潮见他带有银两,遂将他谋害致死,又假装在船中熟睡。周义到船,久候赵信,不见到来,乃命张潮前去喊叫。张潮至赵家门口连叫数声“三娘子”,自然再不见赵信踪影。周义谨慎,到县衙报案,谁知被知县指为与赵信妻子通奸谋害赵信的凶手。幸遇包公巡行至此,从“敲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已无夫”的心理破绽,抓住了差点漏网的真凶张潮,使这桩冤案终得辨明。
清:篇幅宏大 侠义庄重
清代的包公故事仍然在不断丰富,但也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形。这一时期文人作家创作的包公戏有《正昭阳》《双钉案》等,小说则有《三侠五义》《万花楼演义》等,至于京剧和地方戏中的包公戏则更多。
清代流传的包公故事篇幅更加宏大,如《三侠五义》为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本来是道光年间说书艺人石玉昆说《包公案》,当时有文人将他说的内容笔录下来,改名为《龙图耳录》,再后来书名又改为《三侠五义》,成为一部非常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内容上更加丰富庞杂。如《三侠五义》在清官故事中糅入了侠客义士的故事,《万花楼演义》中糅入了狄青的故事,它们都不像明代的包公故事那样单纯。随着地方戏的兴起,包公故事成为各个地方戏剧中的题材,由于地方戏遍及各地,包公故事也随之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
清代包公形象同样呈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包公是清官与侠客义士的结合,这充分体现在《三侠五义》中;还是忠奸斗争中的忠臣,这在《三侠五义》《万花楼演义》中都有描写。包公的性格不再像元、明两代的故事中那样很有“人情味”和民间智慧,而变得非常沉稳庄重。
总之,包公故事经历了由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如胡适所说的“箭垛”和“滚雪球”。包公形象也经历了从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形象内涵各有不同。包公故事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是通俗文艺家的功劳,包公形象的造型是在民间完成的。
朱万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