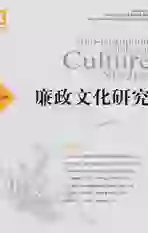公众举报腐败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2019-09-10韩琳余凯徐海燕
韩琳 余凯 徐海燕
摘 要:举报是发现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公众参与腐败治理的主要途径。目前现实中仍存在着部分公众发现贪污腐败现象,但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进行举报的困境。本文利用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2016年在C市开展的“贪污腐败的感知与态度”调查的数据,运用定性访谈数据分析、定量数据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影响公众举报意愿的解释变量分别进行探索性分析和验证性分析。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完善举报制度、加大廉政教育力度、拓宽举报平台和途径等方面来有效提高公众举报腐败的积极性。
关键词:举报腐败;公众意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3-0063-10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腐败往往发生在隐蔽的场所,发现腐败是反腐倡廉工作的关键环节。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举报是发现腐败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据报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2012年立案调查的案件中,线索来源于群众举报的占到41.8%[1],这个比例在各种案件线索的来源中是最高的。另一方面,根据2016年在C市的腐败感知态度调查数据,只有36.9%的市民表示如果知道某人贪污时会举报,2015年的数据显示32%的市民表示会举报。而香港廉政公署2012、2013、2014、2015年民意调查中,分别有79.2%、80.6%、76.7%、78.8%的受访者表示如果知道有人贪污,他们愿意去举报①。从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大陆公众的反腐败举报积极性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调动民众的力量让人们积极参与到反腐败斗争中来,对于我国反腐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愿意举报腐败?人们的举报意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揭示公众参与反腐的因果机制,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在反腐败实践中充分调动人们参与反腐的积极性,完善公众参与反腐的制度和机制。
二、文献综述
对于上述问题,学术界已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不同的学科对公众举报腐败意愿的影响因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1.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潜在的举报腐败人会进行举报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成本较低,而收益(包括公共利益)较大时,人们倾向于举报;当收益不变,而成本增加时,举报意愿会降低。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奖励回报是影响雇员举报组织内部的不当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2-5]刘文革认为,检举腐败是一项个人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成本由個人承担,收益由公众获得。经过建模分析后,他得出结论:举报的收益和成本是不对称的,尤其是当举报的风险和代价较大,而保护和奖励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更严重,由此导致公众的举报腐败意愿较低。[6]Marcia P. Miceli和Janet P. Near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发现组织中因为有高水平的报酬和教育程度而不依赖其雇主的雇员,举报的可能性更大。[7]在另外一篇论文中他们指出,符合下列条件的雇员,举报的可能性更大:具有专业职务,对工作有积极的反应,服务时间较长,最近有较好的业绩,男性,较大工作团体中的成员。[8]
2.从政治学和法学的视角来看,举报腐败的官员是公民的一项权利,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即有相关的规定。李志明认为,公民检举权①的实现,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法律方面的条件,即制定专门的举报法,统一规范各种举报行为;二是外在组织与制度条件,即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制度、言论自由制度以及结社自由制度,鼓励各种公民组织的建立;三是文化条件,即培育健康的公民意识等。[9]洪丹娜则认为,公民检举权的实现机制在于良好的法治秩序,主要包括个体基础、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三方面的内容。[10]杜治洲撰文指出,公众参与反腐倡廉的影响因素有参与能力、参与意愿和参与机会三大类。其中,参与能力跟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关,参与意愿跟自身涉及腐败的程度、公众对腐败的认知度、公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公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公众所受到的保护与激励这五个因素相关,参与机会跟信息公开水平和参与渠道的畅通程度有关。[11]余凯和孙牧欣在对中国、美国、英国、南非和香港地区的反腐败举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发现,受理举报的机构对民众的举报意愿也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受理机构的权威性、受理举报的范围、是否具有独立和完整的调查权以及与此相关的激励措施、法治文化环境等,都会影响到民众的举报意愿。[12]
3.实证研究方面,廉政评价或者对待腐败的态度调查开始在国内流行开来,不少学者利用这些调查展开了相关研究。岳磊利用2015年开展的“河南省居民反腐败社会参与调查”的数据,进行了次序回归分析。他发现,公众对举报制度完备性的感知、对腐败问题的关注度与举报腐败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腐败容忍度与举报行为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行贿经历与举报腐败的可能性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3]倪星和张军利用Logic回归模型,对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持的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一是腐败容忍度和利益相关性均对公众的反腐败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二是公众对政府反腐工作的信心在反腐败工作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反腐满意度和腐败感知水平对公众反腐败意愿的影响比较复杂。三是举报的便利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均对公众的反腐败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四是性别、受教育年限、居住地、户口类型和政治面貌等人口特征对反腐败意愿也有显著影响。[14]肖汉宇和公婷在一项基于香港市民的实证调查研究说明,香港市民对腐败行为的文化认知会显著影响到举报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公众越认为腐败是由于‘熟人关系’或‘个人贪婪和自私’所造成的话,其举报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15]。刘昕则从伦理学的视角探讨了举报人的动机,印证了上述结论。他认为,举报人进行举报的主要动力就在于内心对于行为本质正义性的认定,整个举报过程体现了举报人自我的伦理认同和救赎。[16]
实际上,无论是私人组织内部还是在公共生活当中,个体的某些特征或个人经历都会影响他(她)的举报意愿。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在50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调查了个人对腐败的态度,数据显示,妇女、从业者、贫穷者和老人对腐败更不容忍。不过,郭夏娟和张珊珊对在校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和在职研究生(以党政人员为主,包括MPA学生和行政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的实证调研却表明:“在校学生的反腐意愿和积极性略高于在职人员,更为理想和热情。”[1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认为,对公众举报腐败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政治文化因素。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流文化越是对腐败不能容忍,公众举报腐败的意愿就越高。二是法律与制度因素。对举报人或证人的保护制度是否完备、举报是否安全便利、是否构建反腐举报激励机制、是否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反腐败机构等,都会影响公众的举报意愿。三是反腐败力度及其成效。反腐越坚决,成效越大,举报意愿则越高,这个因素可以看作法律与制度因素的具体实现。另外,这个因素和举报意愿二者之间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四是个体特征与心理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性格、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生活的经历(包括自身涉及腐败的程度)以及对举报的伦理认知等。当然,对于其中某些个别的因素,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
因此,公众的举报意愿会受到所在地区的反腐力度、公众反腐意识以及地区性举报制度的影响。本研究的特色就在于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以对C市市民的廉政感知和态度调查数据为现实依据,通过定性访谈和定量问卷调查数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分析影响C市公众举报意愿的各类因素,最终提出如何更有效地提高群众举报积极性的政策建议,以期弥补既有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的不足。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的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对C市城区居民腐败感知和反腐败态度的社会调查。访问员采用深度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式,对C市市民关于社会整体腐败水平的看法、腐败容忍度以及反腐成效的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调查。为了保证受调查者具有代表性,我们采用了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C市5个城区(市辖区)各抽取了4个小区,一共抽取20个小区,之后在每个小区通过系统抽样抽取了50户家庭。通过KishGrid技术,我们对抽取家庭中的成人进行再次抽样,确保被抽样的成员能够代表整体。50名访问员从2016年12月3日至2016年12月15日对这1000户家庭进行了入户访问,问卷回收后经过审核,共获得969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6.9%。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访问员使用事先设计的访谈提纲随机对其中30名市民进行了同一主题的深度访谈。在此基础上,本文首先对深度访谈数据进行编码分析,探索性提取居民(不)举报的原因。其次,對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基于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前一步定性数据提取的影响因素变量进行验证性分析和因子降维分析。最后,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得出结论(见图1)。
四、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根据扎根理论[18]的思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概括,形成新的概念和思想。对访谈数据进行定性分析,使用Nvivo11软件对访谈数据进行编码分析,对受访者所陈述的(不)举报的原因进行探索性提取。然后,进行定量验证性分析,针对问卷中公众(不)举报原因的调查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具体的分析思路如下:
(一)定性访谈数据分析
定性访谈数据主要来自于对30位市民的深度访谈,主要围绕公众是否举报的原因以及公众在反腐败中的角色等问题进行深度访谈。与本文主题相关,我们选取了被访问者对于问题“如果您知道某人可能涉及贪污腐败行为,是否会举报?为什么?”的相关访谈数据,对公众(不)举报原因进行提取和编码。
因此,本研究首先使用Nvivo 11软件对访谈数据进行编码,提取出市民反映的12个(不)举报的原因(见表1)。在30位受访者中,有29位受访者回答了相关问题,根据研究目的共提取了56种答案,并对其进行归纳编码,总结编码为12个原因。其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影响因素包括腐败容忍度、举报人保护、社会关系、个人利益相关与否、举报有效性、反腐责任感。一些出现频次较高的变量,将通过下一步的定量数据进行验证性分析。
(二)定量数据变量测量和描述
通过对定性数据的探索性分析,然后再进行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验证性分析。首先介绍各变量取值情况,一是因变量:公众举报意愿。调查问卷中,对受访者举报意愿的调查问题是“如果你知道某人贪污,是否会举报?”答案包括“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以及“不确定”(按缺失值处理)。二是自变量:影响公众举报意愿的因素。
1.X1-X4(见表2):在调查问卷中,专门设计一个问题调查受访者是否举报的原因,答案选项包括“举报方式是否便利”(举报途径)、“不确定举报是否有用”(举报有效性)、“担心信息是否都得到保密”“不想对我认识的人造成伤害”(举报人保护)、“不确定”和“其他”。选择某项赋值为1,不选赋值为0,选择“不确定”和“其他”按缺失值处理。
2.腐败感知程度(见表3)。问卷中对各领域贪污腐败程度的感知进行调查,主要包括党群系统、行政机关、司法机构、社会中介组织、银行及金融业等10个不同行业和领域的腐败程度进行调查,问题答案分为五个级别,分别是“非常严重”(赋值为1)、“比较严重”(赋值为2)、“不太严重”(赋值为3)、“根本不严重”(赋值为4)和“不知道”(按缺失值处理)。最后取所有回答的平均分即为各项最终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该行业(领域)腐败感知程度越低,即清廉程度越高。问卷中同时询问:“总体来看,您认为目前C市的贪污腐败现象的普遍程度如何?”答案选项包括“非常普遍”(赋值为1)、“比较普遍”(赋值为2)、“比较少”(赋值为3)、“非常罕见”(赋值为4)和“不知道”(按缺失值处理),最后取均值即为C市总体腐败感知得分,得分越高表示总体腐败感知程度越低,即清廉程度越高。
3.反腐满意度。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你认为,在过去一年,党和政府对贪污腐败的控制有效吗?”问题选项包括“非常有效”(赋值为1)、“比较有效”(赋值为2)、“不太有效”(赋值为3)、“完全无效”(赋值为4)、“不知道”(按缺失值处理)。所以,得分越低,则表示民众对反腐成效的满意度就越高。
4.腐败容忍度(见表4)。问卷中设计问题:“在你看来,下面的贪污腐败行为可以容忍吗?”选项涉及的贪腐行为包括行贿、受贿、索贿、买官卖官、贿选,得分从0(表示完全不能容忍)到10(表示完全能容忍)。该变量将公众在五个选项上的得分求均值而得。因此,得分越高,表示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越高。
5.腐败经历。问卷中询问公众:“在过去一年,你或你的亲友是否遇到过贪污腐败的情况?”如选择“是”赋值为1,选择“否”赋值为2,“不知道”按缺失值处理。
6.举报经历。问卷中询问公众:“你或你所认识的人是否曾举报过可疑的贪污行为?”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2,回答“不确定”按缺失值处理。
7.举报程序。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你是否知道举报贪污的程序?”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2,回答“不确定”按缺失值处理。
三是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教育程度以及在C市居住的时间。其中性别为虚拟变量,教育程度分为:小学或以下(赋值为1)、初中(赋值为2)、高中(中专)(赋值为3)、大专(赋值为4)、大学本科(赋值为5)、硕士及以上(赋值为6)。月薪收入答案分为:“无收入”(赋值为1)、少于2000元(赋值为2)、2000~4000元(赋值为3)、4000~8000元(赋值为4)、8000元以上(赋值为5)。在C市的居住时间,小于1年(赋值为1)、1~5年(赋值为2)、5~10年(赋值为3)、10年以上(赋值为4)。
(三)定量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定量数据分析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首先,对X和Y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进行卡方检验和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析。然后,对X1-X1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10个自变量进行降维。具体结果如下:
1.自变量和因变量相关关系分析。首先,要对问卷中涉及的解释变量X1-X10与因变量Y之间是否相关进行分析。因变量Y是定类变量,X1-X4和X8-X10同样也是定类变量,因此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检验方法是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X5-X7是定序变量,因此其与Y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进行检验(见表5)。
2.因子分析。上述一共有10個自变量,需要对其进行降维归类分析,因此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使用SPSS21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运算结果KMO=0.593,接近0.6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数据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将10个变量合并为4个公因子(见表6),累积解释总方差为55.782%。虽然没有达到85%以上,但因为本文运用因子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将自变量进行归类总结,并结合定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对公众举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因此这个结果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目的。
按照因子分析的结果,将原有的解释变量X3(举报信息是否保密)、X4(举报人保护)、X2(举报有效性),可以合并为一个新的解释因子。因为这三个变量都与举报制度相关,因此我们将其定义为公因子1:举报制度。同理,对于解释变量X5、X8和X6,根据以往研究,反腐满意度和腐败经历都与腐败感知度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这三个变量可以合并为一个新的解释公因子2:腐败感知度。对于X9和X10,是否有过举报经历与其是否知道举报程序也是相关联的,因此重新合并为公因子3:举报经历。最后一个解释变量X7单独归为公因子4:腐败容忍度。总结起来包括举报制度、腐败感知度、举报经历以及腐败容忍度。
五、结论
结合定性访谈数据分析和对问卷数据的定量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1.举报制度与公众的举报意愿有很显著的相关性。在定性访谈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9位受访者提供的56种答案(说法)中,举报制度是被提及最多的原因,相关的答案(说法)比率达到了35.72%,分别是举报人保护,占比为17.86%、举报有效性,占比为14.29%、举报途径,占比为3.57%(见表1)。而在因子分析中,举报制度这个变量维度包括X3(举报信息是否保密)、X4(举报人保护)和X2(举报有效性)这三个变量,它们都与因变量Y(公众举报意愿)呈较强的相关性。同时,变量X10(是否知道举报程序)、X9(举报经历)也是与举报制度有关的变量,但是X9与Y经过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后没有相关性,X10通过了相关性检验。因此,完善举报程序是优化举报制度中的重要一环。
2.腐败感知对公众的举报意愿没有多大的影响。在定性访谈分析中,与腐败感知相关的回答(包括腐败感知度、反腐满意度)合计只有3次,占所有56种答案(说法)的5.36%。在因子分析中,腐败感知这一维度包括X5(腐败感知度)、X6(反腐满意度)、X8(腐败经历)这三个变量。根据分析得出的结果,只有X8与Y有相关性,X5、X6与Y没有相关性。因此,腐败感知与公众举报意愿之间的相关性在问卷调查的数据中没有得到验证。但是,腐败经历与公众举报意愿之间的相关性在问卷数据中得到了验证。
3.腐败容忍度对公众的举报意愿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定性分析中,有13个答案(说法)与腐败容忍度有关,占比达23.21%,是访谈数据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变量。在因子分析中,X7(腐败容忍度)单独呈现一个变量维度,而且其与因变量Y的相关性也通过了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检验。因此,公众的腐败容忍度会对其是否举报产生较大的影响。腐败容忍度越高,越不倾向于举报腐败行为,这一结论在之前的研究中已得到证实。
六、政策建议
结合上述数据分析的结果,本文就如何健全完善反腐败举报制度,提高公众举报腐败的积极性提出以下建议:
(一)多层面健全反腐败举报制度,切实保障反腐败举报制度的有序运行和功能发挥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反腐败举报制度设计的完善与否与公众举报意愿有着非常强烈的相关性,应从多个角度和环节对反腐败举报制度进行完善。首先,简化优化举报程序,减少公众举报需要经历的行政程序和中间环节,提高举报的效率和快捷性。其次,要完善保密制度和举报人保护制度,从访谈中可以看出,很多公众都会对举报以后所面临的安全问题表示担忧。因此,要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重视对举报人的保护,包括其他相关人员的安全都需要进行保障,免除举报人的后顾之忧,才能更好地提高其举报积极性。最后,针对不实举报数量不断增加的问题,要相应地完善“澄清不实举报”的相关政策,对一些“错报”“枉报”进行澄清,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切实保障举报制度正常发挥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功能,避免其功能错位。
(二)多视角加大廉政教育力度,为民众举报腐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首先,加大廉洁文化的宣传力度,实现宣传全覆盖。不仅在政府公务部门,还应在企业和其他社会部门中都要加大传播力度,营造全社会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社会风气。其次,进一步拓宽廉洁教育的受众群体,针对腐败风气不断向低龄人群渗透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对在校学生的廉洁教育,设立专门的廉洁教育课程,从小帮助青少年牢固树立廉洁意识,使其自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最后,提高公众对举报腐败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公众对举报腐败必要性的认知,强化对举报腐败程序的了解。关于公众是否知道贪污腐败程序的调查,2017年有18.4%的公众表示知道举报贪污的程序,2016年和2015年分别为16.8%和15.9%,比重相对有所上升,这表明近几年反腐宣传力度的加大确实有利于增加公众对举报腐败的认知,但是还有较大的空间去提升。
(三)多渠道拓宽举报腐败平台,丰富民众举报腐败的途径和渠道
首先,完善传统的举报腐败方式,包括电话、信件等传统方式,对这些传统方式进行与时俱进地更新,使其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其次,为适应互联网时代技术发展的需求,可采用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有力拓宽举报腐败的快捷性和公众的可达性。最后,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在某些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列出负面权力清单及可举报行为的清单,让公众可以有针对性地举报腐败,提高举报的精准度。
(四)塑造良性社会关系网络,增强个人反腐责任感
在访谈数据中,一些频次较高的解释变量虽然没有在定量数据中得到验证,但是也会对公众的举报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人利益相关与否这两个变量均被提到7次(见表1),表明我国关系社会的特征以及维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会对举报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培育良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打破滋生腐败的社会关系,可以减少公众举报腐败的感情障碍。另一方面,访谈中反腐责任感也被提到3次(见表1),进一步说明对个人进行教育的重要性,针对不同行业的人员进行有的放矢的廉洁教育和廉洁文化宣传,可以有效增强公众的反腐使命感,将举报腐败行为内化为自身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1] 2012年全国纪检机关立案調查案件中41.8%线索来自群众举报[EB/OL].(2017-06-21)[2019-03-20].http://fanfu.people.com.cn/n/2013/0507/c64371-21390732.html.
[2] Yin Xu,Douglas E. Ziegenfuss. Reward Systems,Moral Reasoning,and Internal Auditors’Reporting Wrongdoing[J].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2008(4):323-331.
[3] Alexander Dyck,Adair Morse,Luigi Zingales. Who Blows the Whistle on Corporate Fraud[J]. Journal of Finance,2010(6):2213-2253.
[4] Siddhartha Dasgupta,Ankit Kesharwani. Whistleblowing:A Survey of Literature[J]. IUP Journa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0(4):57-70.
[5] 栾甫贵,田丽媛.吹哨者、公司、审计师的博弈分析——基于吹哨者保护制度的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7(1):38-48.
[6] 刘文革.腐败的检举成本与收益分析[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5(1):185-192.
[7] Marcia P Miceli,Janet P Near.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Beliefs,Organizational Position,and Whistle-Blowing Status:A Discriminant Analysi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4(4):687-705.
[8] Marcia P Miceli,Janet P Near.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al Correlates of Whistle-blowing[J]. Personnel Psychology,1988(2):267-281.
[9] 李志明.公民检举权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1.
[10] 洪丹娜.公民检举权的实现机制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5.
[11] 杜治洲.公众参与反腐倡廉的影响因素及其挑战[J].理论视野,2013(3):39-43.
[12] 余凯,孙牧欣.典型国家与地区的反腐败举报制度之比较[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2-19.
[13] 岳磊.正式制度、文化观念与信息传播对反腐败社会参与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1):130-134.
[14] 倪星,张军.文化环境、政府绩效、制度安排与公众反腐败意愿——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分析[G]//江南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的突破、创新及前瞻论文集(精华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15-35.
[15] 肖汉宇,公婷.腐败容忍度与“社会反腐”:基于香港的实证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16(3):42-55.
[16] 刘昕.举报人动机的伦理正义性辨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4-49.
[17] 郭夏娟,张珊珊.腐败容忍度及其影响因素探析——基于比较的视角[J].伦理学研究,2013(6):104-112.
[18] 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4):58-63.
责任编校 陈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