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在等我(外一篇)
2019-09-10李光彪
李光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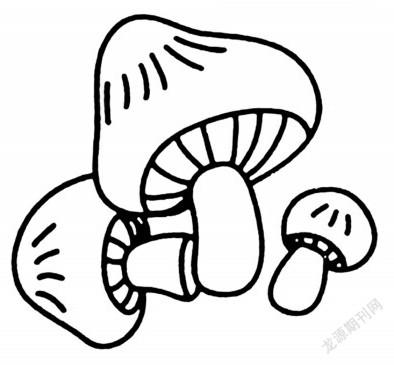
每年夏秋季节,地处滇中高原千里彝山胎盘里的故乡,经过阳光和雨水的不断舔吻,雷声鼓点般的呼唤,漫山遍野的蘑菇,如村庄里一个个呱呱坠地的孩子,孕育而生。此时,把我视作老家“一朵鸡枞”的大哥,总会隔三差五打来电话,催促我回去找蘑菇。我心里明白,是乡情在召唤我,故乡的蘑菇在等我。
故乡的蘑菇是一种不需播种、不需耕耘的天然庄稼。不论是树上生长的蘑菇,还是地上生长的蘑菇,谁赶早找到便是谁的。因此,故乡的人祖祖辈辈就与蘑菇相生相伴,人人都认识蘑菇。找蘑菇是故乡每个人从娘肚子里生下来,从小就要历练的生存本领。
故乡的蘑菇种类繁多。可蘑菇再多,就像父母能记住孩子的生日那样,人人心中都有一本方言叫“菌子”的《蘑菇志》。盛产蘑菇的季节到来,人们就会不约而同涌向山头,打开各自记忆的密码,东奔西跑找蘑菇。如果遇到干旱少雨的年景,蘑菇有时会迟到,有时冒不出来,让人等啊等,一直要等到第二年才能与蘑菇如期相见。所以,要找到蘑菇,每个人还必须总结一套自成体系的“天气预报”,才能根据气候多变的特征,胸有成竹及时找到蘑菇。
故乡的蘑菇也有自己的“户口册”。每一种蘑菇就像村庄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名有姓,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如以颜色命名的有青头菌、铜绿菌、母猪青、火炭菌、石灰菌等,以形状命名的有鸡枞、喇叭菌、牛肝菌、猴子菌、皮条菌等,以味道命名的有香喷头、鸡油菌、白香菌、酸芭蕉等。还有以节令命名的,如火把菌、杨梅菌、谷熟菌等等。因此,故乡的人认识蘑菇,就像认识村庄里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都能分别叫得出蘑菇们的姓氏名字来。而且,哪种蘑菇有毒,哪种蘑菇可以吃,大家都心知肚明。找回家的蘑菇既可以炒吃,也可以煮吃、烧吃,吃不完的,还可以用油煎炸成“菌子干巴”,或是腌菜一样腌吃,剩下的风干菜一样风干,储藏起来,要吃时用水泡发,即可用肉炒吃煮吃。在故乡的红白喜事宴席上,几乎都能吃到这种反季节的风干蘑菇菜肴。时代在变,如今故乡纯天然的蘑菇,已经穿上了市场的外衣,戴上商品的帽子,走进城市,走上餐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山珍”。经过商家冷链保鲜、加工包装的蘑菇,如松茸、松露、干巴菌、羊肚菌,更是身价百倍,漂洋过海。
故乡的蘑菇与乡村的生活息息相关。有用那些毒蘑菇,骂心术不正歹毒的人的;有用那些腐烂蘑菇,骂有外遇的女人的;有用形状各异的蘑菇,给人起绰号的。最有意思的是,故乡的人喜欢用蘑菇的贵贱作比喻,分别以“青头菌”、“大鸡枞”等来称呼村庄里谋得一官半职的人。还有用“鸡枞拱土”、“蘑菇打伞”来形容那些根红苗壮、读书优秀的孩子。也有人把“松茸”、“大根菌”、“奶浆菌”“、“翻毛鸡枞”等蘑菇,比作男人和女人的敏感器官,逗乐取笑的。几乎每一种蘑菇都与故乡的喜怒哀乐生活有关,人拟蘑菇,蘑菇喻人,有褒有贬,幽默诙谐。
故乡的蘑菇是孩子最渴望的零花钱。那年秋天,我们一群娃娃一边放牛羊,一边找蘑菇。看见不远处一辆拉烤烟的汽车正在猪哼似的爬坡,我们迅速把蘑菇在公路边摆开,目的是为了卖点读书的笔墨纸张钱。慢慢驶来的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司机看中了我那堆花骨朵一样的鸡枞,一边讨价还价,一边问我在哪个学校读书,说他是我们班主任的老同学。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八角钱成交。可是,司机把鸡枞提上车,却说没有零钱,便写了张欠条给我回学校找班主任拿。然后,我们在司机的默许下,像一群猴子爬上汽车,被拉倒四、五里外的山顶,就被司机卸了下来。过足车瘾的我们生怕司机跟我们要乘车费,跳下车,一个个比兔子还溜得快。那是我第一次坐过汽车。收假开学的第一天,上午全班同学进行卫生“大扫除”,下午交学费、书费领新书。坐在第一排的我,看着班主任一边强调学校“交不清学杂费不发新书”的规定,一边给同学们发新书。因家里无钱交,直到最后就我一个人没有拿到新书,我恨不能把头插进抽屉,手不停地搓揉着那张皱巴巴的“鸡枞欠条”。直到全班同学走后,班主任叫我留下,问我不交学杂费的原因,我鼓起勇气把司机写的“鸡枞欠条”递给班主任。班主任先是摇头,最后心地善良的班主任还是把书赊给了我。面对班主任,十二岁的我潸然泪下。
故乡的蘑菇是乡下人的亲戚朋友。蘑菇虽然一年只生长一季,但蘑菇就像那些家里饲养的猪鸡牛羊,总会在等主人。只要是蘑菇生长的季节,不论你什么时候上山,蘑菇都会在老地方等你,或多或少都能找到蘑菇,从不会空手而归。离家多年已成客的我回到故乡,顺着童年记忆的“脚迹窝”,翻山越岭去找蘑菇。每当看见松毛、腐叶凸起的地方,弯下腰扒开,那些“头顶盖头”的蘑菇,如童年和我“躲猫猫”的小伙伴,“集群式”的一大片,好似儿孙满堂的一家人,簇拥在一起。千姿百态的蘑菇,仿佛久别重逢的亲人朋友,笑容满面不停地向我打招呼。边走边找,不知不觉就到了母亲安身的坟山,令我高兴不已的是,当我逐渐走近母亲的坟茔时,坟尾巴上竟然长出了几朵鸡枞,我情不自禁掏出手机,给鸡枞拍照发微信,群里的“点赞”很快就雪花般飞来。有远方的朋友好奇地问我:“哪里找的鸡枞?”我回复:“在遥远的故乡。”朋友穷追不舍问:“你的故乡在哪里?”我回复:“在蘑菇生长的地方——云南楚雄。”
我伫立在母亲的坟前,看着那些如母亲化身的鸡枞,却迟迟一直没有动手拔。
旧时光里的县城底蕴
追根溯源,我所居住的滇中腹地牟定县城,是洪武二十二年从吕交城迁至今址共和镇的,屈指算来,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这些年,新城的藤蔓从旧城底蕴的根部长出来,沿着南大街义无反顾地向前延伸,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在涨潮般长大。渐渐的,旧城像一个掉队的孩子,变成了新城身后的影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习以为常地把县城叫做“老城区”和“新城区”。这样划分,对于很多地地道道的牟定人来说,也许是便于记忆。其实,旧城与新城,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在我的眼里,牟定县城更像一本书,蓬勃发展的新城如封面,饱经风霜的老城如封底,页码标示着老城的耄耋年龄。老城的容颜虽老,却面孔清晰,和蔼可亲。东、西、南、北四条扁担宽的街子,交叉呈十字型,四个不同的方向,入口也是出口,真可謂四通八达。只是街很短,若是站在“十字街”,一眼就能望到头,不论你从哪个方向进城,差不多一支烟的功夫就赶完了一条街,一顿饭的时间就逛完了老县城。
几多岁月,几多沧桑,老城与今天鳞次栉比的新城相比,没有森林般的高楼大厦,只是个矮子,仿佛由昨天的父亲、爷爷变成了新城的儿子、孙子。老城虽然商业气息没有新城区浓厚,看不到灯红酒绿的酒吧、歌舞厅、网吧、桑拿洗浴、超市等很多现代的场所。但对于久居县城,目睹着新城长大,老城变老的人来说,旧城始终是一部回味无穷的老电影,一本载满“小城故事”的旧书,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时不时翻开它,那段旧时光总会让人勾起无尽的回忆。
老城和新城,如同父子分家,早已另立门户,可生活在新城区的人如回家探望父母的孩子,隔三差五,总少不了要去老城旧街逛逛。我也不例外,有时新买了新裤子,由于身体不匀称,总要跑一趟老南街,去裁缝店剪裤脚。一句话,家里不论是谁的衣服有了破绽,或是纽扣丢了,或是拉链坏了,或是要换窗帘……家中一切必不可少的针头线脑之事,几乎都要往老南街跑。每次去缝纫店,总会遇到和我一样去那里缝缝补补的熟人,为数不多几块钱的缝补费,经常不是别人提前给自己付了,就是自己顺便帮别人给了。有时,家里的门锁坏了,钥匙丢了,或是鞋子坏了、脱胶了,同样少不了要跑到邮电局老东街口,找师傅配钥匙,修鞋、补鞋,同样会遇到熟人朋友。好像除了那里,几乎别无选择,还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说实在的,老城的旧街子并不那么热闹,有点像乡街子。房屋旧的居多,高高矮矮,参差不齐,砖房、瓦房,挤头夹耳朵。街坊邻居隔街相望,一家炒肉,隔街飘香,一人喷嚏,全城感冒。沿街的铺面都是自家的房子,门敞开,就在家门口做起各式各样的营生。做这些小本生意买卖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经营的项目大多以“老”为主,都是地道的传统工艺。譬如老东街上原来供销社对面的“宋家早点铺”、“马家牛肉馆”,好多年了,顾客是比从前少了些,但招牌还在人们的心头,每天回头客还不少。老西街原县政府大门口的“米线店”依旧如故,米线、面条、饵丝、卷粉“老四样”,天天开张经营,价格不涨,五元一碗,卖完为止。偶尔想去尝尝老味道,若是迟了,已收摊关门,白跑一趟。老十字街口的烧饵块,烤松毛豆腐,白天晚上,炭火通红,走过路过,常抵挡不住诱惑,随手买几块尝尝,特别地道。
时光在流逝,老街子上很多美好的东西也不知不觉在消失。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十字街口的饮食服务公司、老南街有名的餐馆,曾经为不少人举办过婚宴,现在已变成了人们舌苔上的永久记忆。原来是县城文体活动中心的老北街“灯光球场”、大礼堂,已面目全非,不复存在。曾经看戏、看球的热闹场景已成了小城里很多人的记忆。曾经不少老年人茶余饭后一堆堆聚在北街尾,此起彼落对唱山歌的景象也烟消云散。如今沿着北街走走,偶尔还能见到几个老人围在一起低头下棋,也许他们就是当年常来北街的“戏迷”、“球迷”。漫步东、西、南、北四条老街,从早到晚,简易的茶室里,常有世袭后裔的街民喝着大碗茶,一边打牌,一边消磨时光。
原来老县供销社、老贸易公司、老日杂公司的门前,已不是从前的商业核心区,自发形成的蔬菜、肉食摊,虽然品种不多,但早开午散,是老城区居民就近的“露水市场”。老十字街口的钟鼓楼下是牟定县劳务市场最早发育的地方,雇工的、卖工的都在这里成交。多少年来,八月十五中秋节,月亮团圆的时候,老十字街是年轻人玩耍“蛇贯标”的地方,少男少女们都会相约这里,站成两列纵队,互相拉起手,选一个人匍匐在众手架起的“轨道”上,大家一齐吆喝使力,把扮演蛇的人反复抬起,又丢又簸,让扮演蛇的不断往前爬,时间越长,阵势越大,越好玩。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转移了“战场”,在新城区的网吧、酒吧、KTV……
老县城实在很老,又窄又拥挤的街道已不适应车水马龙的需要,却又像一个捡垃圾的老人,拾遗补缺着人们的生活。老东街的银匠铺,多少年来以加工手镯、耳环、戒指等银器自产自销,如今“叮叮当当”的锤声已没有从前清脆。西街尾的榨油坊、碾米坊“嗡嗡”的机器鸣叫声也断断续续。来料加工的切烟房还在。因牟定盛产烤烟,很多人喜欢吸水烟筒,烟则是用烘烤过的烟叶切成黄灿灿的毛烟丝,随手捻一小团,放在烟筒哨子上,点着火“咕咚咕咚”翻江倒海地吞云吐雾地吸。所以,切烟房就是为了满足当地农民自产自销烟叶做经营、收取加工费的。主人为了招揽生意,还准备了好几支水烟筒,捻上毛烟,供赶街过往的人吸,便成了不打自招的商业广告。
老街子上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事物,总是与世无争地活着。坚守在南街上集群式的小旅店,以“南街旅社”为首,一家挨着一家,十分便宜,是乡下人进城打工、赶街歇脚的“根据地”,它们仍在接待着稀稀疏疏的来客。开了几十年的“李光理发店”如今还在,只是从南街搬到了西街,上了年纪的人都喜欢去关顾。老南街、老西街的理发店最多、最实惠。婴儿满月要剃胎头,小孩子要剃毛头,很多父母都喜欢带着孩子去理剪。若是男婚女嫁,乔迁新居,要合婚、要测个良辰吉日,就去老城区,西街、南街、东街都有此行当。要算命、要取名、要叫魂、要安山、要安土……一切源于民间古老的民俗,老街子上都名正言順挂着招牌。就连死者的花圈、香纸、纸衣服、纸钱店,寿木棺材店,一切丧葬用品,也只有老城区才能买到。刻章的、刻碑的、做喜匾、寿匾、门牌、锦旗的,要数老城区的南街口最集中。古老的石碑雕刻,现代的广告喷绘,纯手工书法雕刻的,电脑机器雕刻的,应有尽有。甚至修旧电器、修钟表等等,一切与生活有关的琐碎烦恼事,有时在高大上的新城区买不到、找不到的东西,只要去“请教”一下老城区,就能找答案,迎刃而解。
老县城在老去,我也在老去。记忆中东街上的中药铺消失了,南街上的照相馆消失了,西街上诱人的油条、黄粉消失了,北街上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消失了……很多事物仍在逐渐退化为人们往日的记忆。
城市化的进程在突飞猛进,老城区已经纳入了“棚户区”改造规划,即将脱胎换骨。我是个念旧的人,闲暇之余喜欢去老城的旧街逛逛,不是要去买东西,不是要去修修补补,也不是要去光顾小吃摊,而是越来越留恋西街上那几间老房子。我面对老房子打开相机,把镜头对准木板窗上当年用油漆刷写成的标语,拍下了没有被时光啃完的残余碎片,目的是想为即将消失的老县城留下一张底片。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