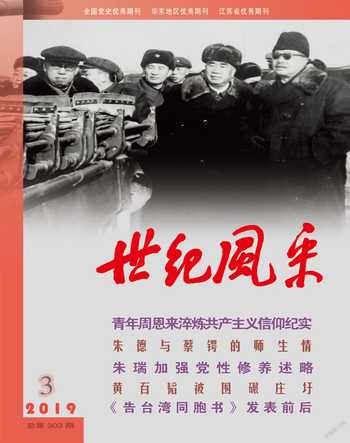井冈山见的经济斗争
2019-09-10曹春荣
曹春荣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地处湘赣边界。自从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这里,创建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来,怎样对付敌人,怎样打仗,成了此地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不过,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因如何筹措足够的、以粮草为代表的日常生活所需物资而产生的经济问题,其实并不比军事问题轻松多少。边界的党组织和红军与群众一道,为解决经济问题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且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井冈山五大哨口内,人口不到2000,产谷不上万担。红四军初到这里时,人马不过千余,部队用粮难以长年供给。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部队人马骤然过万,用粮、吃菜、穿衣及医药等经济问题日益严重而紧迫。“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以为继。现在全军5000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由于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以及营养不足、受冻及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但山上医生和药品均缺乏,只能靠草医草药对付救急。有的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治疗,痛苦死去。
造成边界种种经济困局的原因,除了当地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红军所需粮食、现金全靠打土豪解决外,还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界厉行经济封锁政策,货物、金融不能流通有關。山里的丝、木、茶油、米、花生等农林产品不能运出卖钱,山外的食盐、棉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也进不了山,边界军民生活艰难。由于边界一度实行过左的土地革命政策,“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乡村中的市场商店也遭到彻底破坏,“烧得精光,一切日常用品,无处可买,要点什么东西也无处可买,因此油盐起恐慌”。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人和红四军领导人对造成边界经济困难的原因和经济困难将带来的后果,有极清醒的认识。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写给上级的综合报告中指出,首先是边界物价“加速度地高涨”,最高处如大小五井,肉卖1元钱4斤,青菜萝卜之类卖100(文)钱1斤;从酃县偷贩过来的布匹、棉花及日用品,因为供不应求,价贵等同上海。“经济如此的崩溃,经济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众感觉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富中农多反水,中农动摇,贫农不安,农村中革命战线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经济没出路,不仅导致大量农民出走,也成为红四军主力下山、游击赣南的重要诱因。所以,杨克敏断言:“这个经济恐慌的危机,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也指出,红区白区间几乎完全断绝贸易,其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所以,毛泽东在他为中共湘赣边界二次党代会写的决议中告诫道:“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民主主义与自力更生
红四军(及后来的红五军)是怎样应对这个最困难的经济问题的呢?
首要的当然是发挥党的作用,包括组织领导作用如“支部建在连上”、政治教育作用如阶级、理想、前途教育等、先锋模范作用如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等。其次,“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日‘伙食尾子……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因为官兵待遇平等,所以红军物质生活如此菲薄,“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诚然,经济困难问题多因物资匮乏而起,除了依靠精神力量外,更多的还得通过寻求物质的获取来解决。在这方面,红军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很多人间奇迹,克服了很多实际困难。
粮食不够吃,他们把红薯、南瓜切成片、切成丝晒干,合着红糙米一起煮。为利于和敌人作长期斗争,他们往返几十里从山下挑粮食、背油盐、干菜到山上贮藏。有的战士背上磨起了红块,大水泡套小水泡,却毫不在乎地说:“不要紧,起点泡算什么?我们在枪林弹雨中都不怕,还怕这点泡泡!”有人还编起了顺口溜:挑谷上坳,粮食可靠,为着(山上)伤员,不怕起泡。红四军军长朱德那时已年过40,在军中算得年长了。但他用一根刻有“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字样的专用扁担挑粮,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根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戴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50斤,竞比年轻的战士还多挑了10多斤。没有菜吃,红军一面开园种菜,一面就地取材,山上挖竹笋、摘木耳,河里摸螺丝、抓鱼虾,田里照泥鳅、盘黄鳝。这些劳动不只改善了伙食,还给大伙带来了喜悦和欢笑。
山上天气寒冷,夜间尤甚。寒冬季节,许多官兵没有棉被,他们用稻草铺床,往布被里塞稻草做成“金丝被”。半夜冻醒了,起来生个火塘烤火,或者抱团取暖。
为支持武装割据,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依靠井冈山群众,利用战争缴获,兴办了不少保障军需民用的后勤机构。举其要者有:
红军被服厂,设址在桃寮张家祠。初时募乡间裁缝以手工缝制粗布军衣,后用战争缴获的缝纫机、洋布、洋线,组织流水式生产军衣、绑带、帽子、子弹袋等。厂子一度拥有60多名工人,6架缝纫机。
红军军械厂,位于步云山上。其基础系袁文才农民自卫军修械所,后经红四军抽调20多名安源煤矿、水口山铅锌矿机修工人出身的战士加入,遂扩充为红军军械厂。厂里能修复各种枪支和追击炮,生产单响枪、步枪子弹及生铁手榴弹。
红军石印厂,设在茅坪象山庵。1928年5月19日,红军第二次占领永新城,从赣敌杨如轩师部缴获一架油印机,以此办起石印厂,隶属湘赣边界特委。边界党团员训练班讲义材料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均由该厂印刷。
茅坪粮库,由红四军军需处在茅坪大户谢冠南家设立,红军四出打土豪运回的稻谷全部存放在这里。除保管粮食外,粮库还设置十多张砻床,雇请茅坪村妇女砻谷筛米。
大垅硝盐坊,由红四军军需处开办,设在大垅后街尹家大店,延请大垅乡工农兵政府主席朱天伦负责,有员工20余人。作坊取老墙土熬硝盐,代替稀缺的食盐。
红军医院,院本部设于攀龙书院。初创时只有医生3名,后从附近各村招收乡间郎中、草医草药师数人,增设茶山源草药店。1928年5月,红军两克永新县城,从赣敌杨如轩师缴获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从而令医院扩展到拥有医务人员42人、护理人员近60人,并有一个担架排。院本部可收治伤病员300多人,有效缓解了红军伤病员救治的压力。
调整政策,发展商贸
中共六大决议的传达贯彻,尤其是大会指出当前最危险的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警告,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调整对小资产阶级政策和商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因政策失当加之敌人严密封锁造成边界经济恐慌,则从现实需要方面,推动了根据地对上述政策的调整。这些调整固然反映在书面形式上,而更多的却体现在实际行动中。
1929年1月颁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指出:“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这几句话表明:第一,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政权,承认商人通过辛苦经营赚取利润是正当合法的;第二,商人只要服从共产党及工农政府的管理,缴纳一定的税,就可以放心做生意,而不必担心受到斗争惩罚。这显然有别于此前过左的做法。
同年由红四军军党部发布的《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一文,更具体地反映了对商人商业政策的拨乱反正:“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也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
循着调整过的政策策略思路,边界工农兵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发展根据地的商业贸易。如整治和辟建圩场,促进物质交流。边界经济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交易多数凭藉“日中而市”的逢圩办法进行。遂川县城西北20余公里外的草林圩,是个有200多家商铺、600多户人家的大圩镇,每逢农历一、四、七日为圩期,所谓“十日三圩”。届时方圆百里的农民群众都汇集这里,卖出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买回所需日用工业品或手工艺品。然而,农民群众的自由交易却常常不得不忍受镇上劣绅兼奸商黄礼瑞的重重盘剥,弄得外乡人来过一回便不敢来第二回。原来是黄礼瑞勾结地方反动靖卫团,在草林圩周边设了5道税卡,群众买卖何种东西都得向他们纳税进贡。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县城后,随即在黄坳至草林的70里路上,打掉了靖卫团的所有税卡,惩处了黄礼瑞,取消了国民党当局的苛捐杂税,宣布农民在圩上交易的商品都不必完纳捐税。这一来,草林圩更加繁荣,物资交流大为活跃,赶圩的人数多至2万余人。
为繁荣农村经济,毛泽东还倡议、擘划了宁冈县大垅红色圩场的开建。大垅镇处赣湘数县交界地,在这里建圩场便于边界各县群众及商贩进行买卖交易,互通有无,调剂余缺。
此外,边界工农兵政府还在新城、睦村等地恢复了老圩场,开办了类似消费合作社的公营商业“公卖处”“公卖店”,出售打土豪没收的物品,以及战利品。这样做既充实了市面物资,又使政府和紅军有所获利,减轻群众负担。
为扩大边界竹木等林产品出口,他们又组织了边界委员会、竹木委员会等机构,设法与商人建立生意往来,打通关节进行红、白区间的物资交易。这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有积极意义。
铸造银元,山内流通
货币是人们进行交易活动的媒介。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向群众购买粮油菜蔬等物品,既不能用国民党当局发行的货币,也不能用市场上大小商号推出的代金券,否则易被敌币扰乱边界金融,破坏边界经济,就只有自己另谋良策了。
当年,金属铸币如银元、银毫、铜元、制钱,还是市场上的硬通货,尤其是银元,其信用高于任何纸币。红军手中有大量打土豪及战争缴获的银元、银饰品、银器具,银元当然可直接用于交易,但用一点少一点,恐难以为继。这样,利用银饰银器制造银元的设想,很快就在井冈山变为现实。
20世纪20年代,客家人谢荣光、谢火龙从广东来到井冈山下谋生。他们身怀制造银器技艺,一边务农,一边私铸银元使用。红四军未上山前,当地“山大王”之一的王佐已结交谢氏银匠,并参与私铸银元。此后,身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军委委员、三十二团副团长、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的王佐,便顺理成章地向领导建议请谢氏银匠上山办厂,铸造银元。此议旋即得到毛泽东、朱德等的同意。于是,谢荣光、谢火龙应邀到上井村开办造币厂。随着业务扩大,后来又在牛路坑、银坑、黄竹坳、金狮面等地增建了几处车间。
上井造币厂以火炉、风箱、熔银瓯、铁锤、冲压架、碓石、铁砧、锉刀等粗笨设备及模具,仿制墨西哥鹰洋。由于设备、工艺粗糙,做出的银元整体并不平正,而是凹形。为区别外间银元,这里的产品用钢錾打上了“工”“人”或“七”“八”“九”等字样。红四军军需处将它们等同“袁大头”,发给部队去用,但开始时信用并不好,群众怕用。红四军和边界工农兵政府于是广泛宣传,告诉群众这种银元是我们用银首饰制造的,不会假。同时允诺群众可以到“公卖处”“公卖店”购买货物,价值跟“袁大头”一样。慢慢地,群众相信并接受了,井冈山造银元遂在边界流通开了。不过,因为品相不怎么好,又是仿造,井冈山造银元从未在边界地域以外流通。
用手中掌握的银饰银器仿造银元,既解决了这些物件因不便分发给群众而产生的积压问题,又使红军手头多了硬通货,便于从市场内外购买生活物品,可谓一举多得。
井冈山根据地仿造银元的成就和经验,不仅有利于边界的经济斗争,而且为后来中央苏区铸造金属币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