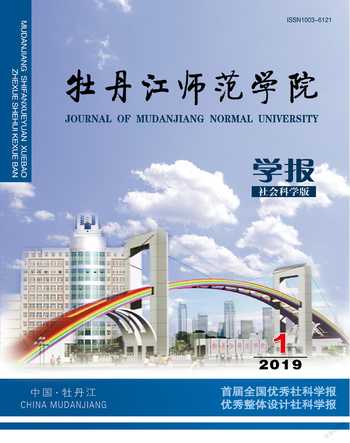挑战强权观念 追求人性平等尊严
2019-09-10张荣升丁威
张荣升 丁威
[摘要]乔利深刻体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以不动声色的叙事揭露了强权化的二元观念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残酷。《斯科比先生的谜语》批判了护士长为代表的强权文化,展现了以斯科比为代表的老年群体的生存危机;《皮博迪小姐的遗产》赞扬了身处逆境却彰显人性光辉的作家霍普威尔;《可爱的婴儿》赞颂了青年知识分子为自由和理想所进行的努力和拼搏;《代理母亲》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在感情和事业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乔利聚焦弱势群体,赞扬了弱势群体追求平等自由、捍卫人格尊严付出的努力,彰显了生命意识和平等尊严之上的人性张力和人生审美。
[关键词]伊丽莎白·乔利;弱势群体;强权;人性尊严;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19232007)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女作家。由于其卓越贡献,她荣获澳大利亚荣誉勋章,当选为澳大利亚作家协会主席,并被四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乔利是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作家,黄源深教授认为,乔利作品主题模糊、含混、抽象,难以捉摸;笔下的很多人物性格怪僻,举止出格,读者不容易把握;小说提供的图像又常常是零散、跳跃、不完整的,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1]。乔利在《斯科比先生的谜语》(1983)《皮博迪小姐的遗产》(1983)《可爱的婴儿》(1984)《井》(1986)《代理母亲》(1988)《果园窃贼》(1995)和《天真的绅士》(2001)等作品中,以不动声色的叙事揭露了强权化的二元观念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残酷;并通过作品中弱势群体的不懈抗争,张扬了弱势群体和弱势文化的生存权力;批判以剥夺和毁灭为特征的强权文化,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严。
一、批判强权文化、强调生命意识和平等尊严
《斯科比先生的谜语》(Mr. Scobie's Riddle,1983)是乔利创作的第三部小说。目前国内只有梁中贤教授的“权力阴影下沉默的符号意义”运用符号学视角解读了该作品。斯科比先生是圣·克里斯多佛和圣·裘德疗养院的患者,被亲人抛弃,被疗养院的护士长冷落。他生活的唯一慰藉是靠回忆打发时光。被安置在疗养院后,他感到一切都很陌生,只能在音乐的世界里寻找和谐。小说家哈利被斯科比播放的音乐吸引,“在这个精神的荒原,还有被救赎的希望么?只有在你的音乐中才能找到。你知道吗?我已经饥饿多年,是的,饥饿,当然我指的是文化饥饿”[2]99。这不禁使人想起T.S.艾略特的《荒原》,用艺术赋予混乱的生活以秩序和意义。与唯美主义、零度写作不同,乔利强调艺术的功用。作为作家,乔利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感,她的作品关注人类生存状况,再现了弱势群体遭受的困境与磨难。萨特认为:“如果文学什么都不涉及,它便一文不值。这就是我所谓的‘介入”[3]。乔利的小说就是一种“介入文学”,《斯科比先生的谜语》展现了老年人的孤独与困苦,揭露了人们灵魂深处的贪婪与冷漠,书写了老年人对理想精神家园的苦苦追寻。
疗养院本应是老人获得关爱的地方,此类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年老体弱的人,却并不以改善提高服务质量为宗旨,也不以延长患者的寿命为目标;职员们关心的是个人的贪欲,他们的工作依据效率而非患者的需求。更令人担忧的是,来这里疗养的老人都受到了医院不同程度的盘剥。斯科比被外甥强行安排住进疗养院,这个陌生的环境令他感到压抑。“与其它地方的习俗相比,澳大利亚人也许更容易把老人委托给类似的机构”[4]。然而,在疗养院老人远未受到应有的对待。斯科比在给外甥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很孤独,很悲伤。你什么时候能来看我?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这里一点都不适合我”[2]124。疗养院的居住环境恶劣: “这里的生活没有尊严,丝毫没有。厕所门根本关不上。”[2]46。狭小的空间里苍蝇满天飞,室内散发出难闻的尿味和臭味。隔壁房间里喋喋不休的闲聊声、打麻将的声音,老人受尽辛苦,连休息、睡觉都难以保障。作品中,护士给老人洗澡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老人像物品一样被任意扔、塞、堆,已没有任何尊严。小说家哈利同样感叹老年人的不幸遭遇:“我们只不过是调查问卷的素材,被他们用来统计数字和结果而已”[2]177,因此,不要对他们有所期待。在这个冷酷的疗养院,老人得不到友善的对待,只是一个物品。谜语的使用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象征。斯科比多次向身边的人提问:“人人都知将要去,却不知什么时候、如何去的地方是什么”[2]165乔利在作品中没有给出“谜语”的答案,但细心的读者定会猜到谜底是“死亡”。
斯科比是一位虽处弥留之际仍追求人格独立、维护人性尊严的音乐教师。虽然在疗养院受尽剥削,为了保住自己的房子和土地,斯科比勇敢、机智地与护士长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他想尽办法,三次尝试逃离疗养院。逃离与求索是《斯科比先生的谜语》着重表现的主题之一。纵观世界文坛,不难发现逃离与求索是作家反复表现的原型主题。斯科比自搬进来就渴望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努力探寻更有意义的生活。为了逃离疗养院,斯科比向他人寻求帮助,他首先向外甥女琼求助:“琼,我不想呆在疗养院。一天也呆不下去,一天也不愿多留,我想回家”[2]45,可外甥女丝毫没有怜悯心,心中始终盘算着如何把舅舅的房子弄到手:“舅舅,你的那片土地很值錢,你一个人享用太自私了”[2]50。琼更是不经老人同意,私下和租户签了约,让老人有家不能回:“你现在回不去了,我已经租出去了,租期至少一年,我又不能把人家赶出去”[2]51。第二个求助对象是他的外甥。外甥来后,他迫不及待地表达想要回家的愿望:“你终于来了,哈特雷,我想离开疗养院,必须离开”[2]126。然而,他的外甥和外甥女一样冷漠无情,根本不顾及老人想家的心情,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舅舅回家。他先假装给老人租了另一个房子,后来又谎称房子被拆掉了。老人的心被亲人的冷漠伤透了。但他没有放弃,而是向志愿者怀特小姐寻求帮助:“请一定要带我离开这里,你是开车来的么?我必须想办法离开,你要相信我,我身体很好,我只想回家,一天也不想呆在这里”[2]172。反复求救,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援手。无奈之下,85岁的斯科比勇敢地面对困难,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向命运抗争。有一次,为了躲避身边认识的人,老人借故躲到厕所,翻墙而出,步履艰难地走到火车站,却因工人罢工导致火车停运。老人回家心切,不顾旅途劳累,步行回家,结果不堪重负,终因体力不支被警察带回疗养院。第二次,老人顺利买到火车票:“买单程票,我再也不想回来了”[2]167。登上火车后,斯科比便开始畅想着回到家的情景:“家里的一切应该和被带走前一样吧”[2]170。但最终,他还是被护士娆玲发现,带下了火车。为了自由,为了生命的尊严,斯科比决定再搏一次,准备趁着外面下暴风雨匆匆离开,却被看护人员发现:“我告诉你,你今天哪也别想去”[2]187。一句话让斯科比的心凉了半截。家是老人心灵的港湾,作品中的老人都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强行送进了疗养院,“作品展现了一幅悲凉的存在主义画面:老人们的努力注定徒劳,回家的愿望永远无法实现”。[5]虽然,没能成功逃离疗养院,但他反抗强权,追求人格平等的行为值得称赞,为维护生命尊严所做的努力值得同情。人终有一死,每个人都将面对。如何善待老人?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如何让老人老有所用,老有所为,在晚年的生活也具有尊严和生命意义?乔利在《斯科比先生的谜语》中聚焦老年人的危机,提高了社会对老年人弱势状态的人性化关注,批判了以护士长普莱斯为代表的强权文化,教导我们换位思考,善待老人,善待人生,善待我们自己。
二、身处逆境、彰显人性光辉
坎坷的生活经历和艰辛的创作历程使乔利深刻体会作家的弱势状态:他们是思想的巨人,现实的弱者。“作家可能是渺小的,可能是弱者,可能面临种种危机,然而,其作品的光芒却可以温暖他人。”[6]《皮博迪小姐的遗产》(Miss Peabody's Inheritance,1983)中塑造了身处逆境、彰显人性光辉的作家霍普威尔(Hopewell),赞扬了作家伟大的道德光辉。乔利聚焦作家危机书写,提高了人们对作家弱势状态的关注,彰显了生命平等尊严和人生审美。
霍普威尔是乔利笔下身处困境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多年前发生了一次事故,她从马背上摔落下来,脊柱严重受损,从此困在床上不能自由行动,只能在养老院度过余生。她非常清楚:“作家没有朋友,……即使有朋友也不会读作家创作的作品。”[7]69,这句话道出了作家经常面临的尴尬境地,没有朋友,就自然缺少与他人的交流,没有交流,就自然面临难以忍受的孤独。人类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上帝,崇拜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都蕴涵着寻求依赖,摆脱孤独的愿望,而且这种愿望至今仍然存在,这也常常使有创造性的作家深陷孤独之中。许多著名的作家都曾有过孤独的内心体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迷失在黑暗森林里”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陈子昂,“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李白,“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杜甫,等等,都充分展现了作家的孤独。
霍普威尔是幸运的,黑暗中有一盏灯为她而点起。带给她快乐和幸福的不是别人,是作家梦寐以求的倾述对象,忠实的读者皮博迪。孤寂之中,霍普威尔偶然收到了皮博迪小姐的一封来信,表示对自己小说的赞赏。皮博迪是伦敦一个五十多岁的打字员,没有抱负、没有野心,没有期待,生活枯燥乏味。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除了上班外,就只有回家侍侯卧病在床的母亲。她根本不知生活还有其他方式,不了解外面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世界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生活并不都是枯燥乏味的。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说故事、讲故事、写故事都是为了有人能够听故事、读故事;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话語,使人看到一个开拓的空间、一个希望的世界、一个行动的准则。“小说的存在本身就是希望的传递……伊丽莎白·乔利就是这样的小说家之一。”[8]小说作品所蕴含的深刻信息唯有被读者阅读并感知之后,才能显示出教育意义。因此,在接受美学理论家看来,读者的接受活动不是一个单纯的接受过程,而是一个在阅读中与作家共同创作的过程。斯坦利·费希更是针对新批评的感受谬误提出“文学就在感受中,文学就在读者之中”的观点。[9]阅读小说激发了皮博迪生活的活力,给了她把自己的世界变成另一个世界的能力。霍普威尔也很高兴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读者来信,并将正在创作的小说一章章地寄给皮博迪。对于作家霍普威尔来说,皮博迪是她写作激情得以延续下去的火种。这其中也隐藏着作家的一个愿望:即理想的读者是小说存在的理由。而皮博迪小姐就是一个接近于宗教式的虔诚而又崇拜的理想读者。她甚至专程到图书馆查了作家名字的含义:“自由的自然之主。她和她的一群仙女在山上狩猎。她们生活在树林中、牧场上。她与树的培植有关,是富饶女神……她既是贞洁女神,又是生育女神……这些都是戴安娜”[7]73。
霍普威尔的小说,以及信件中所描述的作家生活强烈地吸引着皮博迪小姐,使她不自觉地进入到了小说世界中。小说写得最好的地方就是小说在小说家和读者之间交替进行的时候。小说最后,皮博迪放弃了英国的工作,决定去澳大利亚给自己的偶像一个惊喜。然而,令她震惊的是,自己的偶像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在农场里穿着高筒马靴从马背上潇洒地下来迎接她,而是静静地在一家养老院里安然离去。多么仁爱、体贴的作家啊。作家可能是弱者,可能更需要社会的关注;但是,作家却能带着生活中的遍体鳞伤去为他人疗伤。在这一点上,作品就是作家们开出的一剂良方。“在艰辛的人生旅途中,霍普威尔饱尝痛苦,却为能够改变他人的生活而感到欣慰”[10]。霍普威尔的小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这个人就是读者皮博迪。
三、聚焦作家弱势状态、传递人性尊严
《可爱的婴儿》(Foxybaby,1984)是乔利的第五部小说。主人公阿尔玛·博奇(Alma Porch)既是作家,又是教师。小说的艺术特色获得了评论界的肯定,同《皮博迪小姐的遗产》一样,作品使用了小说套小说的技巧。小说融合了多种表现手法,既具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故事生动、人物鲜明的可读性,又不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写作特色。小说家以自身的职业生活为小说的艺术背景似乎有些狭隘,如果把握失度,很容易陷于当局者迷的思维定式,对审视人生带来干扰。因此,作家题材是一个很难把握、也很少有作家采用的题材。乔利亲身体验了职业作家的艰辛,并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作家的生存危机,以期提高人们对作家群体弱势状态的关注。
小说开篇,博奇受邀到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应聘。这个学院位于一个叫Cheathem West的地方,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废弃场所上的暑期减肥学校。这里,文学不再向人类传播真理和智慧,而是用来供学员们排练戏剧,以此减轻体重。她的作品与减肥有什么关系? 专职从事创作“精神食粮”的作家,在这里变成了为他人谋取物质利益的工具。不仅如此,博奇小姐还要时刻听从校长的安排和学员的建议,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解读和说明,甚至于研讨会的主题都得依学员的兴趣进行。但无论情愿与否,她都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她需要这份工作以减轻和缓解生存压力所带来的孤独无助感。巴尔扎克认为:“人有一种对孤独的恐惧。而在所有的孤独中,精神上的孤独是最可怕的。”[11]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总是那么地困难。博奇发现自己在现实世界里成了一个无语者。在这部多半由对话构成的小说里,除了博奇小姐朗读自己的作品外,很少有她的声音。这充分反映了年轻知识分子博奇真实的生存境遇:物质上的艰难窘迫与精神上的孤独无依。其实,人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普遍的。除了博奇小姐,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展现出不同程度的孤独。正如维加斯夫人所说:“真相就是,博奇,我到这个学校来不是为了减肥。我到这一类学校来是因为我孤独。我想你不懂我的意思。我期望你有思考,你有写作,你不会感到孤独,事实上你需要大量时间独处。我太孤独了。我不属于任何人也没有人属于我。”[12]这便是现代人内心的真实写照:孤独。
写作是作家生命寄托之所在。但对博奇来说,安静地写作却成了奢望。房间里的喋喋不休的闲聊声、嬉闹声、电话声,使她不能安心地创作。在学校里,博奇还多次遭到不公待遇。虽然在这所学校任教,但却得不到一名教师应享受的权利和尊严。即使使用学校厨房电源这样的小事,都需要经过迈尔斯夫人的同意,并自己承担费用。为了让自己指导的节目顺利进行,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博奇从未付的工资中拨出100澳元给了迈尔斯夫人。还有一次,哈罗小姐要带她去两个男同性恋的住处居住,虽然感到十分为难和尴尬,但是她也没有反对。作家所面临的生存问题不仅仅是这些,他们常常要无端地遭受尖酸刻薄的评论家们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指责。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就受到了评论界的无情攻击。济慈在致友人的信件中清楚地表明,虽然他认为自己可以坦然面对这种无端的指责与莫明其妙的批评,其实他的内心总是患得患失的。安徒生的文学之路也不平坦。由于出身低微,他呕心沥血完成的作品根本不受重视,也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许多批评家恶语中伤,批评他文章里“别字连篇”,沒有丝毫“文化”。这使得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跑到国外寻求一点安静,平静自己的心绪。
虽然博奇深处困境,备受压迫和剥削,但她并没有逆来顺受,仍然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并通过表演的作品传递人性的尊严和平等意识,使广大学员终身受益。故事结尾,维加斯夫人的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决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学员们不仅实现了减肥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想上实现了质的飞越。从这个意义上讲,博奇小姐对学校强权的反抗,为追求平等自由、捍卫人格尊严付出的努力获得了胜利,虽然柔弱、孤独,但她用自己的思想和聪明才智赢得了学员们的尊重和认可。《可爱的婴儿》的结尾令人意想不到:原来,故事中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博奇在公共汽车上做的一个梦。博奇身单影只,对未来的生活感到担忧和恐惧,尤其是当自己的汽车被撞坏以后,她对所去的学校更增加了某种惧怕。但是由于无人可以倾诉,她的担忧和恐惧便以梦的形式得到了宣泄。幸福的人决不幻想,不幸的人才需要幻想。在现实中,由于受到自我和超我的抑制以及外在条件的制约,人的本能往往无法得到满足,于是渴望通过艺术作品来实现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因此,艺术又是人们摆脱痛苦的一条途径。写作正是这样一条令乔利摆脱痛苦的途径。充满挫折与痛苦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使乔利深刻体会到作家生存的艰难并将作品聚焦于作者弱势状态的书写上。
四、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道德危机
《代理母亲》(The Sugar Mother,1988)是乔利的第八部小说,故事名称中的“Sugar”是由对“Surrogate”的误读形成的。乔利用传统第三人称叙述方式,随着佩奇教授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他跳跃的纷繁思绪展开叙述。乔利通过对艾德温教授境遇的深切关注,揭露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失落潦倒,深刻反映西方现代生活的荒诞不经。作为澳大利亚学院派小说家的代表,乔利通过作品唤醒了读者重新审视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乔利的作品展示了学者文人光鲜耀眼生活的另一面,丰富了学院派小说人物画廊”。[13]如果说学院派小说家布雷德伯里通过作品集中展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软弱与无助,洛奇的作品更多关注学者在事业上的学术纷争和争权夺利,那么,乔利在小说中更多关注学者文人在生活、情感和事业中的弱势状态,给读者展示了象牙塔内部分学者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尴尬处境。
故事开篇,埃德温教授独自一人在家,打扫房间,煮个鸡蛋,读读报纸,看看电视,来到书房撰写论文,生活单调、孤寂而压抑。他的研究领域是伊丽莎白时期的法律,已经54岁,为人谦和内向,不常与人交往,稍有感触便引经据典:“小说不外乎两种,一种以主人公们终于结婚并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为结尾,另一种以主人公们已经结婚,生活得不幸福为开头。[14]19埃得温不时陷入回忆,又不时从回忆中惊觉回现实。这符合他逐渐进入老年的生理、心理特征。学校里的年轻同事似乎都在等他退休了,妻子也大大咧咧地建议他提前退休,“你可以去去画廊或者在我忙的时候帮帮忙。”[14]13乔利的小说大多描写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挣扎,他们在生活中的压迫感、孤独感、恐惧感。埃德温夫妇的生活看似轻松、惬意,但已渐入老年,膝下无子一直是二人婚姻生活中不可承受之痛。随着埃德温的思绪,聪明的读者可以随时发现他们对孩子的渴望。他每天早上都穿过马路,经过一片松木种植园,步行到学校上班,但生命变得如此脆弱,毫无意义。他喜欢孩子们尖叫的声音。“要是塞西莉亚有一个自己的女儿的话,事情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14]105而妻子塞西莉亚也是每日都经受精神缺失的煎熬。没有孩子这件事成为了利拉母女引诱埃德温上当的直接诱饵。妻子一走,家中格外冷清,埃德温教授伏案备课至深夜,却意外地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邻居鲍特(Bott)夫人和20岁的女儿利拉(Leila)因被锁在门外前来借宿。埃德温一向最怕人打搅,害怕有陌生人出现,却慷慨地接纳了她们。他发现波特夫人是料理家务的能手,尤其烧得一手好菜,并且随时注意不让他生厌。在随后的对话中,利拉的母亲开始怂恿埃德温请利拉代孕生子。她多次旁敲侧击地询问埃德温对代孕生子的看法。“你们考虑过领养一个孩子吗?”[14]64如果你们不想领养孩子的话,“总是有解决办法的,他们都怎么说的,代孕母亲,是吗?”[14]67“这比领养好多了,这就像是你亲手做的蛋糕一样,是你自己在家做的,你了解里面有什么。”[14]68利拉母亲显然在有步骤地实施她的计划,先问埃德温想不想领养孩子,如果不想领养孩子的话,自然就需要代孕生子 (surrogate)了。
渐入晚年等待退休的埃德温早已被社会边缘化,学术平平的他也无法获得学界的认可,生活对他来说,无疑是平淡、乏味的,而利拉母女的出现使他压抑已久的本我又充满了“各种沸腾的兴奋”。当朋友达芙妮劝他采取办法赶走她们时,他竟迟疑起来,觉得心里想得越来越多的是利拉,而不是妻子。他盼望妻子永远留在埃及,不再回来。这恰恰反映了西方文明下道德约束的苍白无力和知识分子面临的道德危机。故事按利拉母亲的计划如期展开,利拉很快怀孕,埃德温每天下课就迫不及待地回家,利拉总是在门厅笑脸相迎。埃德温觉得前所未有的幸福、安全和满足。他对利拉母亲的“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还表现出些许的赞赏并开始重新考虑遗嘱的问题,“利拉,利拉的母亲和孩子一定都要考虑在内,妻子塞茜利娅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受益人,其他三个人一定要在遗嘱的分配中获得应有的份额”[14]129。经过医生的推算,孩子的预产期将是3月14日。当妻子回家后,孩子已经3个月大了。他外婆一再称赞“长得与爸爸一模一样”,但埃德温很高兴孩子完全像利拉。她喂养孩子的神态令他敬意油然而生。此时,妻子突然决定提前回家,埃德温紧张得不知所措, 不得不匆忙地安排利拉与母亲匆匆离去。他付了所有应付的款项,外加两件昂贵的毛皮大衣的钱。他请达芙妮来照看孩子,自己准备去接妻子,但是孩子哭闹不休,这时,利拉与母亲突然转回来,看都不看埃德温一眼,一把抱过孩子喂起来。利拉母女没有按约定淡然离去,却突然返回,使得埃德温突然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外人,根本不是孩子的父亲,他也不再确信利拉母亲之前所说的都是真的。埃德温开始痛苦地意识到,他也许真的不是孩子的父亲。最后,他别无他法,决定送她们暂时去邻屋安歇,带上了孩子所有的东西。家里顿时恢复得与原来一模一样。他与达芙妮等候妻子回来,却接到电话说她暂时因航班问题困在埃及了。埃德温虽知那孩子并非己出,却沉湎于儿子、情人、父亲的三重角色中,柔情缱绻、情不自禁。他恍惚中听见窗外似乎有脚步声,担心明天她们已不在那里,又担心她们仍在那里。
五、結语
写作是乔利生活的中心,乐趣之所在。虽然乔利的写作生涯停止了,但其对强权文化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对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建设人类的未来都十分重要。生活的坎坷和创作的艰辛使乔利获得了对生活新的认知视角,并在多部小说中展现了弱势群体的困惑与危机。疗养院里的音乐教师斯科比先生;瘫痪在床的作家霍普威尔;生活得不到保障的作家博奇;事业、家庭面临双重危机,被排挤、被边缘化的埃德温教授等都是乔利笔下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是社会的弱者、他者、边缘人,是需要社会关注的群体。乔利将社会上备受忽略的弱势群体的尴尬、痛苦与无助展现在读者面前,并通过作品批判了以剥夺和毁灭为特征的强权文化,提高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赞扬了弱势群体为获得平等权利所付出的努力,歌颂了他们为维护人性尊严和自由所彰显的伟大人性光辉。
[参考文献]
[1]梁中贤. 解读伊丽莎白·乔利小说的符号意义 [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Jolley, Elizabeth. Mr. Scobie's Riddle [M]. Ringwood, Victoria: Penguin Books, 1983.
[3]萨特.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M]. 伦敦:新左派书社,1974:13.
[4]Andrew P,Riemer.Between Two Worlds- An Approach to Elizabeth Jolley's Fiction[J].Southerly,1983(3):239252.
[5]丁威. 伊丽莎白乔利的创作世界与审美意蕴[J].北方论丛,2017(6):5458.
[6]张荣升. 伊丽莎白·乔利小说的作家危机书写 [J],学术交流,2017(6):208212.
[7]Elizabeth Jolley. Miss Peabodys Inheritance[M].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3.
[8]Thomas M, Disch.Bound,Gagged and Left in the Party[J].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84(11):14.
[9]周忠厚.文艺批评学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422.
[10]丁威. 伊丽莎白·乔利小说中作者与读者的动态互助[J].学术交流,2018(4):182187.
[11]晓树.思想家论人的情感[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171.
[12]Elizabeth Jolley. Foxy Baby[M]. Boston: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4:254.
[13]张荣升. 论伊丽莎白·乔利对学院派小说的继承与发展[J].外语教学,2016(2):7881.
[14]Elizabeth Jolley. The Sugar Mother[M]. Western Australia: 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 1988.
[责任编辑]甄欣
Challenging Hegemony, Pursuing Human Dign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Australian Female Writer Elizabeth Jolley's Novels
ZHANG Rongsheng1, DING Wei1,2
(1.School of Western Languages,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Mudanjiang,157011,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Due to her rough life experience and hard writing career, Elizabeth Jolley has a deepfelt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Mr. Scobie's Riddle criticizes the hegemonic culture represented by Big Nurse and reveals the survival crisis of the elderly group represented by Mr. Scobie; Miss Peabody's Inheritance focuses on the writer's vulnerable state and praises Mrs. Hopewell, a writer who is handicapped but perseveres and inspires her readers immensely. Foxybaby focuses on the weak state of young intellectuals and publicizes the hard work for freedom and ideals by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The Sugar Mother focuses on the dilemma of middleaged Professor Edwin and analyzes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modern intellectuals being marginalized in their feelings and career. Jolley focuses on and raises people's concerns about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challenges the concept of hegemony through many novels, while praising the efforts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to pursue equality and freedom, defending the dignity of the humanity, and demonstrating the ethnic tension and morality beyond the living consciousness and equal dignity.
Keywords:Elizabeth Jolley;disadvantaged group;hegemony, human dignity;intellectu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