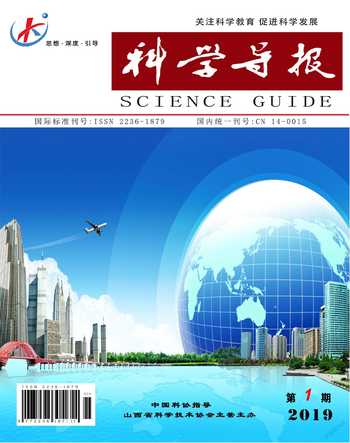“礼异乐同”的内在结构与一致性探析
2019-09-10耿苏鑫
耿苏鑫
摘 要:礼乐制度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其重要性不遑多让,在整个儒家理论中具有支柱性意义。然而礼乐制度并非单纯一整套“死”的典章制度,其内蕴着的礼乐精神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哲理价值。“礼异乐同”便可以视为对礼乐文化的浓缩性概括。“礼者为异”,礼乃是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外在秩序,“乐者为同”,乐则是通过个人修养以达到群体共鸣的内在手段。礼与乐虽然有着本质、功能、范畴上的差异,但礼与乐同时又具有内在一致性,它们通过内外之分、同异之别相辅相成,紧密相连地共同塑造着礼乐精神,最终达到上达天道,下感民心的教化意义。
关键词:《礼记》;礼“异”乐“同”;内在一致性;礼乐教化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选择的“救世之道”仍是试图恢复周代礼乐制度与上古圣王之治,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试图通过个体内在的修身立德和建构起一整套倫理道德体系以谋求天下大治,结束混乱的时代现状。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里,有如“仁”、“诚”、“中庸”等极为重要的理论概念,但在维系社会稳定秩序的过程中,起核心纽带作用的,仍是自三代时期便传承下来的礼乐制度。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实际上儒家思想正是发轫于上古圣王手中,而儒家之精义也暗含在自尧舜至周公所建立的一整套礼乐文化之中,孔子所起到的作用乃是传承这套礼乐文化并发扬成系统的理论学说。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华夏民族的先民们通过对天道人心的领悟确认创造礼乐制度,故礼乐制度有修身养性、同化民心、上达天道的多层次教化意义。而礼与乐虽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但其最终目标仍是一以贯之的。本文便试图梳理以“礼异乐同”为内核的礼乐文化的内在结构,考察“礼”“乐”各自的功能作用,通过比较分析来厘清二者的定位范畴,同时试图说明其二者内在的高度一致性,以对礼乐文化做进一步的整体理解。
一、礼:以血缘纽带为核心的社会伦理秩序
《礼记》中记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在创立之初的目的就在于“定亲疏”、“别同异”这些差别性概念上面,无论多么复杂的礼仪,其制定实施都是为了群体间产生“别”和“异”这种身份类型的不同,使人产生一种对自身以及他者身份地位的确认,继而达到“各安其分”的认同感与稳定秩序。简单来说,儒家伦理就是一种从“自我——家族——社会——天下”的同心圆的不断扩大,以血缘纽带为核心确立远近亲疏的不同,从而形成伦理关系,而要维护这个伦理关系,就要靠礼制。礼制创立之初的直接目的,乃是试图在周代分邦建国背景下建立起一种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当然这个所谓“等级”并非今日理解的封建压迫之谓,可以看成是符合当时历史形态的“圣王之治”,其本质意义在于寻求社会的普遍秩序。故从本质上说,“礼”乃是一种对于群体生活带有普遍原则的伦理规范,它创造某些外在的社会规范形式,将人们的言行纳入一定的范式之中,以稳定秩序来保证整体社会的良性运作。而在轴心时代文明中,并非只有中华土地上孕育出这种思想,譬如古希腊柏拉图对于理想国家的构想,也是从对城邦中分工的不同而将公民划分为三个等级——生产者,护卫者与统治者,最终通过三个等级之间分工合作各安其份的秩序关系,来形成稳定繁荣的城邦以达到全体公民的普遍幸福。
所谓“大礼与天地同节”,礼的起源也并非由古代圣王凭空创作,而是通过对天地人心的观察来制作礼乐,所以礼乃是一种符合天道、与天地相同的自然秩序。“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礼的制定是为了人们节制自身的欲望,礼具有抑止邪念、引导人心复归中和本性的作用。同时,尽管礼作为一种外在规范,但儒家的“礼治”理想与“法治”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更注重对人心内部的教化意义,从根本上去除邪念。故《礼记·经解》说:“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在儒家看来,如果邪恶已成然后使用刑罚以止之,那便是法治,并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整饬人心,这与儒家理想中的礼治教化大相径庭;只有借助于礼乐这一教化手段,才能在源头上使人“徙善远罪”,进而实现礼治主义的政治理想。
二、乐:发于人心以达到群体和同的内在共鸣
实际上儒家经典并不只有“五经”之说,还存在着《乐经》这第六部经典,只不过在历史的演进中早已亡佚,但这已充分说明“乐”和“礼”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过现今保留的《礼记·乐记》一篇仍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乐”的起源作用,并对礼乐关系作了深刻的比较总结。“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起源于人心情感,心受外物的感发萌动形成声音,各种声音应和变化才形成歌曲,而对歌曲再进行演唱加以舞蹈的才能叫做“乐”。这充分说明“乐”在上古时期的严格定义,“乐”的内涵并非今日之流行理解,也并非所有的“声”和“音”都能叫做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乐的根源乃是人心有感于物,从而发出的真挚之声,有什么样的感情则发出何种声音,继而形成何种“乐”。“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同时“乐”与“声”、“音”等概念有着本质区别,存在着“声”、“音”、“乐”三个逐渐递进的层次。乐既发于人心故有通伦理之功效,动物和一般的民众并不能够掌握“乐”,他们最多理解“声”和“音”,只有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君子”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乐”。君子还能通过对乐的理解进而懂得政教,乃至达到完备的治国之道。由此观之,乐和礼在严格内涵下都具有博大丰富的外延属性,都有“教民平好恶,反人道之正”的强烈教化功能。
我们还可再进一步探讨乐的起源。《礼记·乐记》有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里已经已将对乐的起源的探索上升到了极高的哲学层面,直接从对人之本性的阐释进而剖析“乐”诞生的文化土壤,如同《中庸》中对“天命之谓性”的精辟论述。人之生的本性乃是处于一种无情欲的“静”的状态,这正是天所赋予人的本性,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阐释的也是这种人之本性处于无所偏倚的中间状态;唯当受外物之影响方能产生情欲,这是由于性的欲望所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之为节”,乐的作用就是当人们已经产生情欲时,通过节制的方式引导人们走向“和”的境界,这便是“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乐之起源于人心,其目标也在于节制人心,而且就“礼”乃是以外在秩序节制人心来说,乐作为一种内在修养,其更能从根本上引导、节制人心,故有“致中和”的化育功效。
有关乐的功能价值,《乐记》中还有诸多精辟之言。譬如“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和谐而不丧失原则,是乐的精神;使人欣喜欢爱,是乐的功能。乐之功效精髓就在于一个“和”字,在礼制实行的社会等级背景下,一昧地强调“别”和“异”的不同身份,可能导致群体的过度疏离与社会的阶级撕裂,而加入“乐”的元素,则能够使人们恰如其分的保持和谐又不丧失差别,亲爱又不丧失节制,使在秩序的建立过程中真正达到和谐的中庸式良性平衡。故从总体上看,“乐”起源于人心,为人情之所共有,其就能够作为一种内在教化方式而达到群体的普遍共鸣,这种共鸣以“和”(同)的形式呈现,最终促使人们通过陶冶内心情感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将礼制转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
三、礼异乐同
上文已较为具体地阐释了礼和乐各自的起源、功能以及本质,下面我们的重点仍在于对“礼异乐同”内在意义的梳理探索上。《礼记·乐记》中明确有言:“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这段记载已直接反映出礼和乐的目的功用以及相互关系。礼的目的功用乃是“异”,亦即在人们之间起到区别的作用,礼的区别作用能够使群体保持尊敬,从而形成良好的秩序感,但如果过分强调礼的差异就会使人们产生疏离;故而有与礼相匹配的另一端——乐的目的功用在于“同”,乐则在人们之间起到和同的作用,乐的和同功效能够使人互相亲近,在群体成形成友爱一致的氛围,但同时过分强调乐的和同也可能让人们过于随便而缺乏敬意。所以《乐记》的此段记载继续说道:“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則上下和矣。”由此看来,礼与乐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对于调和社会关系、改善人心具有密不可分的互生关系,它们可被看做一枚硬币的两面,具有辩证统一的哲学蕴意。再结合上文,我们便可以对“礼异乐同”的内蕴做一个大致的判断了: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目的正在于“异”,为了使人们之间有所差别区分,从而保持一种等级差异的外在秩序;乐,作为一种内在修养,其目的正在于“同”,通过个人的内在修身以达到群体的普遍共鸣,从而形成一种和谐友爱的氛围,最终达到“致中和”的化育功效。
以“礼异乐同”为代表的礼乐精神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还可视为“礼外乐内”。《乐记》有言:“乐自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与乐在领域范畴上有着显性的内外之别。礼是由外部的仪节所规定,其在社会外部向人做出规范制约,使人在外观言行上有所表现;乐则是从人的内心本性发出,直接在内部引导节制民众之心性,复归平静无欲之“中和”态度。故而外部的礼教达到了就没有纷争,内部的乐教达到了就没有怨恨。这深刻地体现着礼和乐对于治理国家社会的不同方面的不同功能。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礼乐制度在政治教化中的内外之别,实质上也意味着“礼”与“乐”分别承担起教化人们“身”与“心”的不同职责。礼更多强调对人们言行举止的外力约束,是对“身”这一外在条件的束缚;乐则注重对人们心灵的直接感化,是对“心”这一内在动力的引导。
而有关“礼异乐同”的深层内涵和本质起源也并非制作礼乐者们的凭空建构,如同上文我们阐释“乐”起源于人心人性,“礼异乐同”的关系同样起源于上古圣王对宇宙秩序的确认,对自然法则和人道本质的感化。“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古人认识到在自然世界中存在着天尊地卑的差异秩序,进而从对天地法则的考察推导出以“礼”为代表的人类社会的普遍规范,故“礼”具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种对社会的差别性区分特质;而天地二气融合互生、化育万物,故有以此为背景的“乐”的兴起,乐也就带有了“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的和谐特性,直指民心之内。所以《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最终,以“异”为内核的“礼”塑造出差别区分的社会秩序,以“同”为内核的“乐”营造着和谐化生的的群体氛围。以礼的实施来制造以血缘纽带为核心的社会稳定伦理秩序,以乐的推行来调和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冲突,达到感情上的融通,使整个社会进入一种融合稳定的良性平衡。诚如有研究者指出:“当礼乐两种手段运用相得益彰时,社会政治就能够达到“礼义立则贵贱等,乐文同则上下和”的理想境界,于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状况也就真正得以实现了。”
四、“礼异乐同”为代表的礼乐精神的一致性
尽管礼乐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以及社会定位、价值功能上的诸多不同,但归根结底,儒家思想向来是“一以贯之”的,礼乐精神也具有其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这里不仅将礼乐并列一起,而且纳入了政、刑这些更具有强烈外在约束力的法治规范,以说明它们的本质作用都是“同一”的,即“同民心而出治道”。礼乐政刑其各自适用的领域和功能虽大相庭径,但就最终目标和根本作用而言,都是为了整饬民心治理社会。尤其就礼乐制度而言,它们同属于儒家治国理政的内在教化手段,都属于从根本上解决民心问题的礼治主义范畴。所谓“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礼与乐尽管一主敬,一主爱,但其最终作用实际上一以贯之,爱与敬之感情也是合而为一的。因此,以“礼异乐同”为代表的礼乐文化,从具体形态上看,则有其各自功能作用之差别,具体的社会教化功效也相区分地适用于各自的领域定位;但一旦从整体处着眼,礼“异”乐“同”也凸显出强烈的内在一致性,无论是通过内在修养共鸣,还是外在秩序规范,其最终目的殊途同归,最终都是要在社会群体中找到一种“中庸式”的稳定平衡,在个体“各安其份”的同时不丧失社会整体的亲近一致性伦理导向,以谋求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目标。
在隐喻的程度上,当“礼”和“乐”相辅相成共同塑造出礼乐精神时,其通过内在一致性的升华以至拥有“大本达道”的天地化育功效,自三代传承下来的礼乐制度也就包含着无限增殖的文化意义。礼乐文化也就并不只作为社会治理之手段,而是成为比“治国平天下”更高一层的文化系统,其暗含着一种至高的价值观念——即指向文化(传统)的主体性地位,这种文化系统奠定着儒家的框架和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代表)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传统,而对于这种传统的传承正是儒家的精义所在,也是其一以贯之的终极目的。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 力行.儒家礼乐并举的治国方略[J].思维与智慧,2017
[5]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