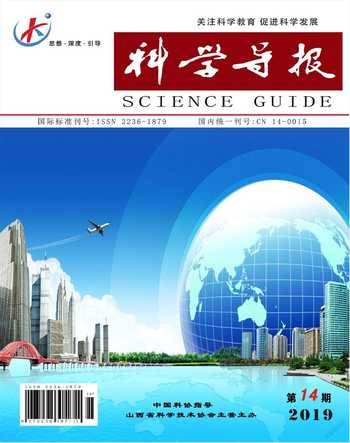《竹林》的静寂,《萧萧》的偶然
2019-09-10赵丽
赵丽
摘要:废名与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认为是有着近似风格的两个小说家,同样的淡化情节,同样的诗意,但是他们对人事的态度却是迥然不同的,废名的清净带有的是一种对人事的冷漠,有一种拒绝的尘世的独立。而沈从文的清净中有着热闹的一面,有着更多的人间烟火气,在一种必然之中处处显现出偶然的痕迹。而这种不同在《竹林的故事》和《萧萧》中最为突出。
关键词:《竹林的故事》;废名;《萧萧》;沈从文;静寂;偶然
废名与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认为是有着相似创作风格的两位小说家。他们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以情节结构的淡化、环境气氛的渲染、人物形象的白描、诗性的孜孜以求赢得了读者的青睐。尽管他们的创作倾向与风格大体一致,但在细微处却还有着各自的异同。从整体风格上来看,沈从文所迈的步子是温文尔雅、自然无雕饰的,其以湘西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总笼罩在如同那一片经久不散的烟雨朦胧般的温柔、热情且必然中又有着偶然的凸显,《萧萧》便是这一风格的最佳体现。而废名的足音多少有些冷漠、寂寥且一切顺其自然,他的作品即便是抒写田园风光也“以冲淡为衣”,较为“闪露”,《竹林的故事》便是这一风格的最佳体现。
《萧萧》给我们展示的是一幅不着色彩的淡淡的湘西山村的山水图,平平常常的山和水,一代又一代似乎有规律而毫无波澜的生活,没有浓烈的色彩,只有春来秋走的时间如流水,只有春后一个秋的狗尾巴草、南瓜、毛毛虫、,山间无名的野花,,一切的事情都平常朴实得如同我们自己的生活一样,时间在悠悠的春秋中走了又来,只是这个时间中有着自然的必然,却有着小小的偶然的波澜。作者取人物唇吻间的话语,简单自然的举动,天真在眉目言动之间流露,这萧萧如她所在的那一片碧水,任情而无所顾及的流淌着,即便偶有思虑也是山川草木的问题,小说在写了十二岁:萧萧过门(交待其童养媳的生活内容),夏夜乘凉,祖父戏说女学生,萧萧的女学生之梦的产生;十三岁:秋收摘瓜,花狗挑逗,情欲初萌;十五岁:春日野合怀孕,逃跑未遂,生子被恕;十年后:圆房,生次子,为大儿娶童养媳;在《萧萧》中,时间体现出的结构和功能意义尤其明显。因为每一个时间对应着萧萧独特的一段生命景观。不仅如此,文本中的季节还具有深层的隐喻意义。小说中每一个季节对应着一个萧萧生命中的特定事件。如春的万物滋生对应着萧萧与花狗的野合;冬的调零、空芜对应着萧萧童年期的提前完结以及最后萧萧情欲和梦的消失。而四季的循环往复又象征着一个固定的、封闭的生命结构模式,即萧萧这个符码所代表的乡间女子的整体命运模式,因而,沈从文笔下的人与自然的节律是相宜的。作者在这种纯净中体现着人即自然,自然即人的一种相融。
翻开《竹林的故事》,尽管是精简、朴素的两三句描述,却呼之“已”出的是幽幽竹林园的自然、美丽、清净。“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作者尽管只用了“河”、“竹林”、“茅屋”、“菜园”等几个简单的词汇,却勾勒出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图景,传递着恬静清幽的温馨,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林里的竹子,园里的菜,都一天一天的绿得可爱”。“雨之后,河里满河山水”。“因为太阳射不到这来,一边一颗树交阴着成一座天然的凉棚,水涨了,搓衣的石头沉在河底,剩现绿团团的坡,刚刚高过水面,废名所描写的大自然,尽管处处是小桥流水、疏林修竹、桃红柳绿,但没有骚动,没有风波,人与自然尽管交织汇融,回归到浑然一体的原始之初,但作者并没有寄情感于自然万物中。所以,在《竹林的故事》中,人与外界、心灵与自然产生了距离,他们彼此独立,因为作者的内心早已皈依自然,所具备的是超然尘外的自然人格。书中对与老程死了以后是这样说的:“然而那也并非是长久的情形,母子都是那样勤敏,家事的兴旺,正如这块小天地,春天来了,林里的竹子,园里的菜,都一天一天的绿得可爱。老程的死却恰好相反,一天比一天淡漠起来。”人物的内心与环境是相互独立的,人的生死与自然是自成一格的,自行其道。
沈从文专家凌宇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中,提到此篇小说是“常与变交织,必然与偶然错综”,并认为萧萧面对许多“偶然的因素”,包括:出现过一个读过“子曰”的人;有人家买萧萧;生下的是儿子,他的结论便是:“情节的发展指向一个明确的思维方向:萧萧这类善良、纯朴的山村儿女,生命在一种无法预测其结果的人生浪涛里浮沉,任何一种偶然的因素都可能使她们的人生命运改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无可否认的偶然与变数并没有影响整个生命循环的自然规律。乡下人生活中不断出现的“规矩”,即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礼法制度,或者称为“偶然”和“变数”,同样也不曾禁锢他们善良的心灵。小说中萧萧的失贞、怀孕是犯了滔天大罪的事情了,它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这个必然的出现在其他作家那里绝对是重笔,会以血、泪、火来体现,但是在文中却出现了一个“子曰”的伯父决定发卖而不是沉潭,然后生了一个“团头大眼”的男婴,“大家把母子而人照料的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一家子都喜欢那儿子。这个男婴长大了叫萧萧的丈夫‘大叔’,‘大叔’从不生气,并让男孩长到十二岁时照样给接了亲”这样一个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在萧萧的小丈夫嘴巴里唱着花狗教的情歌时,我们可以预料到萧萧与花狗会发生故事,这是常也是人性中的必然性,但是当这件事情就这样顺其自然的落幕的时候,一种人生偶然就在自然中融化了,一切的不合理都在它自己的規律之中合理了。这就是沈从文的静,他的静不是死寂,有着最贴近生活的原来面目,热情中有波澜,只是这种波澜并不会打破生活原有的平静,沈从文的小说有水的色彩,透明澄净,却是流动的,有着小小的跳跃,最后有静静的流到它应该到的位置。
废名的小说《竹林的故事》则是波澜不惊,是一潭死水,承载的生活没有烟火人心,是所有的东西都在静静的流淌,连爱怜都是如风的清新,带有失音的鞋印。三姑娘的爸爸不知不觉地死了,“绿团团的坡上从此不见了老程的踪迹”,一笔带过。这种风格若以诗比,则近于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那份淡雅;若以画比,则近于元四家之一倪云林那种地老天荒似的寂寞的美丽。小说的叙述者是带着爱恋的对三姑娘但是却处理的波痕都没有一点。对三姑娘的回忆是从“我”十二年前的读书生活开始的。“我”曾经在那个村庄的私塾读了六年书,那段时间也正是“我”的青少年时期。然而在十二年后“我”还对一个乡村少女如此念念不忘,可见,当时作为一个青年男子的“我”对三姑娘所产生的特别情愫。最初的“我”作为回忆者以全知角度叙述的只是三姑娘在河边嬉戏、帮爸爸捉鱼的欢快场面,以及三姑娘一家温馨的生活场景,那时的“我”也只当她是一个小孩子,常常借割菜来逗她玩笑。在此,他们之间的情感只是纯洁无邪的童真童趣。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三姑娘己经长成一个十二三岁情窦初开的少女。他们之间也开始形成了男女两性世界的对立,三姑娘也处于“我”这位男性目光的追寻和看视之下。在“我”眼里,总觉得“见了三姑娘活泼泼的肩上一担菜,一定要奇怪,昨夜晚为什么那样没出息,不在火烛之下现一现那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样的面庞呢?”由此可见“我”对三姑娘是有着爱慕之情的。当三姑娘多抓了一把青椒给“我”,我取笑她将来碰上一个好姑爷,而她却害羞地逃走时,可见三姑娘对我也是有着绵绵情意的。然而“我”还是“我”,既不敢向她表白,也不敢向她求爱。只是将这份爱存入心底,直至一句“从此我没有见到三姑娘”道出了后来自己对她的思念与惋惜,并最终让“三姑娘低头过去”平淡地完成了“竹林”里的这个“爱情故事”,似有若无,没有什么热情,没有偶然和波澜,岁月无声的流失中什么都走了,没有怨,没有恨,只有岁月如歌。
废名是坐在柳荫下,平静悠然地看着人间景致的,而沈从文则是划着一张桃源筏子,雄浑地前进有风有浪更有生命的激情。他们都在构建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然而他们所站立的姿态不同,一个是孤独的、缺乏斗志的,而一个却在描绘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时,一个是在他的“竹林世界里封闭自我,来逃避现实世界而寻找自身的,而另一个是以一个有追求、有爱心、有理想,希望人们爱自己,也希望人人爱别人的形象出现的。曾经,沈从文将自己与废名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废名“所显示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细微雕刻……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对宇宙光色的眩目,有爱有憎,———但……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而认为自己“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一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沈从文在人间生活,废名在真空中生活。
(作者单位:昆明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昆明市中等职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