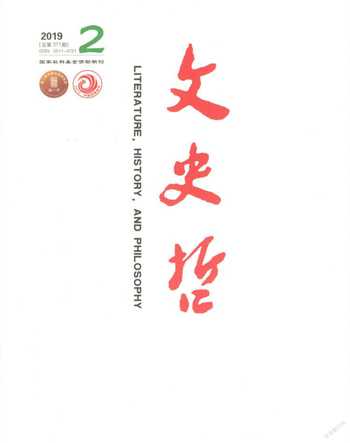《竹书纪年》与夏代编年:我对历史方法的反思
2019-09-10夏含夷
1923年1月27日,倪德卫(David Shepherd Nivison,1923-2014)生于美国缅因州法明代尔。1940年进入哈佛大学,准备学习古典,然而他的学业被太平洋战争打断了。倪德卫在战争期间服务于美军情报部门,学习了日语。1945年战争结束,倪德卫回到哈佛,次年毕业,取得了东亚研究(重点是中国历史)的学位。1948年,他开始在斯坦福大学教书,直到去世。倪德卫最初研究思想史,由章学诚(1738-1801)上溯宋代思想家,再上溯孟子(公元前372-289 年)。1970年代,他试着阅读商代的甲骨文,关注点遂转移到更早的时代。
我与倪德卫初遇于1978年,那时我是斯坦福古代中国研究专业的研究生。一年后,我上了倪德卫的西周金文研究课。倪德卫后来回忆,一个周日的晚上,在他准备教案时,他“发现了难以置信的事,它成了我余生研究的主题”。这项研究最初仅针对四年前在陕西扶风庄白发现的微氏家族铜器,但最终扩展到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竹书纪年》不是伪造的,而是无价的史料”,其次是他可以精确重构从夏代开始的中国上古纪年。他说“第二天晚上的讨论会令人激动” [ David S. Nivison, 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 Taipei: Airiti Press, 2009, p. 8.]。讨论会确实令人激动,同样令人激动的是他接下来三十五年的研究生涯,在此期间,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主要方面,他还研究了其他关于上古中国历史编纂和纪年的论题。
倪德卫以他此后三十五年重构《竹书纪年》的原始文本并以此重构整个上古中国史编年而著名。他的研究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早了十五年[ 倪德卫关于这一主题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他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刊行的长文“The Dates of Western Chou”。二十六年后他出版了对《竹书纪年》最详细的研究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参看注➀)。此书的中译本《〈竹书纪年〉解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在他去世后出版。他的未刊论文集The Nivison Annals: Selected Works of David S. Nivison on Early Chinese Chronology, Astronomy, and Historiograph (Berlin: De Gruyter, 2018)随后结集出版。],在很多方面比断代工程更有雄心,在某些方面比断代工程有更长久的价值。他比这个国家资助的大项目投入了更多的时间,也期望更大的成果。倪德卫探索了中国古史的许多不同方面,思考它们需要再来一个国家项目。然而,因为本笔会的主题是探讨夏代纪年,所以我们可以只考虑他重构夏代纪年这一点。我与这一研究有密切关联,尤其是倪德卫最后的一些思考,我要对它们做出回应。
倪德卫声称他解决了夏代编年问题。在早期的研究中,班大为(David W. Pankenier)证明公元前1953年二月发生了五星连珠。倪德卫假定这一天象标志夏代的开始,他注意到公元前1953年在《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代元年——公元前2029年的76年之后。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76年为一蔀,倪德卫因此假定某个文本编辑者将76年额外的材料插入文本。接着他和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一个天文学家、业余历史研究者彭瓞钧(Kevin D. Pang)合作,确定了《尚书》中记载的著名的“仲康日食”发生于公元前1876年10月16日。根据这些天文现象,倪德卫发展出了一套异常复杂的关于整个夏代纪年的论证。他的论据是他自己重构的《竹书纪年》,而他的重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依次为:1.夏代君主以即位元年首日的天干为名;2.夏代君主之间的不规则间隔(零、一、二、三、四年以及一次四十年)通统应是两年;3.末代君主桀完全是虚构的。
倪德卫在《〈竹书纪年〉解谜》中充分阐释了他重构夏代纪年的企图。他的论据包括天文学(见上文);文本考据(尤其是对《竹书纪年》);以及相当多的对历史编纂的猜测(他考虑到了夏代和战国时代的情况,认为《竹书纪年》在这个时代遭到多次修订)。介绍他的论证最公平的方法莫过于引用他自己在《〈竹书纪年解谜〉后记》中的简明论述[ David S. Nivison, “Epilogue to 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53 (2011), pp, 17-18.该文是对我写的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的长书评的反驳,下文中我会提到我的书评。]。在下面的一长段引文中,我仅删去了我认为无关紧要的说明以及四条脚注(文中提到年代都指公元前):
《竹书纪年》中开始于我假定的原始年份的纪年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我认为《竹书纪年》中夏代君主的在位时间是准确的,而他们之间的间隔通统是两年(前任君主的丧期)。战国时代的某个时候,也许是在鲁国(因为尧的元年从2026年推前到2145年,该年是鲁国闰历中的蔀首,而商的元年仍是1589年,该年是从1554年前推而得,但在帝癸的在位时间被发明之前),夏代纪年被改造以使原来从1989年禹取得“法理上的”(de jure)王位開始的十六个王的在位时间加起来恰好等于四百年。
“实际上的”(de facto)夏元年(舜十四年舜把权力转交给禹)从1953年前移了一蔀76年到2029年,得出了《竹书纪年》的夏积年——471年。头四十年(到舜五十年,然后是舜的丧期)被算做禹“实际上的”在位年份。于是禹“法理上的”在位八年变成了从1989年开始。(从这里开始,把这些年份当做固定的。)
同时,A类的圣王尧、舜、禹的丧期由两年增为三年。既然舜在禹“实际上的”在位期间去世,那么夏就增加了两年。作为补偿,第二个君主启的丧期(临时)由两年减为零年。
第四代君主仲康的日食推前了一个蔀(76年,配合夏元年的改动)。如果日食的正确日期——夏历九月一日——在1876年,它必须被推前到1952年。但这一年的九月朔太阳应在房宿(《左传·昭17.2》)。这一年份需减去一纪1520年验证,结果是432年,验证失败。432年之后第一个通过验证的年份是428年,该年(夏历)九月朔是庚戌(47)。(该年有个闰八月,所以张培瑜的十二月是夏历九月)。所以《纪年》选定的年份是428+1520=1948,日期是庚戌……移后这四年需要在《纪年》中此前夏纪年的某一点插入四年。启后的“零年”间隔正满足了需要,于是启与嗣君的间隔变成了四年——《纪年》夏纪年中唯一的四年间隔(这一结果与彭瓞钧的日食日期——1876年10月16日契合。)提前的年份现在减少了四年,由76年变成72年。
相之后寒浞的四十年间隔被发明出来,以代替两年的间隔,用来填充推前的七十二年中剩下的三十八年,将它减少为三十四年。
这使得从禹“法理上的”在位开始到第八任君主芬的丧期结束的时间变成202年。因此,芬的两年丧期被取消,推前年份增加到三十六年。于是夏代前八个君主分配到了两百年,如此则后八个君主也被分配到了两百年,使1789年变成第九任君主芒的元年,而1589年变成了商元年。
第十一任君主不降之后被插入两年间隔,忘了他是退位的。这使推前年份再次下降为三十四年。从1589年往回数,会发现后八位君主(芒到发)包括间隔有201年;于是第九任君主芒后的间隔从两年减为一年。这使推前年份增加到三十五年。
接着,不降后的两年间隔被注意到不应添加,于是就被取消了,而不降前后的君主(泄和扃)的丧期(即间隔)从两年增加到三年,以与之前的年数一致。
这篇《〈竹书纪年解谜〉后记》是被我在同一本期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发表的书评[ Edward L. Shaughnessy, “Of Riddles and Recoveries: The Bamboo Annals, Ancient Chronology, and the Work of David Niviso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52 (2011), pp. 269-290.]激出来的。在书评的开头,我评估了他广为人知的西周君主用两套历法的理论——一套从前任去世后的一年开始(新君“立”),一套从前者的两年后开始(新君“即位”,可能是完成了三年之丧)。我认为这一理论很可能是解开西周纪年之谜的关键。然而,我接着批评倪德卫将这一理论从西周推前一千年用到夏代——文字记录出现还要好几个世纪呢:
不幸的是,在我评论的这本书中,我认为倪德卫将一个好想法“超负荷”使用了。他把这种历法实践从西周前推一千年到夏初。当然,这一时代别无文字记录,支撑倪德卫主张的唯一根据是一直背负伪名的《竹书纪年》。倘若有证据表明《竹书纪年》的这些部分确合史实,那么它可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这样的证据确实存在于《竹书纪年》中。只有部分在位时间提到之前有间隔,有时是一年,有时是两年,有时是三年——如倪德衛所注意到的,“大约三分之一是两年”。从这点出发,他断言“认为所有的间隔都是两年应是合理的”。为什么是“合理的”?实际上,我认为更“合理的”说法是早期不规则的间隔规则化了,但这需要时间。对我来说,没有任何证据(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文本)能支持倪德卫的假设。倪德卫认为还有其他证据支持它——他重构的夏纪年需要用到规则的两年间隔。很明显这是循环论证,即便如此也不需要倪德卫去论证夏的末代君主、恶名昭彰的帝癸或桀“是虚构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君主”。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包括了这位君主三十一年的纪年,但倪德卫说他重构的文本说明这些是后来插入原始文本的(显然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魏襄哀王时插入的)[ Shaughnessy, “Of Riddles and Recoveries,” p. 274.]。
下面我还要整体上说说《竹书纪年》。现在我仅对两点作进一步说明:关于夏代君主之间的间隔和末代君主桀的编年。从大禹的儿子启到桀,《竹书纪年》包括了十六位君主。他们之间的间隔如何,文本说的不是很清楚。然而,联系插入文本的每一位君主在位元年的干支名和他们死时记载的在位时间,我们可以计算出他们在位时间的间隔如下:4,2,2,40,2,2,0,1,3,0,3,2,2,2,0。因此,十五次王权转移中有七次的间隔是两年,比倪德卫所说的“三分之一”多。尽管如此,八次转移中要么压根没有间隔(三次),要么有一、三、四、甚至四十年间隔。我仍然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说所有的间隔都正好是两年;没有任何文献支持此说,我认为倪德卫在这一重构上师心自用了。至于说桀“是虚构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君主”,在我看来这是倪德卫对史料更专横的干涉。我相信我们所看到的关于桀的零星史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传说,但《竹书纪年》中桀的编年与其他编年没有本质的区别。删去他在位的三十一年,除了满足倪德卫夏编年的需要,还有别的根据么?
很明显,倪德卫被这篇书评刺痛了。他在《〈竹书纪年解谜〉后记》的结论部分详细罗列了他对我的书评的直接回复如下:
所以他说:“倪德卫做了这么多研究,怎么仍然错得如此离谱?”他把自己抬到了历史学圣人的地位:他“确信”这样,“确信”那样[ 倪德卫在此添加了一条脚注:“夏含夷坚持说是‘我’太自信;这让我不怒反笑。”],“认为”这样,“认为”那样,宣判我的整个先周编年无效(没有对具体细节的批评,他断定我错的唯一论据是因为我的答案“是建立在(我)重构的《竹书纪年》上的完整系统的一部分。”[ Nivison, “Epilogue to 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 p. 15.]
这一批评针对的是我书评末页后的一节。我支持它,而且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确信”——我没有把自己抬高到“历史学圣人”的地位:
尽管《〈竹书纪年〉解谜》有诸多贡献,我在这篇书评中对此书仍持(可以说是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倪德卫做了这么多研究,怎么仍然错得如此离谱?我认为答案很简单,他想要做的太多。他试图说服自己,他为我们重构的文本是完美的(想想他的《引言》:“现在我明确地知道前七分之五的原始文本上的每一个字,共303简。”。我对《竹书纪年》下的功夫不亚于倪德卫,但我不确定文本是否像他确信的那样。另一方面,我确信,而且十分确信,我思考的事有些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不知道倪德卫包括进文本的注释中的大部分是否在出土时已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是否和编年一起写成(不论是什么格式);叙事部分或许如此,但我十分确信解释性的注文是西晋编辑者添加的。我不知道原本有多少毁坏或散佚,但我确信至少有一部分——包括倪德卫重构的七分之五中的一部分——已湮灭无存。最后,我也十分确信,西晋编者在编辑过程中至少犯了一些错误——有些是遗漏,其他则是逞臆私改,制造一些出土文本中所无但符合他们对上古史的认识的简文。如果我对《竹书纪年》和它流传的种种没有把握,那么我是不会相信在相对简单、不相关联的段落组成的文本以外的任何重构。我当然也不会相信倪德卫的重构是可靠的[ Shaughnessy, “Of Riddles and Reconstructions,” p. 289.]。
在此只有一處我伸张了自己的权威,像倪德卫一样,我也对《竹书纪年》做了大量研究[ 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amboo Annal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6.1, 1986, pp.149-180. 该文后译成中文《也谈周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文史》第29辑,1988年,第7-16页。更广泛的研究发表为《〈竹书纪年〉的整理和整理本》,蔡国良、郑吉雄、徐富昌编:《出土文献研究方法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339-441页。该文英文稿也收入我的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6)一书。],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文本有三点毋庸置疑:
“解释性的注”——如“芒或曰帝荒”——“是西晋编辑者加上去的”。
在墓葬发掘时,“至少有一部分简文遭到破坏或散佚”,同时代人的墓葬发现记录中有很清楚的证据。
“西晋编者在编辑过程中至少犯了一些错误”,可由各种中古史料中引用的《纪年》异文证明。
尽管这么做被人批评,我仍然“确信”这三点是正确的。至于我不相信“在相对简单、不相关联的段落组成的文本以外的任何重构”,我很乐意有人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但我怀疑新的《竹书纪年》简文出土的可能性都比根据现有文本令人信服地重构一个公元279年从汲冢盗发的《竹书纪年》大。
根据倪德卫的说法,我们的分歧在《竹书纪年》、尤其是在上古中国的编年(特别是其中的夏代编年)上的分歧源于我们在哲学上的不同,更甚于在文献研究上的不同。在他去世后出版的The Nivison Annals: Selected Works of David S. Nivison on Early Chinese Chronology, Astronomy, and Historiography,有一章题为“The Nivison-Shaughnessy Debate on the Bamboo Annals (Zhushu Jinian)”,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
实际上,我们之间的辩论在哲学层面上非常有趣。夏含夷发自肺腑地相信培根的(Baconian,译者按:指归纳推理)历史方法,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对其他方法不屑一顾(他自己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则遵循科林伍德(Robin G. Collingwood)的“反思”(Rethinking)和波普尔(Karl R.Popper)的证伪主义,对整体证据进行“最佳解释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夏含夷受不了,认为我的论证超出了我掌握的史料范围[ Nivison, The Nivison Annals, pp. 614-15.]。
倪德卫在他的《〈竹书纪年解谜〉后记》中已经提醒读者注意他“最佳解释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的方法:
在拙著(第3–5页)中我回答,在他反对的论点中,我其实是在将多种初始可能性较低、但在一个值得证明的整体结构中处于兼容状态的事项有逻辑地结合起来——只要其中的一些因素以实证为基础,这种兼容性不可能是偶然的。他反对我提出的夏代君主之间有2年的规则间隔,认为间隔应该是不规则的。他这么想只能说明他没搞清楚:我的论述结构是先假设再证实,而2年的间隔期是我假设的一部分。
那么,如何看待夏含夷所指循环论证(他认为我用两个 “未知因素”:编辑过程和所谓真实的年份互相证明,因而结论无效)?我已经证明了它们;但一开始我是把它们作为假说提出的。它们必须互为假设;否则我的假说将不一致,导致在在进一步论述前犯错。夏含夷将我的假设必须的连贯性和所谓循环论证混淆了[ Nivison, “Epilogue to 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 pp. 14-15.]。
回到夏代君主之间的不规则间隔问题,我反对倪德卫将所有的间隔修正为两年根本无关合理与否,我反对是因为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文本里间隔是不规则的。如果遵照文本就是“培根的历史方法”,那么我很乐意和这位真正的圣贤持同一立场。我也略懂假说,但我认为假说需要新的证据证实(证据不能在此前用于建立假说,然后再来检验假说),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则要由中立的第三方再现同样的结果。据我所知,迄今没有新证据能验证倪德卫的假说,也没有第三方能重复其结论。因此,倪德卫关于夏代纪年的假说仍然是假说。不管它如何“前后一致”,这种连贯性无法达到证实它的高度。
让我来引用倪德卫的文章“The Nivison-Shaughnessy Debate on the Bamboo Annals (Zhushu Jinian)”的结论部分结束我在《文史哲》夏代笔会上的文章吧:
夏含夷行动前应该考虑代价。但他没有,因为考虑代价必须接受这样的准则:相关的事至少应该有一以贯之的解释,即便事实上还没有。他不打算这样做,也没法容忍其他人这么做。我给了他一份简报,其中提供了夏初君主纪年的证据;我出书研究夏、商编年的变化;他都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这些事不能做。所以他问:“倪德卫怎么错成这样?” [ Nivison, The Nivison Annals, p. 654.]
如果我对“提供了夏初君主纪年的证据的简报不以为然”,部分是因为我认为这些证据不能支持这份编年,事实上也不能支持任何夏代编年。很可能将来会发现新的证据,提供解决这一谜题的关键,我热切盼望着这一天。唯一的遗憾是倪德卫在2014年去世,不能再投身其中。
(程羽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