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知青”书写与文化“寻根”
2019-09-10汪晓慧
汪晓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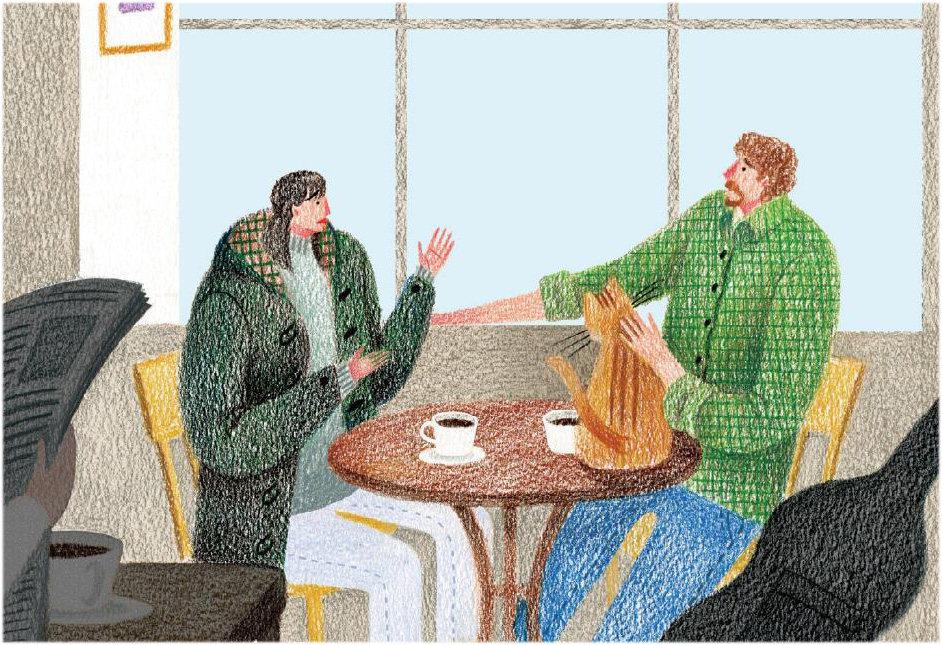
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坛风云变幻,涌现出了几股强有力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或称“文化寻根”运动,便是其中之一。不同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学习西方经验为启蒙手段的文学传统,亦迥异于延安延续下来的以工农兵审美取向为主导的革命文学传统,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包含着一种具有反叛意味的文化主体重建意识: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倾向于挖掘其中的积极因素,并对其作现代性的转化。
《棋王》是作家阿城登上文坛的处女作,也是“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
故事讲述了“文革”时期的知青“棋呆子”王一生四处寻找对手下棋、拼棋的故事。小说抛弃了知青小说惯常的阴郁灰暗色彩和“文革”时期惯有的语言逻辑,转而回归质朴真诚的生活和宋明小说的语境之中,富有朴实而飘逸的美感。正如王蒙所说:“《棋王》是那个特殊的时代对人的智慧、注意力、精力和潜力的一种礼赞。”
对《棋王》的解读要紧紧围绕其时代背景和文学语境来进行。作为读者,我们首先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本中去。阅读《棋王》,不仅要看到作家以独特视角对知识青年群体的刻画,还应感受到文本背后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作家在小说中孜孜不倦地探寻和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向阳面”的努力。
“痴”与“智”:别样的“知青书写”
举重若轻,点到即止
虽然同样是以“文革”时期为背景的故事,不同于“伤痕文学”对苦难的宣泄,《棋王》的故事基调是明朗而轻快的,其中写吃饭的段落和王一生与人下棋的段落,读来还相当痛快,令人振奋。故事的开头,作者惜墨如金,寥寥几笔便勾勒出火车站的景象,还原出浓厚的时代氛围。而关于“我”、脚卵、在垃圾站同王一生下棋的捡烂紙的老头,作者并没有巨细无遗地讲述人物的不幸遭遇,而是点到即止。例如王一生得知“我”父母已经不在世,便问这两年“我”是怎么活着的,还追问“我”是怎么吃饭的。虽然作者并未细述“我”的沉痛往事,但读者自然能通过王一生的追问感觉到背后的辛酸和凄凉。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不同于其他的知青文学,阿城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看到“文革”中“没有被生活打倒”的一代。阿城书中的下乡知识青年大都是一些悲壮的乐观主义者,不怨天尤人,不愤世嫉俗,不玩世不恭,更少有自暴自弃、甚至自杀的。世事瞬息万变,他们也曾怀疑,但怀疑过后却更加坚定了自身的信念,并由此将目光“从自己的脚下移向远方的地平线”(汪曾祺《读(棋王>笔记》)。“棋王”王一生便是这样的人。
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我”申请下乡成功,乘火车的时候遇到“棋呆子”王一生。在“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的喧闹车站,众人皆因离别而伤感,王一生却像个呆子一般,不哭不笑,邀请“我”下象棋。在下乡的旅途中,王一生不是下棋就是求着“我”讲故事,“我”由此与他熟识。王一生到农场插队,不像很多知青那样,每天不情不愿却又麻木地完成分配的任务,反是由着自己的喜好,频繁请假,到处找人下棋,完全不遵守农场的纪律,一心钻进了棋的世界里。或许在别人眼中,这样的做法显得过于离经叛道,但王一生却不会被其他人的看法影响:“我迷象棋,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待在棋里舒服。就是没有棋盘、棋子儿,我在心里就能下,碍谁的事儿啊?”
不久后,王一生来到“我”插队的乡下寻找棋友,“我”便给他介绍了队里的象棋高手“脚卵”(倪斌)。脚卯被王一生的精湛棋艺和对待象棋的赤子之心所折服,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情。脚卯劝王一生参加运动会,去领教领教县里的棋坛高手,王一生欣然同意。可等王一生前去报名的时候,却因为经常请假四处斗棋而被领导取消了参赛资格。脚卯为了让王一生参赛,不惜将家传的明代古董象棋送给主管运动会的书记。虽然王一生因为不想欠脚卯的人情而拒绝了这次机会,但运动会结束之后,王一生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与象棋比赛的前三名切磋。没想到凑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成了王一生一个人车轮连环对战九个人,场面壮观,轰动一时。大战结束后,王一生呆了半晌,方才哽咽而泣:“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
《棋王》中,王一生看似痴呆顽愚,但这“痴傻”后面却暗藏着“大智”。他那自由放达、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消解了胶着于现世价值而产生的时代焦虑,回到无关价值的本然状态中,以此达到内心无待于外的自由。王一生的“杲”和“痴”可谓是一种极致的人生态度,与阮籍的颓、米芾的癫、倪瓒的愚、黄公望的痴、李白的狂,有异曲同工之妙——超然于世、物我两忘的痴迷才能带来矢志弥坚的韧劲。
“吃”与“棋”:王一生之形象分析
汪曾祺曾评论道:“《棋王》写的是什么?我以为写的就是关于吃和下棋的故事。”
《棋王》中对于王一生的“吃相”着墨很多,将王一生对吃的虔诚态度描写得十分精细深刻。书中有两处写“吃”,一处是王一生在火车上吃饭,一处是下乡时吃蛇。前者写的是对“吃”的需求,后者写的是“吃”的快乐:
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缺一不可
作者围绕吃饭和下棋,生动地塑造了王一生的形象。马洛斯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其中“吃”无疑属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而“棋”之于王一生,则属于最高的“自我实现”的需求。王一生对于吃的态度严肃而务实,连衣服上一粒干硬米饭都要放进嘴里,他不喜欢杰克·伦敦把饥饿的人写成“发了神经”,当别人听说他下棋可以不吃饭,他反驳说“我可不是这样”。他信奉知足常乐,“半饥半饱日子长”。下棋好玩,让他忘却不如意的现实生活,此外,最后与九人的车轮大战更使他明白了人生在世,实现个人价值的意义。
(王一生)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
我将酱油膏和草酸忙冲好水,把葱未、姜未和蒜末投进去,叫声:“吃起来!”大家就乒乒乓乓地盛饭,伸筷撕那蛇肉蘸料,刚入嘴嚼,纷纷嚷鲜。我问王一生是不是有些像蟹肉,王一生一边儿嚼着,一边儿说:“我没吃过螃蟹,不知道。”脚卵伸过头去问:“你没有吃过螃蟹?怎么会呢?”王一生也不答话,只顾吃。
现当代文坛中,将食物写得极为精彩的名家有不少,如梁实秋、汪曾祺、唐鲁孙,多为风雅精致一路;路翎、莫言等人也曾写到酒肉吃食,却以食物为载体侧重表现人的欲望和原始的强力;像阿城这样直接而强烈地写“吃”本身,表现对食物和饥饿的敬畏的作家,却是罕见的。王一生对食物“饱于腹”的朴素追求正是他善于知足的人生态度体现之一,他把“饿”与“馋”严格分开,只要吃饱了,那么菜里的油便如同那可有可无的书和电影一样,全是“超出基准线之上”的。阿城通过刻画王一生的“吃相”及其对于吃的“低标准”,实质上赞扬了他超脱物质禁锢、遨游于人世的理想人格。
在阿城的笔下,“吃”并非一种简单的物质主义,它是一种“本我”的表现,也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通过“吃”,可以反映出王一生对身体本能进行自我调节的积极态度。而“棋”则是用以摆脱现实生活困境、完成精神追求的手段,是主人公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追求,更是他脱离“本我”达到“超我”的一种升华之道。
对于王一生而言,“棋”绝不是休闲娱乐的工具,它承载了别样的意义。在初学棋艺之时,王一生的母亲并不同意。在她看来。他们那样贫穷的家庭没有经济能力培养这种从前属于有钱人的爱好,下棋不能谋生当饭吃。但母亲拗不过王一生对棋着魔似的痴迷和狂热,最终同意他在不耽误功课的情况下下棋。母亲临死前,留给了王一生一副她自己用捡来的废旧牙刷柄磨制的无字棋。尽管它一文不值,但对于王一生来说,那是母亲留给他的“念想”,因此无比珍贵。在他经过九局连环大战之后,也不忘摸一摸黄色挂包中的“念想”。王一生清楚地意识到,下棋是自己无法被剥夺的精神寄托,他“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待在棋里舒服。没了棋盘、棋子儿,在心里就能下”。
在结尾的“九局连环车轮大战”中,王一生“一个人空空地在场中央,谁也不看,静静的像一块铁”,“眼平视着,像是望着极远极远的远处,又像是盯着极近极近的近处,瘦瘦的肩挑着宽大的衣服,土没拍干净,东一块儿,西一块儿”。他在棋中实现自我,远离世俗,达到忘我的境界:“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干世界,茫茫宇宙。”
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人生在世要不断努力满足的两大需求,具体到“棋呆子”王一生的身上便是“吃”与“棋”。“吃”是生存之本,是“本我”的原始诉求,是生活的前提与基础;而“棋”是升华之道,是“超我”的超凡脱俗,是人生的终点与巅峰。只有二者兼而有之,充分协调,“自我”才能活得潇洒出色。
“道”与“侠”:文化寻根中的坚守
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道”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而“侠”亦可以追溯至同时期刺客和侠士的故事,这两种文化基因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在小说中,王一生的棋被称为“道家的棋”,一是因为他学的棋谱有道家学说的成分,二是因为他下棋只讲究技艺的比拼,不在乎名利,已经达到了“道”的至臻境界。而王一生独自一人四处与人拼棋,最后与九人车轮大战的形象,叉恰似一个身怀绝技,孤身浪迹天涯,与众多高手会战的独行侠。至于脚卵和“我”,则与古道热肠、行侠仗义的江湖中人无异。“道”能帮助我们解决内心与外界的冲突,而“侠”反映的则是一种有良心、富有正义感的个人道德准则。不管在什么时代,这两点都具有积极的价值。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内容对当下具有积极的意义,等待羞我们去重新发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创作有两种流向:一是以文化批判为主要内容和价值取向,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有着深层次的继承关系;二是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更多的认同,着力于发掘和追寻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与正面价值。《棋王》是后者的代表,并对道文化和侠文化有多方面的积极、正面的思考,直接回应了寻根文学倡导的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诉求。
从《棋王》的主人公王一生的身上(无论是他对于“吃”的态度抑或是对于“棋”的追求)都不难看出道家思想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庄子在《逍遥游》中借用鲲和鹏的形象阐释了“无所待”而“游无穷”,进而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理想境界的人生智慧。而王一生“不役于物质生活”的理想人格与庄子“超越物质”的思想境界有一种遥相呼应的默契。老庄哲学对文本的介入不但没有使书中的主人公陷入一种消极虚无的避世观,反而让他更加坦然从容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同时从精神上寻求超脱之道,积极地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王一生虽身处“文革”的特殊年代,却不为世俗所左右,忠于内心世界的渴求,保持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態度,展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直指人生极致的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是执着于追求的极境,亦是老庄哲学中“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王一生为了向捡破烂的老人学下棋,主动帮老人撕去了大字报。他并不管哪一派的大字报,看见了就撕,展现出一种逍遥自得的姿态。当时派别林立,唯独王一生保持自我,不参与任伺拉帮结伙的行动,过着自己的生活,为自己搭筑一片自由的空间。王一生交朋友也不受制于当时的环境:无论是出生于书香世家的倪斌,还是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的“我”,他都真心相待。王一生无视外界环境的影响,依然遵从内心、超脱俗世、随遇而安,这正是对“逍遥游”的最好诠释。
阿城在《棋王》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仅诠释了“道”的内涵,还把“侠”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棋王》中的英雄不是传统文化中手拿宝剑的大侠,亦绝少金庸古龙小说中豪气千云的气度,甚至带有几分世俗的庸气,然而这并不影响作者展现书中人物侠义的一面,反而把读者拉到了那个年代真实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主人公王一生,还是次要人物脚卯、画家、“我”,无一不洒脱反礼、仗义忠诚,坚持自己独特道德准则,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内心的自由。
王一生品性近乎古时候的游侠,虽痴迷于下棋,却丝毫不在乎下棋能赢来的名与利。由于经常请假,平时“表现不好”,他失去了参加象棋比赛的资格,这对他而言无疑是极大的遗憾。但当朋友脚卵挺身而出,用家传的明朝古棋为他换来比赛机会时,他却拒绝了。他认为那是小人所为,一点也不光彩:“我反正是不赛了,被人作了交易,倒像是我占了便宜。我下得赢下不赢是我自己的事,这样赛,被人戳脊梁骨。”王一生没有参加比赛,但他却以一场轰轰烈烈、以一敌九的车轮棋局大战为自己的棋艺正名,令人叹为观止。在王一生的眼里,能畅快淋漓、正大光明地与高手过招才是自己的执着追求。
在《棋王》中,阿城垦掘了积淀于国民心灵深处、曾经充满活力的传统文化内核,将道文化中的超然物外、追求人生极致境界的态度和侠文化中的超越世俗的境界融为一体,形成了王一生不受限于物、在棋中实现自我、追求崇高理想的生命形态。这不仅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发现与提炼,同时也是作者面对现代文明负面的冲击而发出的重铸国民文化心理和国民文化主体性的一种理想追求,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流向具有启示意义。
注
草酸原本是用来去污的,小说中因为没有醋,于是知青们把草酸稀释后代替醋使用。草酸有毒,应避免与皮肤和眼睛接触,避免吞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