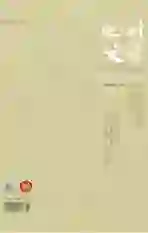母亲的皈依
2019-08-30刘益善
刘益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回到故乡的县城,住在县招待所里写一部长诗。我的一个写诗的学生周玉在县城工作,经常去看我,还接我到她家里吃饭。周玉家里就只有她和母亲两人,她母亲五十来岁,清秀苍白,善良却又有些忧郁,一看就是个有经历有故事的人。
我问了周玉,周玉说:“刘老师你看人真准,关于我母亲,我写了一篇稿子,你有时间帮我看看,你看完了,就知道我的母亲有多么苦了。”
我把周玉的稿子读完了,深深为周玉的母亲担忧,但我无能为力。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一堆旧稿中发现了当年周玉给我的这篇稿子,就稍加整理,成一篇中篇小说,以周玉在三十多年前的口吻叙述。
1
我像掉了魂一样,总感觉有人要来敲我家的门,会问:这是刘翠翠的家吗?来人会望着我母亲说:您就是刘翠翠?他心里会想,这样个瘦老太婆偏要叫这样好个名字。来人或者是个邮递员,递给我们一封信。这封信是辗转送到这个山区小县来的,信封都揉得很旧了,信封上写着:刘翠翠收。我看那在国内很少看到的邮票上盖的戳子中隐隐约约的两个字:台湾。或许不是,这封信是另一个地方寄来的,香港或是美国。上班时,我很注意电话,或者县里的统战部政协民政局的哪个人打电话找我,问:你是刘翠翠的女儿吗?我答:是呀。这个打电话的人说:是这样的,三十八年前......
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的了,他是谁?他是我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什么人?他要是真的来信了或回来了,我代母亲给他回信吗?他假如问我是谁,我准会立即回答我是刘翠翠的女儿。他可能觉得他的刘翠翠是没有女儿的,有过,他也不知道。
他是我母亲过去的丈夫,他还在吗?他会不会回来?我不知道。
我的母亲已经皈依了,她的心已如我们老家的那口废弃了的井。母亲的工作就是帮一对夫妻带好孩子,为我做三餐饭,再就是跪在供在她那个黑房间里的木头菩萨前,口里喃喃诉说着。我曾经躲在一边努力地听过,也没听出来她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只看见她发涩的嘴唇在不停地动着。
那个木头菩萨一尺来高,是个蓄了胡须的干巴老头,木头菩萨的底座上,用朱笔写著“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这是母亲不在时,我潜入她的房间看到的。
我十六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的傍晚,落日在小县城西边的山头上似乎被人捅了一刀,喷溅出一片淋漓的鲜血,殷红殷红的,染透了那半壁云彩和山上的草木。我不敢朝那边望,太怕人了,我躲进屋里做作业。一道数学题,我做了许久才做出来。
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饭,弟弟在门前逗小狗玩。我们家的小黄狗跟弟弟最好,弟弟上小学,作业比我少多了。
我们等父亲回来吃晚饭,父亲久久没有回来。而且,从这个傍晚以后,父亲就一直没有回来。
父亲被抓起来了,被判了十年徒刑。
父亲把他开的大卡车停在车库里,锁上了车库的铁门,把钥匙串挂在裤腰带上,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响。他是地质队的司机,是个好司机老司机,车开得稳,技术熟练,他的车爬山过岭最安全。在父亲被抓去后,我在一只箱子里发现父亲历年来获得的十几张奖状。可是父亲坐了牢,这十几张花花纸能说明什么呢?
父亲锁好车库门应该回家来的,他一天的工作干完了。看看天色还早,父亲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折身朝地质队机关办公的一排房子走去,他敲开了保卫科的门。
保卫科长一个人在,他们俩还坐下来抽起了烟,是保卫科长的烟,我父亲揿的打火机。
事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传说。父亲和保卫科长是战友,一起当过兵,一起转业到地质队,他们的关系很不错。那些说父亲因为嫉妒他的战友当了科长,而自己还是个司机,因而放响了那一枪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我的父亲从不嫉妒人。在张叔叔当了科长之后,他常常来我家里找父亲走象棋。如果没有出车任务,父亲就让母亲炒盘黄豆,他们两个还要喝几盅。父亲对他的驾驶工作很热爱,而且当司机的野外津贴高,实际上比当科长实惠得多,我想不出父亲为什么会嫉妒张叔叔。不是这个原因,绝不是。
有的说,他们俩“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一派的,他们结下了冤仇。不对,父亲“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派,他是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一定要划他派,那他就是逍遥派。他钓鱼,他做木工,他活得蛮孤独的,他跟张叔叔没有仇。
人们想不通,我也想不通。事情发生了后,父亲什么也不说,科长就只说我父亲持枪杀人,是凶手。父亲被抓走了。父亲为什么要向张叔叔(不,是张科长,我再不叫他张叔叔了)开枪?父亲不说,张叔叔也不说,办案的人也问不出什么。朝保卫科长开枪是事实,有这就够了,父亲判了十年徒刑。
那天,父亲和张科长抽完了一支烟,父亲站起来准备走了。
张科长也站起身,说:“怎么,不坐了!星期天再到你屋里下棋啊,只三盘定输赢怎么样?”
父亲抬头从窗户里看到西边山头上那幅雄奇的血淋淋的火烧云惨景,他愣了愣,叹了口气,双眼转过来盯着张科长。
张科长朝他笑了笑。
父亲从张科长的笑里发现了什么,他似乎一切都明白了。父亲朝屋子里打量了一眼,到底是当过兵的,他一眼把房子看得清楚。这是保卫科办公室,墙壁上挂着支七九步枪,那枪很老,也有好久没擦油了,上面有灰尘。
突然,父亲一个箭步跨到墙根,伸手摘下了挂着的枪,哗啦一声打开了保险,枪口寻找着目标。
张科长吓得面如土色,一头钻进办公室里摆着的一张木板床下。这张床是保卫科人员值夜班用的,床上的被子脏得要命。
我父亲扣响了扳机,砰!枪响了,地质队大院惊动了,等人们赶到时,父亲已扔了枪,呆呆地望着大伙。张科长的头钻在床底下不敢伸出来,他的屁股被我父亲一枪打了个洞,只流了一些血。父亲的这一枪打得并不准,毕竟他离开部队已经好多年没摸过枪了。
窗外,傍晚前的火烧云已慢慢散去,真正的夜马上就要来临了。那时我的数学作业已经做完,弟弟还在玩他的黄狗。
我母亲做好晚餐后,又跪在她的木头菩萨前,嘴里喃喃着。
父亲没能吃上这最后的晚餐。
没有人来我们的小平房里安慰我们,我们忽然成了持枪杀人犯的家属和子女,我们被突如其来的事变弄糊涂了。
上小学的弟弟睁着大得无比的眼睛,怀里紧紧地抱着他的小黄狗。我们突然没有被喊作父亲的人了。弟弟还有小黄狗,我呢,只有母亲。可母亲对我们只是尽她的责任,她的心早就交给了她的木头菩萨了。
母亲呆呆的,脸色苍白得发青,眼睛死死地盯着院子里的一只未归笼的鸡。我和弟弟一齐望着她,我们感到好冷。
许久许久,母亲的眼角才迸出了泪珠,第一滴,第二滴,接着是一串串地流。这时,我和弟弟才一起张开大嘴哭了起来,声音好大,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哭过了。
父亲被送到很远的劳改农场去服刑。
地质队负责通知家属准备必要的衣物送去。
来通知我们的是长络腮胡子的李伯伯。李伯伯是行政科的班长,调配车辆的。李伯伯在我家门口对我母亲说:“这个二虻子是为啥事呢?偏偏要拿枪打人,他们俩蛮合得来的嘛!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说完这几句就搓了搓他的大手掌,走了。
那是个春天,星期日,我和弟弟没有上学。母亲头天晚上把父亲的各种衣服找出来,打了个包。
我们走在去公安局看守所的路上。路边草儿青青,流水亮亮,雀鸟在树枝上喳喳,油菜花在地里开得好黄,麦田里的麦苗青得发亮,肥油油的腻人。一个老头,穿件破袄,横骑在牛背上,牛在啃草,啃出嗞嗞的声响,尾巴一甩甩的好舒服。老头望着我们,母亲拉着我和弟弟,胳膊间夹着衣物包,走快了起来。母亲没有说话,脸还是那样的白。远一点的地方,有头小牛犊子昂头“哞哞”地叫了两声,被老头压在屁股下的老牛抬起头,看都不看地“哞哞”两声,算是回答。
跟在弟弟屁股后的小黄狗也汪汪地叫了两声,像凑热闹。
地质队离看守所两里多路,地质队在县城的东北角,看守所在县城的西南角。
母亲走得快,我勉强赶得上,弟弟却要小跑了。
弟弟说:“妈,还有多远啦?”
母亲停下来等弟弟半分钟,说:“不远不远,就到了。”
我们朝前看去,果然就到了。在一处有很高的围墙的院子门前,站着拿枪的兵,围墙上还有铁丝网,跟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我和弟弟都有些怕,就紧紧挨近母亲。我觉得母亲的嘴唇在颤抖着。
父亲来了,父亲的眼睛变得好大好大,父亲的胡子好长好长,父亲的头剃得光滑溜的,父亲高高的身躯有些佝偻。
这是我们的父亲吗?好陌生啊,我和弟弟朝母亲身边靠了靠,母亲颤抖得更厉害了。父亲的大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们。
我和弟弟有些怕这个父亲了。
母亲本来苍白的脸显得更惨白了,一句话也不说,把我和弟弟朝父亲身边推了推。
父亲用手摸摸弟弟的头,对我说:“小玉,要听你妈的话,照顾好弟弟和娘,你十六岁了,要好好念高中。”
父亲说这几句后,眼泪流出来了。父亲是从来不哭的,父亲今天流眼泪了。我也想哭,但弟弟一点也不想哭。
小黄狗在屋子外头玩,弟弟从父亲身边走开了,出屋去找小黄狗。父亲叫我出去看着弟弟不让他乱跑。
我在屋门口的窗子下蹲着,看弟弟和小黄狗在院子里走,我听见父亲说:“孩子他妈,我要走十年,对不住你。你再苦也要把两个孩子带大,我周二虻一輩子忘不了你呀!你娘儿们要受很多苦的。”
我没听见母亲的声音。
父亲又说,“孩子他妈,我这辈子对不住你,要是太难,你就再走一家吧,把两个孩子送到乡下老二家里,求他们抚养!”
突然,我听到“啪”的一声响,就伸头往门里看去。母亲打了父亲一个耳刮子,父亲没有动,眼泪却像水一样地涌流。母亲也抱头抽泣着,她瘦削的肩膀不停地颤抖着。
好久,父亲叹口气说了三个字:“黄晓娟。”
我知道黄晓娟,她是地质队的会计,是个很好的阿姨,平时很整洁很干净的,蛮受人看的。
但黄晓娟怎么了?和父亲有什么相干?
有个人出来把父亲带走了。父亲回过头来望望我们,慢慢地随那个人走进了一个大铁门,铁门哗啦一声关上了。
几天后,黄晓娟和她爱人一起调到省城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个黄晓娟阿姨了。
2
当年,我母亲刘翠翠还是个十八岁的新媳妇。我母亲那时长得很标致,皮肤白皙,身材适中,脸面像那三月的梨花,芳香娇嫩又不妖冶。姥爷住的村子叫刘大庄,刘大庄的刘翠翠是个好女子,有多少人上门来求亲。我姥爷在村里开个杂货铺,自己还有几亩地,亦农亦商,家境在乡下算是厚实的。
姥爷要为我母亲择一个门第相当人才出众的丈夫,他没轻易应允那些人家。姥爷内查外调,看准了黄家大湾面铺的黄燕明。姥爷能运筹帷幄,具有较高的组织能力和安排事情的天赋,要是现在,让姥爷领导一个单位或主持一家企业,准能成为一个不错的领导或成功的企业家。
姥爷看准了的事情,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按他设计的步骤来,我母亲体面地出嫁到黄家大湾面铺屋里。
迎亲的花轿停在门口,鞭炮放得轰隆隆的,吹鼓手们将嘴巴吹得像只红汽球,唢呐呜里哇啦响得三里外都能听见,而鞭炮的轰响却传到五里外了。母亲后来对我说,那时候的鞭炮才响哩,如今的鞭炮又贵又不响,现在的唢呐吹得像蚊子叫,哪有那时的唢呐响亮!
母亲穿着红祅红裤红缎子绣花鞋,头上顶块很大的红布。母亲在红布下嘤嘤嗡嗡地哭得很上劲,哭成一支美妙的曲子,哭成一首直抒胸襟的诗。
其实她心里,恨不得快点离开这个家,越快嫁到黄家去越好。我姥爷是个专横的乡下人,他既有经营头脑又有一个长者的威严。为了保持小康之家的水平,姥爷用尽了心计,也用鞭子抽他的几个子女和我姥姥,拼命做事劳动,拼命节俭。我姥姥是个没有任何主意的乡下妇女,一切都听姥爷的。我母亲的全家都怕姥爷,他的眼睛一瞪,脸上的横肉抖动,就要叫人遭殃了,母亲在家是战战兢兢地长到十八岁的。姥爷说,棍子底下能成才。事实是我的三个舅舅都不成才,没有造就。土改时,姥爷家是富农,富农的子弟有什么造就,连当灰扑扑的农民都要低人一等。
黄家开面铺,乡下人用麦子在他家换面粉,他家有磨坊,有两头小毛驴,有日夜嗡嗡不停转的大石磨。给他家做儿媳不亏,黄家的家底子厚哩!那个黄燕明着实逗人爱,母亲在不知道自己要做他的媳妇时偶尔看到他,母亲看到他时心里慌跳着,羞得低了头。母亲听姥爷宣布她要做黄燕明的媳妇时,当时表面装着羞涩,背地里却几个夜晚睡不着觉,喜得乐滋滋的。
黄燕明虽说在镇上读中学,但也被我母亲的美貌与温柔俘虏了,竟成天沉浸融化在我母亲的情爱中,他拜倒在这位十八岁正含苞欲放的少女面前。他们夜夜欢娱,不知餍足。今天,作为母亲的女儿我写这些时,脸都红了,心里直在慌跳。
我想把这段跳过去,但想想也无所谓,我都二十多岁了,已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样样事情我都见过,我当然清楚男人们都是些什么样的德性。
光阴似箭,母亲的丈夫黄燕明在夜夜贪欢中不知不觉过了旧历年,又过了正月十五。乡下人说,年过月尽了,该干点正经事了吧!母亲的公公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似乎有些生气,但这个老头子不像我姥爷,用鞭子发号施令,他只用眼睛暗示法。
于是,我母亲和黄燕明觉得他们是得分开了,黄燕明还有正经事要做,他还有学业啊!母亲的公公花那么多钱叫黄燕明读书,可不是为了黄燕明回来当面铺老板的,他对儿子寄有希望,希望儿子精忠报国,光宗耀祖地干番事业。这些都是母亲从她公公的眼睛里读出来的。
母亲开始催黄燕明走了。
正月十六那天,和黄燕明一起在镇上读中学的两个同学,到黄家大湾邀黄燕明一道上省城,考个不要钱的学校读读,他们已经把镇上中学的最高年级读完了。他们都要寻找一条出路。乡下的土财主供个中学生已经不简单了,他们比不上城里的有钱人,他们希望有既能读书又不要钱的学校招收他们的子女。
母亲的公公为黄燕明准备了去省城的路费,据说钱不够,还到刘大庄找我姥爷借了五块银洋。这五块银洋一直没有还。我姥爷新中国成立后去世时,对我母亲还叨唠过这件事,说黄家欠他的钱已经这么多年了。可是,那时我母亲的公公已死了,黄家已经没有人了。这钱要还,就只有我母亲,我母亲曾经做过黄家的儿媳妇啊!
我母亲的丈夫和他的两个同学决定正月十八上路,他们选了个带八的日子。黄家面铺就黄燕明这个儿子,另有个闺女已出了嫁,我母亲的婆婆是个个子小脚小胆子也小的女人,成天像只老鼠样生活着。婆婆在家庭没有一点地位,一切都听公公的。那时,婆媳俩一起准备黄燕明出远门的一切:穿的和吃的,带了一包衣服和一包烙饼。
临走的那一天,离别的气氛越来越浓了,我母亲躲在新房里不出来。我母亲像被人摘走了心肝一样,痛苦得不得了,黄燕明就在房里陪着我母亲。
正月十七的那个夜晚,我母亲和她的丈夫早早地歇下了,两人在床上紧紧地抱着。我母亲比平日更温顺柔软,任她的丈夫亲着抚摸着,我母亲嘤嘤嗡嗡地哭起来,哭出了十二分的韵味来,哭得像泪人,使得她的丈夫心都要碎了。他们两人就这样哭着亲着折腾着,就好像要生离死别一样,赶快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来享受夫妻间的情爱。我母亲有个预感,她觉得这是她与丈夫的最后一个夜晚,她将要失去他。可怕的是母亲的预感却是那么准,果真黄燕明就此一去不返了,整整后半辈子。
那夜,我母亲有种特殊的销魂荡魄的感觉,就是这一夜,我母亲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听母亲说那孩子叫妞妞,是我异父同母却没有见过面的姐姐。那夜,我母亲和她的丈夫很累,后来就睡着了,直到我母亲的公公敲他们的房门叫吃早饭,他们才醒来。
起来一看,好一场大雪,满世界一片白,早起的村人在雪地里踩出了一个个的黑窟蔭。我母亲当时心里可能一喜,这么大的雪,她的丈夫可能不会走的。
可是黄燕明的两个同学都冒雪来了,黄燕明从父亲的眼睛里也得到了今天就是下刀子也要走的暗示,他决定告别我母亲。
这时我母亲回到房里,她的丈夫也跟了进去,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母亲又哭了。
黄燕明说:“我们等会谁也不要哭,谁哭谁就是小狗。”
母亲点点头。
我母亲把她丈夫和两个同学送到村口,我母亲还是哭了。黄燕明说:“说好了不哭的,你当了小狗了!”
我母亲永远记住了这句话,这句话常伴随着她的梦境。
同行的两个同学说:“燕明,你不走算了,你有这漂亮这嫩的媳妇,舍得吗?”说完两人笑了笑。
黄燕明没作声,背好了包袱,扭头就走进了雪地,再也没有回头。他不敢回头,他怕回头后就真的不愿走了。
男人好狠心呀!
1948年的那场大雪好白好厚,有三个黑点子慢慢消逝在白色的雪野里。
那年,我母亲的丈夫二十岁。
3
从我懂事时起,我就发现父亲和母亲的生活过得不协调,缺少一种和谐圆满性。我的母亲总是郁郁的,很少看见她笑。是日子太苦了吧!我们一家四口,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和我与弟弟的户口都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才由农村户口变成居民户口的。母亲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做临时工或在家里搞点手工赚点钱补贴日子。家里有部老牌的“飞人牌”缝纫机,母亲总是在这部很旧的机子上做口罩,给一家人做质地很差的布料衣服,或改旧翻新。母亲很会持家,我们的日子虽然穷苦,但我们从没缺吃少穿的。父亲节俭,一套工作服穿好多年,穿旧了,母亲再改给她自己或我穿。
我们家有那么一种冷冷的气氛,有一团阴影,我越长大越感觉到这一点。母亲对我和弟弟尽了一个母亲的责任,但我们从她那里得不到多少温暖和愉快。是什么原因呢?是那块破木头菩萨吧!母亲的心全在那上面,她總跪在那木头菩萨前喃喃着。
幸亏我们有个好父亲,父亲是疼爱我和弟弟的,这点我感受特别深。弟弟可能感觉不到,他像我母亲,也有点冷,可能是他吃的母亲的奶是冷的。我推算出,在弟弟还怀在母亲肚里时,母亲的心就冷了。
父亲常出车,有时出去几天才回来,那时我就特别想父亲。父亲回来了,虽说我都十来岁了,我总要扑到父亲怀里,让父亲用他的胡茬子扎我,我还爬到父亲的膝上坐着。这时弟弟就站在一边,望着我们,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只好嘟着嘴回到厨房里。
父亲趴在地下,让弟弟骑在身上,父亲就满地爬呀笑呀,可弟弟却不笑。我怀疑弟弟有痴呆症。但是弟弟长大后不痴不呆,初中毕业了还考上了中专。
父亲在地上做马,口里还叫:“小舵,快点赶马呀,你赶我打我,我就跑得快些。”
弟弟就伸出他的小手,无情地在父亲的屁股上、头上,打得啪啪响,口里就喊:“快跑快跑,你这个不中用的老马。”
弟弟打父亲,打得我的心都痛了,而弟弟和母亲都无动于衷。我真想让母亲制止一下弟弟的顽劣,母亲在忙忙碌碌地干她的事,一声不响。
父亲在弟弟的驱赶下,跑得更快了,他一边跑一边笑着:“小蛇你骑好咧,小心我把你掀翻在地,摔你的屁墩子。”
父亲和弟弟玩过了,我看见父亲一头一脸的汗,弟弟却没事一样,又在一边待着。
吃过饭,父亲就检查我的作业,夸奖我得了三个一百分。作业检查完了,父亲就拉我坐在他身边,叫母亲递把梳子过来,父亲为我梳两只小辫子。父亲那样笨拙,把我的头发扯痛了。
父亲说:“小玉呀,不小了哇,干什么不把头梳好,像个疯丫头样,嗯?”
我都流泪了,为我梳头的为什么不是母亲?父亲你出车一天了,你累了。
父亲见我流出了泪,忙说:“好,我轻轻地轻轻地,扯痛了你吧!就梳好了。”
今天回想起父亲的络腮胡子,父亲为我梳头时的那慈祥的样子,我又要流泪了。父亲再不可能为他的二十多岁的女儿梳头了,父亲已经老了。父亲,在远方服刑,每年都寄两次明信片回来,说明他还活着。
在那个春夜,我覺得我成熟了。我同情父亲,我却不理解母亲,甚至有点恨母亲。我是在了解了母亲的经历后,才不恨她了。但我仍然深深地为父亲叹息,父亲是很可怜的。
父亲出车一个多星期后回来。父亲是运什么东西到一个城市,回来后给我和弟弟带了不少好吃的东西,父亲还给了我一个日记本,作为对我学习好的奖励。我是用父亲送给我的这个日记本开始写下我生平的第一篇日记的。父亲给母亲买了件铁灰色的涤卡春装,那时人们能有这么件据说能穿好多年都不破的涤卡衣服,是生活水平高的标志。
我看见母亲接过衣服时,嘴角抽动了一下,我以为母亲要笑的。哪晓得母亲扯扯嘴角没笑出来,只用眼睛默默地望了父亲一眼,脸又恢复了她的木然。
晚饭后父亲和弟弟玩了阵子,又给我梳了头,检查了我的作业,一家人就都睡觉了。
父亲母亲睡在上房,我和弟弟睡在下房。弟弟早早进入了梦乡,鼻息声轻轻的,很有节奏。也许是得了父亲一个日记本的奖励,我竟激动得好久没有睡着。就在我刚要蒙昽入睡时,上房传来的声音又使我惊醒了。
我听见父亲母亲睡的大木床响了一下,接着有窸窸窣窣的声响。
父亲说:“来吧!”声音柔柔。
母亲说:“算了,人累死了,我不想。”声音冷冷的。
父亲说:“来吧,我求你了!老这样的,我受不了,两个月了。”父亲的声音好可怜。
“算了,我真的一点心思都没有。老周,忍忍吧,莫折磨我了。”好久没听见父亲的声音,我的心慌跳着,无意间,我发现了大人们的秘密。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了,对男女间的事情了解得不深不透隐隐约约似是而非的。父母亲晚间的事情,我这还是第一次耳闻。
母亲又说话了:“老周,原谅我吧,对不住你了!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不能啊!每有一回,我就恶心,就痛苦,就一连好多天像掉了魂样,心里像有把刀子在戳着。老周,你就算了吧!”
只听父亲长叹了一口气。一会儿,我竟听见父亲嗡嗡地抽泣起来,哭得好伤心啦我的父亲,可是母亲却一声也没吭。
我很吃惊也很迷惑,我想啊想啊,我觉得母亲对父亲不好,父亲母亲那时都只四十才出头啊!我估计,从那时开始,我的父亲母亲就没有过夫妻生活了。
他们这是为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父亲已经走了,他又出车去了。母亲正忙着给我们做早饭。我看看母亲的脸,还是那样板板的冷冷的,好白。母亲看上去其实不老,母亲那时还是很端正的,年轻时的风韵还留在她的脸上身上。
父亲还是那样出车,回来后给我们带点东西,花钱不多。父亲还是给弟弟当马骑,还给我梳辫子检查作业。
母亲穿着父亲给她买的涤卡春装,很合身。
父亲有时带我和弟弟坐在他的驾驶室里,父亲驾驶着他的卡车在春天的原野上奔驰。父亲笑,我笑,连弟弟也难得地笑了,我们玩得很高兴。
但我们的家还是有股子冷气,不温暖。
那夜之后,我就很留意上房里父亲母亲的活动。他们偶尔对几句话,说说家务安排方面的事,没什么异常的响动和话语。
只是有一个晚上,我听见母亲翻了个身,叹口气对父亲说:“老周,太难为你了。在外面有合适的,你就……”母亲顿了顿又说,“我绝不管,你莫苦了自己。”
父亲不作声,叹了口长气,简直叹得惊天动地。
4
我母亲和她的丈夫新婚燕尔,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突然的别离,使我母亲难以忍受。从雪地里回来后,我母亲就有些发烧了,一阵晕眩,她病倒了。我母亲的婆婆小心侍候,端茶递水,照顾周全。我母亲的公公也很关心,请医生号脉买药。医生说无碍大事,只是中了风寒罢了,待几天养息,即可痊愈。
母亲独坐空房,特别是在夜间更难熬。想起她丈夫的百般恩爱,情深意长,越想越思,恨不能长翅膀飞到黄燕明的身边。窗外的夜是寒冷的,雪还未化。黄燕明,这时你在哪里呢?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否也在想乡下的新婚妻子,咬着被角,哭了一场又一场,她想她的丈夫想得好苦哇!
服了药,我的母亲就好了些,慢慢就起床走出房门。我的母亲瘦小,皮肤显得更白眼睛显得更大,就更使人疼爱了。我母亲的公公见媳妇这副模样,在饭桌上第一次没有用眼睛暗示而是充满着慈爱对我母亲说:“孩子,你还年轻得很啦,要看远些。把燕明留在身边有什么出息咧?还是让他出去闯,男人家闹出些名堂来才不枉活一场,是不是?”
我母亲点点头。我母亲的婆婆也跟着点点头,她也很想她的这个独生子,只是她不敢表示出来。
道理我母亲明白,她是个明事理的人。我母亲病好后,就到磨坊协助婆婆做磨麦呀筛面剔麸呀等活计,她的公公负责用面和人家换麦子赶毛驴拉磨等一应事宜。这家人的日子就像小毛驴拉磨一般,在磨道上一步一步地走着,平静极了。我母亲的公公的理想超过了磨道,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能否成气候,当父亲的拿得并不太准,但他还是督促儿子去闯。这在乡间是不简单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的公公是个开明富农,虽说还是经常挨斗,但比我姥爷挨的斗少多了。
我母亲白天里参加磨坊劳动,晚间歇下来,看到房里还没暗淡的红纸剪成的“囍”字,看到床上空余的一个枕头,在那漫长的春夜,像我母亲那样含苞正放的新媳妇,我是可以想象她那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情形的。我母亲盼望她的丈夫来信,盼望关于她丈夫的一切信息。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什么信息都没有。公公婆婆着急了,黄燕明的两个同学的家里人也来打听消息,他们也着急了。我母亲急得更厉害,当时,她已怀上了我异父同母的姐姐妞妞,妊娠反应比较厉害。
念丈夫怀孩子,我母亲茶饭不思,默默流泪。
一向有主见的我母亲的公公也有些稳不住神了,他一面说些话安慰我母亲,一面四处打听些消息,仍然没有什么结果。
黄燕明离家三个月后的一天,那天早上我母亲早早地起来,她感到精神比往日好多了。思念虽说还是思念,但比开始那阵要平缓些了,只能在心里慢慢地念了。妞妞在肚子里已有拳头大了,三个月,胎位已经正常,我母親在公公婆婆的照料下,身体也好起来。
那时,中午饭刚吃完。我母亲和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吃的黑面疙瘩。他们家有黑面疙瘩吃就已经不简单了,因为他们家有座磨坊。生意很清淡,新麦没有登场,旧麦又吃完了,穷些的人家正闹粮荒。午饭吃了,勤快点的人都到田地里转转,看那麦子还要多少天才能收割,看那刚播下去的早谷秧返青了没有。没多少田地又有点懒散的人就乘此机会睡上一觉。面铺没什么事,我母亲又有身孕,因此她睡着了,睡得很香很甜,是黄燕明离家之后睡的第一个香甜觉。
当婆婆小心地推醒我母亲时,我母亲有些懒洋洋地爬起身来,很不情愿。我母亲的婆婆小心翼翼地说:“有客人来了,你爹到磨坊去了,你起来看看吧!”
我母亲拢拢头发,扯了扯衣襟,因刚睡了觉,就满面红光有些娇羞慵慵的模样走出房门。
我母亲看到堂屋里坐着个男人,戴顶旧毡帽,穿件粗蓝布做的长袍子,腰里用布带子系着。来人三四十岁的样子,正低头喝着我母亲的婆婆倒给他的茶,似乎走了好远的路。这不是驾船的黄老大吗?
我母亲认识这个人,是她公公一个族里的,长年在外帮人家驾船。我母亲出嫁来黄家时,这人来喝过喜酒的。
黄老大见我母亲出了房门,忙搁下茶碗站起身:“新婶子,燕明叔在南京让我带信回来,这是特地给您送来啦!”
听说黄燕明有信来,我母亲的脸上一阵红晕,心里喜滋滋的。她忙说:“大哥,稀客稀客,快坐快坐!”
黄老大在家族里比黄燕明小一辈,称我母亲为“新婶”,也是规矩,因为是新结婚的。黄老大没顾得上坐,从腰里掏出两封信来,一封是写给我母亲的,一封是写给我母亲的公公的。我母亲接过信封上写着“刘翠翠收”的信,酸甜苦辣,千种思念万般恩爱一齐涌上心来,她简直想要哭一场,是快活的哭还是委屈的哭,她说不清楚。这时我母亲的婆婆已经把公公从磨坊里叫回来了。
黄老大说,他们的船队这回给南京运麻,从汉口开的头,走了好多日子才到南京。黄老大他们的船在南京卸了货后,等着再装一批货回汉口,船在码头上泊着。黄老大几个人没有事,有天晚上到码头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喝大碗酒,没想到在小酒馆里就碰上了几个穿军服的学生兵喝酒,这是个星期六的晚上。
“当时我们也不怎么在意,我们驾船的,他们当兵的,各喝各的酒,我们喝酒说话,没想到来了个学生兵问我们是哪里人,我说了,那人就朝那桌上喊,黄燕明,这是你湾的人呐,快来。那边就答,真的吗?立时就来了个高高大大的军人,我一看,天哪,这不是燕明叔吗,怎么在这里呢?两个多月前,我喝了他的结婚喜酒才走的嘛!可不,就是他,我燕明叔,长胖了,穿了军装,好威风哟!”黄老大歇口气,喝口水,说得我母亲和她的公公婆婆呆呆的,只催问黄老大,黄燕明怎么当兵了?
“不是当兵,他们那叫航校,是军校呢,读书不要钱的学校。听燕明叔说呀,他们毕业后是开飞机的。”黄老大急急地说着。
那天,我母亲的公公很高兴,有了儿子的消息了,而且儿子上了军校,准是有出息的地方,但是他们不知道战争当时正激烈着咧。
我母亲的公公给了黄老大一斗麦子作为酬谢,并嘱咐他,走的时候告诉一声,他要给黄燕明带信去的。黄老大说,那好,他们的船下汉口时,他一定告诉,从汉口到南京的船好多。我母亲当时心里也决定要写封信给她的丈夫带去。我母亲跟我姥爷学得一些字,至今她还能认千把字呢。
我的母亲和她公公写给黄燕明的信后来就一直没有带去,因为黄老大他们的船没有下汉口,后来就解放了。
再后来,跟黄燕明一起出去的两个同学中的一个回到乡下来,他对我母亲和我母亲的公公说:“黄燕明开着飞机到台湾去了。”
那天晚上,我母亲一个人在房里把黄燕明的信读呀读,读得彻夜难眠,特别是信的开头写的“翠翠爱妻”四字,已经融入了我母亲的血液中。那夜,我母亲一定是把黄燕明的信放在她饱满的哺育了我的生命的胸前而入睡的,她一定做了梦,是个好梦。
5
在我记事之前我父亲和我母亲之间发生的事情,是我的大舅妈告诉我的。我姥爷和姥姥死了后,三个舅舅分家立业,各分得顶富农子弟的帽子戴着胆战心惊地过日子,直到前几年政策揭了他们的帽子,他们才松了口气,可他们也都快老了。父亲出事了后,我回过一趟老家,实际上是我母亲的老家刘大庄。
我住在大舅妈家。
大舅的背已经驼了,不爱作声,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大舅妈拉着我的手,鼻涕眼泪一起流,直哭我母亲的命苦。那夜,大舅妈唠唠叨叨给我说了大半夜,直到她家的那只芦花公鸡叫出响亮的声音,她才让我上床睡觉。
那阵子,传说我母亲老家那一带有煤,好多好多的煤。反正那时候大跃进,你说地下埋的到处是金子也不犯法。我父亲就是在那时候随着地质队来到刘大庄的。
地质队整天测量呀,钻探呀,插许多的小红三角旗呀,吸引了不少的乡下人看稀奇。我母亲那时已经回到刘大庄住下来了,她带着我那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妞妞一塊过日子。
我母亲她们一群妇女正在田里薅秧草,忽然看到村里来了七八个人,还有汽车,就一窝蜂地从田里爬起来跑拢去看。我母亲和我大舅妈一起,那时她是个俊俏的小媳妇,显得特别的水灵。
我父亲周二虻正是个毛头小伙子,驾驶着解放牌卡车,神气得不得了。±也质队男的多女的少,经常在野外工作,这次能在一个村里驻扎下来算是好条件了。我父亲看到来了一群妇女,高兴得直揿汽车的喇叭。他一边揿喇叭,一边朝妇女堆里瞅,他一眼就啾到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当时在那群妇女中显然是最端正的一个。我父亲看到我母亲后,把已停的喇叭声陡地又揿响了,吓得我母亲一跳。我母亲朝他望了一眼,他就朝她咧嘴一笑,笑得我母亲红着脸低下了头。当时我大舅妈站在她身旁看得清清楚楚。
地质队在刘大庄住了三年,三年后,连个鬼毛都没捞着就撤走了。只有周二虻除外,他有收获,他终于带走了我的母亲,从而就使我和弟弟小舵有出生在世的机会了。
我父亲得到我母亲那是非常艰难的,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母亲带着妞妞从黄家大湾回到刘大庄是土改工作队的主意。姥姥是一九五四年发大水淹死的。妞妞已经九岁了,在村里念小学二年级。姥爷把本来已经很窄的茅草棚腾出了半间让我母亲带妞妞住,让她们单独开了个小门,算是另一家。姥爷跟三个舅舅是一家,三个舅舅只有大舅娶了媳妇,另两个舅舅是过了许多年后才娶的媳妇。
我母亲帮着大舅妈洗一家人的衣服。刘大庄紧挨着金水河,这金水河是长江的支流,不是天安门前的那个金水河。我母亲每天早晨都提一桶衣服到金水河边去洗。
地质队借用了刘大庄的一幢空房子住下来,空房子坐落在金水河边。
那天早晨,我母亲用左手臂挎着一大桶衣服,右手握着木棒槌,经过地质队的门前到河边洗衣服。那天天气很好,早晨的空气里充满着一股茉莉花的幽香,村里人在菜园里种了一些茉莉花。人们精神很好,人们都很高兴,那时吃饭不要钱,做事人多热闹,共产主义也不远了。我母亲挎着木桶,走路扭动着腰肢和臀部,扭出无尽的轻灵和少妇的风韵。当时,周二虻正趴在他的解放牌卡车下检修,从车底下看见了我母亲,忙钻了出来,不小心蹭了一脸的黑油泥。
我母亲正走着路,口里还哼着歌,突然见汽车底下钻出这么个人来,先是吓了一跳,继而又哈哈笑起来。周二虻也跟着笑起来,两人就说上了话。
“洗衣服去呀?”
“洗衣服去!”
就这么简单。周二虻再想说下句时,我母亲已经下了河坡,只看得见她的背影了。
周二虻这时也就无心检修他的车了,怏怏地钻进住房中,拿了肥皂毛巾漱口的牙刷杯子也下河坡,在我母亲旁边的一个水埠石旁蹲下。周二虻一边用肥皂洗手,一边盯着我母亲看,看得我母亲不敢抬头,心里好恼火。
河边这光景幸亏没有旁人。
周二虻说:“你叫刘翠翠是吧!你一个人带着九岁的妞妞住在你爹家里是不是呀?”
我母亲只好点点头,心想这人好讨厌,才来两天就把我的情况弄清楚了,你弄清楚我的情况又有什么用呢?
“我叫周二虻,今年二十六岁,共青团员,从部队当兵回来,在地质队里开车,还没成家。”周二虻不知怎么回事,在这个早上,在这条静静的小河边,忽然抑制不住自己,向一个刚认识的乡村少妇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情况来。他平时是挺老实的人,多少年来,他也一直不轻浮。但那天在绿绿的小河边,他显得有些轻浮和不可理解了。
我母亲当时就虎下脸:“姓周的,谁要听你这些啦?我不认识你!谁管你成家不成家啦?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母亲气冲冲地说完,扬起手中的木棒槌,把衣服放在石板上,捶得啪啪啪地直响,捶得水花四溅。
周二虻被我母亲的几句话呛得直翻眼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呆呆地停止了手里的搓洗,肥皂泡涂了双手,不知怎么办才好。
我母亲捶了一阵衣服,看周二虻窘得那样,心里又有些不忍,她是个宽厚人。她顿了顿说:“大兄弟,你出门在外,不可太轻贱了自己呀!我是个有孩子的人,我男人在外面。我比你大,可以当你的姐姐。你快洗手洗脸回去吧!今后再莫给我说这些话了。”
周二虻像获得大赦一般,赶紧洗漱完后,低着头匆匆地逃了。
我母亲见他那样子,心里在暗笑。她忽然觉得这个黑黑的小伙子有些可爱了。
周二虻这个人倔,早上受了顿抢白,却对我母亲不死心。
当天晚间,周二虻竟然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提着一包点心糖果,敲响了我母亲与妞妞住的茅棚柴门。我母亲打开门,一见是他,心里吃了一惊,问:“你来有什么事?”
周二虻嗫嚅着半天没说出话来,憋了半天才红着脸说:“大姐……姐,我来看看你和妞妞!我给妞妞买点糖果点心,你收下吧!”
我母亲见他那难受的样子,只好放他进了小屋子。那半间小屋太小了,放了张木床后,就没多少空隙了。一张小木桌子,妞妞正趴在桌上就着油灯写作业。妞妞见我母亲的眼色后,就乖乖地喊了周二一声叔叔。
小屋被收拾得整整齐齐,周二虻听见妞妞喊他,竟兴奋得不得了,就和妞妞一起玩起来,检查起妞妞的作业。周二虻在小屋里慢慢变得自然起来,和在灯下给妞妞纳鞋底的我母亲聊起天来,他看起来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