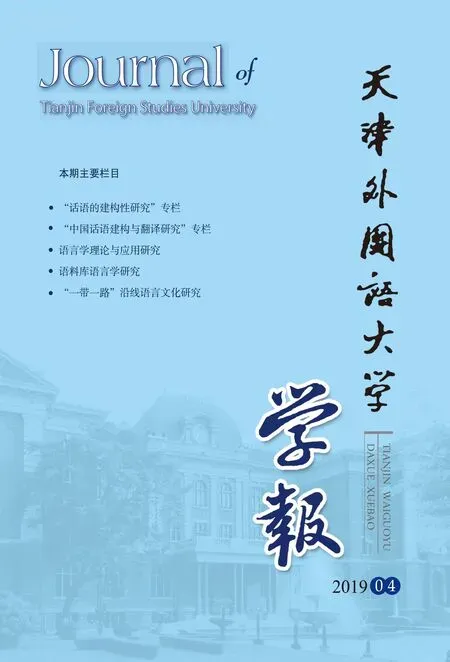基于语料库的隐喻运动事件方式语义突显度研究
2019-08-28邓宇
邓 宇
(四川外国语大学 语言脑科学研究中心)
一、引言
自Talmy(1985)开创运动事件词汇化模式跨语言研究以来,认知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语言和认知中的空间运动事件表征给予高度关注。Talmy(1985,2000)把含有运动及持续性静止的情景都看作是运动事件,其框架事件结构由[焦点](figure)、[背景](ground)、[运动](motion)和[路径](path)四个语义成分构成。这些成分还可以与表示[方式](manner)或[原因](cause)的副事件(co-event)相结合(Talmy,2000:25-26)。例如,the bottle[Figure]floated[Motion]+[Manner]into[Path]the cave[Ground]表征的框架事件是瓶子移动到洞穴,副事件则是瓶子移动的方式漂浮(float)。运动事件中的副事件虽处于从属地位,却有可能比框架事件显得更为具体、形象和生动(严辰松,2008:9)。如上述例子中的float 所编码的运动方式信息是整个运动事件表达中比较凸显的精细要素。
Talmy(2000:222)根据运动事件中[路径]要素的编码位置,把世界上的语言分为两大类型。若[路径]编码在动词词根中,则该语言为动词框架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s,简称V-语言),如罗曼语、闪语、日语、泰米尔语、班图语等,其典型示例为类似Kelly entered the room 的表达。若[路径]编码在卫星语素(satellite)中,则该语言为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amed languages,简称S-语言)。卫星语素是指除了作补语的名词短语或介词短语以外的其他语法成分,通常伴随动词词根出现。卫星框架语主要包括印欧语言(罗曼语除外)、芬兰乌戈尔语、汉语等,典型示例为类似Tracy ran into the room 的表达。
已有实证研究表明,S-语言和V-语言对[方式]语义的突显度存在显著差异,S-语言描述[方式]语义成分的频率更高,编码[方式]语义的动词更加丰富多样,并且S-语言中的方式动词比V-语言中的方式动词更加生动形象(Cardini,2008;Ibarretxe-Antunano,2004;Sabine&Françoise,2011;Slobin,1996a,1997,2004;Slobin et al.,2014)。Özçalışkan(2003,2004,2005)和李雪(2009)通过跨语言对比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类型语言的[方式]语义突显程度差异也会扩展到隐喻运动事件词汇化模式中去。整体而言,[方式]突显的类型学差异在客观运动事件中已充分证实,但在隐喻运动事件中尚需进一步验证,尤其是语料库实证数据。鉴于此,本文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考察现代汉语隐喻运动事件词汇化过程中[方式]语义的突显度问题,探究词汇化类型学差异如何扩展到隐喻运动事件中去。
二、研究假设和问题
有关概念隐喻的理论、实证研究表明,空间运动在人类涉身体验中具有普遍性,因而常作为源域来理解抽象概念,如时间(moments slip by)、思想(the idea sprang back into his mind)、情感(she felt a sudden surge of emotions)、经济(prices plummet)等(Lakoff&Johnson,1980,1999;Özçalışkan,2005:208)。隐喻运动是相对于真实运动而言的,真实运动事件只涉及空间运动一个概念域,如the ball rolls down the hill;隐喻运动事件则涉及两个概念域,即源域(空间运动)、目标域(如心情、情绪、状态、时间等)以及二者之间的概念映射(如TIME PASSAGE IS MOTION ALONG A PATH,MIND IS A CONTAINER,STATES ARE LOCATIONS),如the idea races through her mind like a flame,he drifts into a state of utmost solitude,the ambiguity in her voice pulls his worst fears to the surface(Özçalışkan,2005:213,238)。在隐喻运动事件中,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是单向的,目标域的概念化通过源域实现,源域的结构决定了目标域的结构,因此源域的跨语言差异也会映射到目标域。由此观之,Talmy 的运动事件词汇化类型学在隐喻运动事件和非隐喻运动事件中的效度具有同一性(Özçalışkan,2005:237-238;邓宇、李福印、陈文芳,2015:74)。
Talmy(2000:272)认为汉语是很强的S-语言。倘若Talmy 的假设是正确的,汉语应属于[方式]语义突显度高的语言,方式的概念空间会获得更多注意力。具体而言,汉语表征方式语义的可及性较高,编码方式的词汇丰富程度和频率也较高。如果这一假设通过实证调查被证伪,则Talmy 对汉语类型的论断值得商榷。
基于上述假设,本研究从隐喻维度分析汉语在[方式]语义编码中的类型学特征,具体研究以下问题:(1)汉语隐喻运动事件中方式动词、原因动词、路径动词的使用频率存在什么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2)汉语隐喻运动事件各目标域中方式动词做主动词的分布情况如何?(3)汉语隐喻运动表达中编码[方式]语义的其他词汇和语法手段都有哪些?
三、研究方法
1 语料搜集
本文的语料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Corpus of Chinese Linguistics,CCL)。在语料搜集过程中,我们借鉴Özçalışkan(2005)与李雪(2009)、邓宇、李福印和陈文芳(2015)的思路,选择与人类涉身体验最为密切的五官感知(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和心理状态作为隐喻运动事件的目标域,源域为空间真实运动。隐喻运动事件所涉及的映射模式为五官感知和心理状态是移动实体或五官感知和心理状态是静止处所。为有效提取隐喻运动表达,我们基于上述目标域设定语料检索关键词,具体选取能够充任运动焦点(figure)的五官感知和心理状态类常用名词为关键词。
(1)五官感知和心理状态类关键词
a.视觉感知(眼睛、眼光、泪光、目光、眼波、眼神……)
b.听觉感知(声音、歌声、笑声、驼铃声、哭声、飞机声、回声、哨声、鞭炮声……)
c.味觉感知(甜蜜、甜味、酸味、咸味、酸甜苦辣……)
d.嗅觉感知(香气、腥味、臭味、香味、气味、花香、清香、香水味……)
e.触觉感知(风、寒冷、电流、刺痛、轻抚……)
f.心理状态(思想、记忆、脑海、心、感情、兴奋、喜悦、精神……)
上述关键词在日常使用中出现频率高,且不具备空间物理运动的属性,在与运动动词搭配时,隐喻化的概率较高,因此可根据所在的索引行语境人工识别隐喻运动事件表达。语料提取过程中,在CCL 网络版检索页面逐条输入(1)各目标域中的关键词,以“现代汉语”为搜索范围,提取出以(1)的关键词为运动焦点的句子,如“那如托尔斯泰般犀利的眼神像闪电一般袭到我的头上”,“远处飘来悠扬的歌声”,“刺鼻的臭味钻了出来”,“酸甜苦辣齐齐向心头涌来”,“剧烈的疼痛由指尖流进我的全身”,“一股喜悦之情浮现在他的脸上”等。通过随机抽样和等比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筛选出200 例隐喻运动表达,作为样本(邓宇,李福印,陈文芳,2015)。
2 语料分析
语料编码过程中,我们以小句(clause)为语言分析单位,即每个小句只包含一个谓词,每个谓词只表达一个情景(Berman&Slobin,1994:657)。一个谓词可以是任何运动动词或者动词复合体(verb complex)。我们对样本中的方式动词(V[方式])、表示方式的其他词汇-语法手段、原因动词(V[原因])和路径动词(V[路径])、路径卫星语素(Sat[路径]/[处所])以及与方式动词具有均等语力和重要性的路径动词(V-plus[路径])等语义要素进行编码。样本中的隐喻运动表达的主要词汇化模式如下。
(2)主要运动动词及其隐喻运动事件构式
a.V[方式]+Sat[路径]:我的思想飞向法国去了。
b.V[原因]+Sat[路径]:歌声冲散了水面上的阵阵凉意。
c.V[路径]:有个声音穿过年轮时光。
d.V1[方式]+V2-plus[路径]:各种声音还是钻挤进来。
e.V[方式]:有一股怪味儿在屋里飘。
f.编码[方式]的其他词汇-语法手段:
副词:一种奇妙的浅甜味浅浅萦绕唇齿间。
动词补语:兴奋与好奇倒升得相当高。
形容词:一个奇怪的沙沙作响的声音穿过尘暴。
重复:歌声飘向很远、很远……
g.静态事件:V[方式]+Sat[处所]
他话不多,脸上总是挂着忧伤。
凯薇茫然地走出小铺,风暴般的愤怒和忧伤充斥着她的心。
三、调查结果
1 隐喻运动动词的频率分布
经统计,样本中的运动动词类符和形符的频率分布归纳如下。

表1 汉语隐喻运动事件中的运动动词频率分布
表1显示,200 例隐喻运动表达总共包含60 类运动动词,形符总数为210。方式动词在类别上和数目上均超过其他两类动词。我们对方式动词和路径动词的类符数目和形符数目分别进行非参数卡方检验,结果表明,隐喻运动方式动词和路径动词在类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x2=6.422,p=0.011<0.05),形符总数差异也很显著(x2=37.3 56,p<0.05)。样本中的方式动词类符和形符具体分布见表2。

表2 隐喻运动方式动词类符和形符分布
表2显示,样本中的31 类隐喻运动方式动词以单音节为主,形符数目排在前十位的是“涌、飘、闪、冲、掠、钻、走、袭、滑、飞、流、浮、扑”。大部分方式动词以位移性运动为主,但也有少数方式动词属于静态处所类,如“笼罩”、“挂”、“充斥”、“洋溢”等。
方式动词与其他运动动词在频率上的显著差异亦会体现到主动词的分布特征。按照隐喻运动事件的不同目标域,我们将方式动词和非方式动词作主动词的频率分布归入表3。

表3 各目标域中作主动词的运动动词百分比
表3的数据分析表明,方式动词在各目标域中作主动词的频率均高出路径动词和原因动词作主动词的频率。结合表1至3可看出汉语隐喻运动事件中方式动词在形式上和语义上的突显度均超出其他类别的运动动词。
2 编码隐喻运动[方式]的其他手段
通过其他词汇-语法手段编码隐喻运动[方式]语义的表达总共有13 例(见表4)。

表4 编码[方式]的其他手段
表4显示,编码隐喻运动事件[方式]语义的其他手段主要是用副词性表达修饰运动动词,样本中有10 例。需要指出的是,被副词性表达修饰的动词通常也是方式动词,如“映雪心里一紧,酸楚狠狠冲入咽喉”。使用动词补语编码[方式]的表达只有两例,如“兴奋与好奇倒升得相当高”,方式信息是通过路径动词“升”后的动词补语来描述。形容词表示[方式]的语料只有一例,这类方式信息是隐性的,如(2)f的“沙沙作响的声音穿过尘暴”,形容词修饰的是运动[焦点],而非路径动词“穿过”,但结合语境可推断,声音穿过尘暴时响动很大,这也是运动方式。词汇重复是强化[方式]语义的附加形式,如(2)f 的“歌声飘向很远、很远”。
四、分析讨论
1 [方式]语义的突显
在运动事件中,[方式]的惯常表达体现出[方式]语义的突显程度。[方式]语义突显度高的语言通常用一个可及性高的构式槽位来编码运动方式,如S-语言中的主动词、连动语言中的方式动词、双极动词(bipartite verbs)中的方式语素、Jaminjungan语中的方式前动词(preverb)、声响词等。对[方式]语义突显度低的语言来说,[方式]要素附属于[路径]要素(Slobin,2004:250-252)。样本中的隐喻运动方式动词在类符、形符数目上与路径动词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1)。在隐喻运动事件各目标域中,方式动词作主动词的频率明显超出非方式动词作主动词的频率(见表3)。由实证数据可知汉语属于方式语义突显度高的语言。
在运动事件编码过程中,不同类型语言对各语义成分的词汇化模式存在差异。S-语言常用卫星语素编码[路径],方式动词常出现在主动词槽位。如此以来,S-语言说话人在选择方式信息编码时的心理可及度较高。体现到形态-句法结构之中,S-语言中的方式动词会更丰富,出现频率也相对较高。相比之下,V-语言只在必要情况下才编码[方式]语义,对[方式]的关注度不及S-语言,尤其在跨界运动事件中,V-语言编码[方式]的词汇限制更多(Özçalışkan,2005;Slobin,1997,2004)。样本中可以作主动词的方式动词占62.38%,而可作主动词的路径动词只占23.33%(见表1),二者差异显著;方式动词总计31 类,而路径动词只有14 类(见表2),二者也存在显著性差异。汉语在运动事件词汇化过程中偏好突显[方式]语义,这说明汉语表现出S-语言的特征,因而支持了Talmy(2000:272)的假设,即现代汉语是很强的S-语言。
除方式动词外,样本中编码隐喻运动事件[方式]语义的其他词汇-语法手段(见例(2)f 和表4)从叙述风格上亦能体现汉语的类型学特征。例如:
(3)a.然而,稍停片刻,不经意间,那温馨的香味又轻轻[袭]来了。
b.歌声轻轻地[滑]过雪野,划破夜空,[飘]向很远、很远……
(3)a 和(3)b 分别通过副词“轻轻”、“轻轻地”修饰方式动词“袭”和“滑”,(3)b 末尾还用动词补语“很远”的重复形式来修饰方式动词“飘”。这些词汇-语法手段是对隐喻运动[方式]语义的增容和细化,使得方式意义更加生动形象。Slobin(1996a,1997)认为,V-语言的叙述风格倾向于描述为运动事件提供物理语境的静态场景,而S-语言则更多关注动态移动过程的描述。样本中的附加方式表达与方式动词在搭配中共现,使得运动方式进一步细化和精确,整个运动事件表达呈现出动态画面。这一独特叙述风格从侧面反映出汉语具有S-语言的特征。
2 [路径]与[方式]的此消彼长关系
Özçalışkan(2005:237-239)指出,运动事件词项中某一语义成分的编码会影响句中其他词项的选择。她认为[路径]语义要素的编码对方式语义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上一节论述可知汉语在形式-语义上对运动方式的注意力突显度较高,表现出很强的S-语言特征。由此反推汉语隐喻运动事件的方式动词占据了主动词位置,核心图式[路径]则被迫移位到方式动词外的次动词位置,其结果是路径动词通常语法化为表征[路径]的卫星语素,从而使路径动词的出现频率远低于方式动词的频率(见表1)。由此推断[路径]语义和[方式]语义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当[路径]语义突显度高时,方式信息被背景化,语言形式上[方式]语义更多通过附加成分编码;当[方式]语义处于前景位置时,[路径]语义要素通常位于次要位置,[方式]副事件将获得更多的注意力,其语言表达更加丰富多样。
运动事件中[路径]语义和[方式]语义的此消彼长关系在科学中亦有依据。Senghas,Kita 和Özyürek 于2004年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语言的本质:来自尼加拉瓜手语的证据》(Properties of Languages: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Sign Language in Nicaragua)一文,指出[方式]和[路径]是构成语言系统的离散性单位(discrete unit),这些离散性单位根据组合规则构成语言表达。这里的组合规则就是我们所研究的词汇化模式。他们研究了尼加拉瓜手语(NSL)的产生过程,发现在最初的产生过程中,[方式]和[路径]是同时表征的,后来二者按照先后顺序来表征,最终[方式]和[路径]可以单独表征。他们认为,这是语言进化过程中,离散性单位的发展过程,具有普遍性。
样本中的200 例隐喻运动表达总共包含210 个动词和动词复合体(verb complex),方式成分和路径成分共现的形符居多数,其中V[方式]+Sat [路径]模式形符数目为92,V1[方式]+V2-plus[路径]模式形符数目为27,总计119,占动词和动词复合体总数的56.7%。这两类类词汇化模式通常是[方式]在前,[路径]在后。样本中也存在方式动词和路径动词单独使用的情形,分别占动词和动词复合体总数的2.4%和23.3%。这种多样化的词汇化模式可视作汉语历时进化的结果。史文磊(2011)对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演化过程作了类型学考察,认为汉语表现出不断远离V-型而逐渐向S-型靠拢的倾向。

上古汉语表现出较强的V-语言特征,通常使用路径动词单动式,后世逐渐发生[运动]要素分离,[运动]要素分离以后,转由V1 表达,[路径]要素贮留在语法化为补语的V2 中,从而产生动趋式(S-型)。动词词化模式从综合性向分析性转化,导致路径动词封闭化(史文磊,2011:495)。由此可推断,由于位于第二位置的路径动词(V2)语法化的趋势增大,表征[方式]语义的V1 演变成核心的趋势增强(如表3所示),因而[方式]语义得以突显,而[路径]语义被弱化。这一过程也印证了Senghas,Kita 和Özyürek(2004)关于语言系统离散型单位进化的普遍性定律。
语言表达中[路径]语义和[方式]语义的此消彼长关系还与思维方式有关。汉语隐喻运动表达中“消”[路径]语义而“长”[方式]语义的特征反映出汉民族思维细腻的一面。样本中的31 类方式动词出现频率高达131 次便是证据(见表2)。当然,思维的细腻程度是相对的。由于汉语词化类型在转型过程中有些古代的结构或转化过程中的杂糅结构在现代汉语中遗存(史文磊,2011:495),汉语表达[方式]语义的细腻程度不及英语这种典型的S-语言。英语中的方式动词非常具体,而汉语中的许多方式动词是泛义动词,通常与日常生活相关,如“走”、“跑”、“飞”、“爬”等。汉语中的一个普通方式动词在英语中通常由有多个方式动词与之对应,如“走”(walk,drift,ebb,flounce,linger,lumber,march,meander,roam,rustle,stride,tread,worm one’s way,hike,pace,ramble,snake,trample,trot,swarm,forge,hurry,rush)(Özçalışkan,2005:219)。因此,为了进一步细化运动方式,汉语通常采用分析的方法,借助附加语言表达(见表4)来描述更精确的方式意义。
五、结语
本文基于语料库数据,对现代汉语隐喻运动事件中的[方式]语义要素作了考察发现:方式动词在类别上和总数上均明显超过路径动词和原因动词。汉语中还存在其他描述方式语义的表达,如副词、形容词、动词补语、重复等,这些表达通常用来修饰泛义方式动词,以描述更精确的方式意义。现代汉语可在不同语言表达层次上编码[方式]语义,因而属于[方式]语义突显度高的语言。这符合S-语言的类型学特征。据此本研究结论支持现代汉语偏重S-语言风格的假设,但与典型的S-语言(如英语)也存在[方式]细腻度的差异。
现代汉语隐喻运动事件方式信息在形式上和概念上突显度高的原因有二:一是汉语的词汇化模式偏好,二是汉语的思维方式。这两大因素在运动[方式]语义突显过程中相互映现,折射出汉语隐喻运动事件从概念化到词汇化的认知机制和类型学特征。本研究的结论进一步印证了Slobin(1996b)的“思由言限”(thinking for speaking)假说,即说话人对事件现有的语言编码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说话人会注意该事件的某些特定方面,这种注意习惯会随着时间的演化而形成某种叙述风格。
本文支持了Senghas,Kita 和Özyürek(2004)的观点,[方式]和[路径]是构成语言系统的离散性单位,这些离散性单位根据组合规则构成语言表达。但[方式]这种离散性单位的普遍性程度远远高于[路径]。本文为研究这种离散性语义元素开辟了一个新思路。
注释:
①Talmy(2012:15-20)指出,V2-plus 是汉语连动式中可单用作主动词的路径动词,其词法-句法地位与方式动词相当。如“钻挤进来”中的“进来”在单用时的意义和它作趋向补语时的意义一致。但V1[方式]+V2-plus[路径]这样的均等框架(equipollently-framed)模式在汉语中并不多见,方式动词作主动词仍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