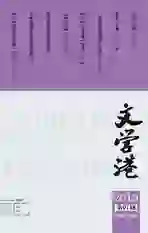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散文
2019-08-26南志刚
南志刚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4辑(宁波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第5辑(宁波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有四本散文集,分别为余姚方其军的《古境思旅》、慈溪潘玉毅的《纸上红尘》、宁海杨小娣的《这一片风景》、慈溪岑玲飞的《卸妆》。四位散文作家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书写对象,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话语场,都有了文体的自觉意识。拥有属于自己独立的话语场,是造就个性化文学世界的第一步。当然,作家建构文学世界的成熟程度和丰富程度\容纳人类核心价值和历史内涵的品质和量级,作家调取话语场资源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决定一个作家能否成为优秀作家。曹雪芹的“大观园”,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都是文学上特殊的话语场。我首先赞赏四位作者营构个性化话语场的努力,四本散文集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立足本土展开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个人与社会的对话,日常生活与艺术境界的对话,个人心灵与人类情怀的对话。
一
方其军游走于以余姚为中心的古老文化遗存,在古境中放飞思想和情感。这是一个能够“思接千载、心游万仞”的写作空间,面对河姆渡、田螺山、大运河、阳明故居、状元楼、白云寺、沈园等文化遗迹,书写对象“自带”厚重的文化意味和沉甸甸的历史内涵。如何打捞这些文化记忆,如何建立古境与今境的有机联系,成为这种书写能否成功的关键。值得庆幸的是,方其军找到了一种体验方式和表达方式,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重新讲述古境的历史故事,阐释古境意义和价值,抒发具有个性化的“幽古之思”。潘玉毅集中于书写“红尘”,或隐或显地表露出一种“出尘”的念头。拿到《纸上红尘》这本书,我有点诧异,聚焦于书写“红尘”可不容易,没有“超凡”之心,没有涤荡俗世雾霾的本事,一般人不敢用“红尘”这个词。读罢第一篇《永远的永和九年》,我在文末写下了一句话:精彩的永和九年,有一股魏晋文人的艺术气息激荡于行文中。相对于方其军以余姚古境为中心的话语场,潘玉毅书写的地理空间要开阔一些,有俗韵,有山水,有物语,有思悟,然這些俗、山水、物、悟,都有着明晰的文化地理空间,那就是以“故乡”为中心的江南,这“故乡”既是“身体”的故乡,如横河老街、屯溪老街、上林湖、南国的雨,更是潘玉毅的精神“原乡”,他对魏晋文人雅集有一股压抑不住的心驰神往,对“从前的”有一种近乎执念的留恋。于此,我觉得可以走进他的散文世界,与他一起去“听听那冷雨”。杨小娣《这一片风景》集中于书写以宁海地域文化为主体的“一片”风景,无论是“乡韵”“流年”,还是“遐思”,都带着浓郁的地域文化和现时生活烙印。“乡韵”中书写宁海的冬笋、海鲜,十里红妆民俗,西店,宁海武术,温泉,有着掩饰不住的骄傲与自得;“流年”多取材于身边事、身边人、身边景,感叹水月流年;“遐思”中集中了几篇文艺评论,有缅怀杨绛先生的悼念体,有追忆西南联大精神的回忆文,有阅读杨东标、阿门等作家作品的感受。杨小娣用细腻的文笔、平静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宁海的风土人情。读《这一片风景》,感觉杨小娣像一个江南小姑娘在做传统女红,那份专注,那份认真,那份气静神娴,那份自信与自得,令人“遐想”。当她写作的时候,笔记本、电脑就好像是传统的女红器具,一个个文字,仿佛就是千万条细若游丝的丝线,在不温不火、不急不躁的状态下,细细密密而又经络分明地编织着一片文学世界。我甚至有点坏坏地想:看你能将安娴静谧坚持到何时?没想到,读到文集最后,她依然没有激动起来。文学写作是一个最需要激动、最不怕折腾的“事业”,你怎么就不激动,不折腾呢?也许,是我对文学的期待发生了偏差,面对这样将安静坚持到底的散文,有点不太适应?岑玲飞《卸妆》可能是“卸妆”后的感性写作,全部都围绕着作者的个人生活展开,文学话语场相对集中、单纯。“戏曲风”写的不是戏里的故事,而是戏外的故事;“动物记”记述家养的动物,偶尔有几只野生的青蛙和虫子出现,基本找不到“动物凶猛”,是不是这个世界太温顺了?“岁月里”基本讲述身边人、身边事、身边物。这种全部聚焦于身边生活和身边体验,是不是一种强迫症的“自我设定”?感觉作者对自己太残酷了,这是一种艰难的写作,如果身边事身边人写完了,怎么办?也许,身边总有事总有人,怎样写也写不完。
二
方其军的写作非常用心,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选材集中,书写对象非常稳定,古境思旅和县城书写都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他善于通过具有时间跨度的题材做文章,通过“咏古”抒发带有哲学思考和历史意识的思想和情感;第二,每一篇散文都引用一句“名人名言”,放大了“古境”的观照视野,如《河姆渡:海洋的向度》引用布罗茨基《无题》的句子:在沼泽地的中央,有座被你遗忘的荒寂村庄。这个沼泽地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沼泽地,也是历史时间的沼泽地,既切合河姆渡,也表明像河姆渡这样的“荒寂村庄”长期被埋没、被忽视,不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有现象,而是世界文明史的普遍现象,方其军观照河姆渡的视野超出了余姚、超出了浙江、超出了中国,进入人类文明史的广阔领域。《再热一壶糯米酒》引用张枣《预感》的诗句:像酒有时预感到黑夜和他的迷醉者,未来也预感到我们。农家的糯米酒一下子具有了穿越的力量,将过去、现在、未来串联起来,将亲情、诗意、少年经验和酒神精神连接起来。
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古境思旅”这样的散文最难写,因为传统很久远,成功者很多,要有所突破不容易。且不说中国古代文人发愤著书,抒发过太多的幽古之思,陈子昂登上幽州台,咏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假托李白的作者也写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王国维曾慨叹: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当代散文家余秋雨有《文化苦旅》等散文,被部分人视为“大文化散文”“文人散文”的代表。历史散文写作首先需要准确的历史知识,不能推测臆想,更不能想当然。抒发幽古之思,容易走向宏大,一不小心就被书写对象带走了,作家的主体意识滑落在历史的长河里。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向方其军提点建议。第一,尽可能避免大词,切近内在体验,用自然的笔触,将心中所思所想说出来,与读者平等交流。在《古境思旅》中,有些词语过大,我没看清楚,“一柄断桨,划了六千五百年。一束稻谷,香了六千五百年。一枚谷笛,嘹亮了六千五百年”,没看懂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特别是与题记中引用布罗茨基的诗句相龃龉,“被遗忘”的意味在这里荡然无存,且与中国六千五百年的历史发展,不完全对应。这六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有过辉煌,有过灿烂,但更多的是苦难,是纷争,是贫穷,特别是对于像河姆渡这样偏远乡村的村民而言,朝代更迭,城头变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夸饰性的表达,实际意思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来。“姚江清清亮亮流淌,映照七千年前的某个暗夜”,这样的表达,让我在云里雾里翻跟头。“地图上,那湛蓝的经脉把我迷住了。我把地图比例一再调小,中国版图就呈现在眼前,就像在天宇俯瞰华夏。”将场面搞大了。第二,个人体验应该建立在相对准确的历史地理知识基础上,经得起推敲。散文不是历史著作,当然不会要求严谨的学术知识,但基本的知识规范还是需要的。“如果说长城实现了中华版图的相对静止,那么,大运河搅动的是中华疆土的生龙活虎”。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秦汉帝国阶段,第二阶段是唐宋帝国阶段,第三阶段是明清帝国阶段,在明代前期的漫长历史阶段中,中原帝国与西北少数民族的矛盾贯穿其中,长城作为冷兵器时代的防御工事,的确起着至关重要的军事文化作用,但是,长城内外,绝不是安静的,围绕长城的战争总能卷起轩然大波,甚至直接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走向,长城也没有带来中华版图的“相对静止”,其间的动荡、流血是中国历史叙述的主要内容。“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最初或许只是隋炀帝某个夜晚的突发奇想”,这种很有想象力的“文学表达”,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建立在臆测臆想基础上。第三,有些地方感觉到“文不逮意”,表达不够完整。“十年来,我已经记不清见到或者去过几次田螺山遗址。每一次,心里总会有一种猛然灵醒的感触。就像少年时期,我骑着自行车去瞻仰河姆渡遗址。阳光与轻风,浸润了我一路的遐想。”但是,在这段文字的后面,作者一直没有交代“感触”“遐想”的具体内容,哪些感触?遐想些什么?才是对读者有所启示的核心内容,只说我有感触、有遐想,却没有内容,造成叙述空白,而这个空白却是必须交代的。
三
杨小娣的特点是文笔细腻、闲适从容,特别是在“乡韵”这一部分。在这里,我想从两个方面提点建议。第一,引入生态美学意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在思考层次和境界上,在向深层“开掘”。《金衣白玉冬笋鲜》《透骨新鲜宁海鱼》等文章,侧重于介绍家乡美食。关键是在行文中,太过于突出“吃”了,本来写宁海处于象山湾、三门湾怀抱中,濒临东海开阔汪洋,山海资源十分丰富,适合万物生长,有“贝类之乡”“鱼米之乡”的美誉。但一句“生态美食的天堂”,把虾贝类生物归入了“吃”的行列,水质优良不是对虾鱼而言,而是对“人”而言,鱼儿长得缓慢,肌肉更加坚实,肉质更细腻。描写“西施舌”一段文字,写蛏子的体型神态,笔法细腻,但仍然归之于“味道鲜美”。作为美食介绍或美食节目,如“舌尖上的中国”,这样写没有问题。但散文是文学艺术的一种样式,首先突出艺术情怀,在题材选择和主题提炼等方面,需要有更加深入的思考。在生态天堂,万物秉天地之气而自由生长,是一种生态美学,但如果归之于美食,就不免人类中心主义了。生态主义和人类发展如何平衡,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大课题,在这方面,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就很有意味,高粱酒转化为人的精气神,成为高密东北乡人们不屈不挠斗争的动力。帕蒂古丽的《隐秘的故乡》在这方面也有所思考,《肉与铁的对峙》将铁器(人的意志)和羊、牛(自然生态)放置在“冲突”的两方,作家有太多的无奈和沉思,尽管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但作家的困惑也是人类的困惑,是文明的困惑,具有生态学和人类学的意义。第二,在写作每一篇散文的时候,注意文气贯通。“气”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人生观的核心概念,天地有气而孕生万物,万物有气而生生不息,文章有气而鲜活生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文气贯通,对一篇文章来说至关重要。《七月流火,八月未央》一文,开篇大氣,有思接千载之意:七月流火,八月未央,九月授衣,《诗经》的句子可以发幽古之思,可以循宇宙之变,在一个相对宏观的时空中体验生命。而紧接着一句:“今夏,温度屡次飙上四十度,浙江境内持续高温”,突然将时空沧桑感解构了,把相对宏大的历史时空拉近了高温现场的固定时间中,文气遽然下沉。接下来,用细腻的笔法叙述了乡村消夏的生活场景,文气又是一变,空间进一步缩小。最后,得出如下结论: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修炼。这话说得没有问题,就是距离心灵鸡汤不远了。从引用诗经的“七月流火,八月未央”,到最后的心灵鸡汤,文气越来越弱,一个大境界的时空开头,引出的是越来越弱的内容。让人读起来,怎么也不过瘾。
四
在四本散文集中,我最喜欢读的是潘玉毅的《纸上红尘》。潘玉毅在选材层面具有历史纵深感和空间大跨度,在情感体验层面有典型的文人气质和江南情怀,追古抚今中有对现状的冷静思考和批判精神,行文中有古典诗词的意趣。这些,与我的性格意趣有点类似,我产生一种“心有戚戚然”的感觉。《永远的永和九年》追记一千六百年前发生在兰亭的那一场文人雅集,“有人临流赋诗,有人言志,有人载道,有人放浪形骸、引吭高歌”,而王羲之《兰亭序》行文的洒脱与豪迈,把这次朋友聚会定格在中国文化史上。潘玉毅不是单纯地叙述历史故事,而是在叙述中不断发掘绽放新的思绪,在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里自由地舞蹈,极其自然地将古今连接起来。或透出文人式的自信与洒脱:“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人们早已经忘记了中国历史上出过多少个帝王将相,忘记了会稽山境内历任的市长、县长,唯独对兰亭集会和《兰亭集序》记忆犹新。”让我想起曹丕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岁有时而终,荣乐止乎其身,不如文章之无穷。”或透出对现实的深层忧虑:“会稽山还在,兰亭还在,曲水流觞还在,只是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临流赋诗的才气和豪情。”是啊,会稽山破败了,可以修整,兰亭倒塌了,可以新造,一代一代文人的才气和豪情泯灭了,到哪里去寻找?潘玉毅在这里不仅揭开中国历史的大课题,也揭开了当代生活的大课题。许多文化人怀念晚明江南士子,追忆民国大家风范,西南联大的诗人圈子成为热点,有人要重返八十年代,不是偶然的。而对于作者自己而言,他的遗憾是:徒有一段与古人畅叙幽情的情怀,来去匆匆,与“永和九年”至今未遇。唯如此,才是“永远的永和九年”。《横河老街的记忆》一路洋洋洒洒叙述了“那个年代”的人、事、物,而一句“这个藏有回忆的地方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了”,颓败的老街与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给“现实”画出了极不协调的图画。《故乡书》里那些朴素而有意味的句子,几个“有”字,将慵懒闲适恬静自然的乡村记忆呈现出来:“老屋后面有池塘,池塘边上有柳树,柳树上有鸣蝉,蝉声过处有大黄狗和牵着大黄狗的打盹人”。“从前的水能养人,也能滋润群山和草木”,“现在的水”能怎样?作者要回家,回到那“飘着墟里烟的远人村”,那里“是我们的来处,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归处”。潘玉毅的骨子里,有一种乡村情怀,相信许多人都有,但是,我们还能回去吗?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环境变了、制度变了、人也变了,我们自己何尝没有变化?他所追忆的“永和九年”,只有在情感记忆中,才能永远。《听听那冷雨》,从北国的秋雨,写到南国的秋雨,化用古典诗词意境,诗意地传达了思乡之情。北国的秋雨像白居易的《琵琶行》,南国的秋雨“说不尽的古色古香”,化用戴望舒《雨巷》的场景。这篇散文趣雅,韵味悠远,满足了我的阅读期待。
五
四本散文集中,岑玲飞《卸妆》写得最为感性。感性,当然不能用简单的“好”和“不好”来判断。文学艺术首先需要的是感性,感性体验的丰富性、真切性是作家区别于常人的地方,至于如何表达这种感性体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将个人在具体语境下的感悟,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化的经验,也就是歌德所说的从个别到一般,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感性体验的真切性,来源于细致入微的观察,来源于特殊语境下心灵的突然悸动,来源于观照主体与观察对象在某一瞬间的联通,来源于写作者在日常生活基础上形成的“稳定注意”。有时候,对于我们而言索然无味的事情,引不起我们注意的事情,作家却孜孜以求,从司空见惯的人事物中,体会出一种独有的哲理和人生况味。罗丹曾经说过,所谓大师就是这样一种人,他能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事物上发现美来。岑玲飞是一个具有细密观察眼光的人,她的关注点与我们不大一样。她的关注点集中于二胡独托的“慢”,慢到仿佛有千钧之力也拉不回来的地步,“细细一缕马尾,在琴弦和琴筒上不易察觉地擦过,像年近百岁的老人那样举止缓慢,又像巨轮拖着的一张大网,忘了几百斤的鱼虾,那么沉,那么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怎么也来不快,只能一分一毫地移动”。她聚焦于主胡的手,十分细长,很白,手势很低调。她注意伴舞演员的“快”,一个“快”字写出了伴舞演员的辛苦。在她的艺术记忆中,黄美菊《鼓上貂蝉》的刚硬感具有美的差异性。台柱子黄荣抖水袖的动作灵动飘逸,有造型感,有时如激流,水花四溅,有时稳重沉静,如无风之水。水袖服帖了手,手与水袖,如鱼和水、花和枝叶、明月和清风,非常自然。用这句“非常自然”,给黄荣抖水袖秘诀提供答案,“功到自然成”。她注意到旧越剧的味道,就在于“旧”。这些对每一个具体场景的感性体验,岂能没有长期的稳定注意,没有理性思考,没有人生积累在其中?将真切的感性体验,长期坚持下来,就会呈现出生活体验的丰富性。岑玲飞是一个有心人,对生活有心,对写作有心。坚持有心,用心写作,她应该走得更远一些。集子中有一篇文章《关上阳台门,写》,我对岑玲飞的建议是:打开阳台门,写;打开所有的门,用心写。
六
点评了四位作家的散文集,我还想说一说我自己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散文,或者说我以为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散文。
在所有文学的领域里,散文最容易入门,似乎拿起笔来就能写,但写过散文的人都知道,散文最难写。有人说,散文就是形散而神不散,也有人说形散而神亦散。不论哪一种理解,都提到散文中形与神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主张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将神提到文章灵魂的地位,这个神就是精神气质、胸襟眼界。现代美学,特别是受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英美心批评、语义学等影响的美学,消解艺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鸿沟,主张艺术形式就是内容,形式中积淀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这些历史内涵,在埃里希·弗洛姆那里,是人类普遍经验的象征,在乔治·桑塔格那里就是“艺术的生命欲望”。如何从个体生活和生存体验中,见出人类普遍经验,见出历史和时代的“集体”记忆,而又能保持个体体验的完整性、丰富性和独特性,是艺术创造的根本性命题。
具体的散文写作,第一要处理好小与大、少与多、近与远、具象和抽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这么多关系,实际上就是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从写作者角度而言,胸襟、眼界、沉思、情怀是关键。可以从身边事、身边人、身边物出发,但一定要突破身边事、身边人、身边物,突破日常思维,进入更为广阔、深邃的空间。有个人独特趣味,当然不错,但远远不够,要有气象,有坚守。这,无疑很难,但如果走上写作散文的路子,就一定要有這个追求。
第二,语言文字要有力量,有趣味。文学是语言艺术,首先是艺术,不是语言,语言达到艺术的程度,才能成为文学。艺术语言具有艺术精神、艺术趣味。艺术精神是什么?曰万物平等共生意识,曰生态竟美意识,曰人类终极关怀,不能用底层关怀(关怀一部分人)代替人类终极关怀,不能用等级性的价值观代替平等性价值观,不能用人类中心主义抹杀万物生存权利。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许多散文、诗歌、小说、戏剧,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艺术趣味是什么?曰雅致,曰力度,曰美畅,曰滋味,曰正奇。而个性,倒在其次。我们常说的“文雅”,就是一种趣味。艺术趣味和艺术精神是统一的,其核心是自觉、自由。
第三,文气要贯通、要淬炼。文气关乎散文的气质、气韵,关乎散文的运思方式,涉及诸多内容。我这里只说一说文气流畅与文气凝滞的问题。写文章的时候,文气流畅与凝滞是一对矛盾,是矛盾就具有矛盾的同一性,不仅仅有矛盾的斗争性。好的散文,一定是文笔流畅的。但这种流畅不是“生活流”,不是闲话一箩筐式的流畅,而是作者遇到了常人所遇到的凝滞处,破开了这个凝滞,进入一种新的流畅境界,方能成散文。所以,当我们在写作散文时,如果一路顺畅,高歌猛进,可能就要警惕了,要问问:这是不是散文?韩退之为文,往往凝滞不前,突然破开,让人惊喜,故其文多险峻处,几近死去,突然于绝境中生出。苏东坡的散文,文字浏亮,但文气往往几经转折,可见构思时曾几度凝滞,奋力破开,方才成文。《前赤壁赋》那种矛盾、那种纠结、那种无奈、那种无解,突然来一句:“相与枕籍乎舟中,不觉东方之既白”,心境赫然开朗。
现代白话文开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人强调流畅、白话、口语化。然而,胡适之文,有坦荡之气,周作人之文(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有散淡之气韵。他们的文气,不仅贯通一篇文章,而且,贯通自己的人生实践,“文如其人”啊。文气不仅是一篇文章的气质气韵,是一篇文章“生命”流转的核心指标,更是一个作家的全部生命实践的标识,也许是许多人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