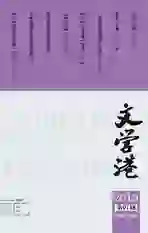银杏烂漫
2019-08-26陈典
陈典
秋意最浓的时候,银杏树干中间会伸出几条臂膀般的枝权,将密密的树叶撑开,黄得透亮的银杏叶茂盛层叠,小扇子似的迎风招展。秋日霞光倾泻到伞形树冠上,璀璨夺目,犹如一朵金色的祥云,悬在暮霭之中。银杏的美恰在秋天发挥到极致。
我在心中努力搜寻古人状写银杏的句子,却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结果。其实,就连一代文豪郭沫若也有过类似的感叹。他在现代诗《银杏》中写道:“我在中国的经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我没有读过中国的诗人咏赞过你的诗!我没有看见过中国的画家描写过你的画。”的确,与众多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植物相比,银杏的地位并不突出,在《诗经》《楚辞》中也不见其踪迹。銀杏的“低调”令人并不甘心,反倒激起我更多的兴趣。我试图在古典文本里,爬梳出一些关于银杏的线索。
原来银杏打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叫“银杏”,“枰”是它最早的称谓。比如西汉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列举汉朝皇家园林栽植的树木,其中就有“华枫枰栌”的记述。唐朝初年的经学家颜师古有注解:“枰,平仲木也。”而“平仲”是唐代之前文人对银杏更流行的一种叫法,唐代学者李善编撰的《文选》中有“平仲之木,实白如银”之说,肯定了平仲木就是银杏树。西晋的文学家左思在《吴都赋》中也有“平仲桾櫏,松梓古度”之句。“平仲”之谓颇值玩味,在当时“仲”字往往是指在弟兄之间排行老二的意思,用称呼兄弟的办法去命名一种树木,确实像是魏晋名士的行事作风。
非独文字,南京博物院所藏的六朝砖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也出现了银杏的形象。画中八位名士席地而坐,两人之间以树木相隔。其中银杏树最多,一共出现了五棵,足见其深受当时士大夫的垂爱。据艺术史家考证,砖画中银杏的表现手法和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背景相同。《洛神赋图》中的银杏数量相当丰富,或一棵独立,或几棵一组,前后呼应,富有节奏,极具变化。若再往前追溯,不难在汉代的画像石里发现刻画银杏的内容,比如《徐州汉画像石》一书中收录了汉画像石270余幅,其中表现树木的有22幅,银杏就占了16幅。古人早就认识到银杏的古老长寿与坚韧不拔,数百年的光阴从它们身旁流逝,银杏树依然挺拔高大、永葆生机,自然而然就成为承载人们祝福的嘉木。而银杏的守护总是静默深沉的,如同它那并不彰显的声名一般。
直至宋代,在文人诗歌中银杏才频繁出现。银杏在宋代与文人的生活联系得非常紧密。当时银杏主要盛产于宣州,北宋初的诗人梅尧臣恰是宣州宛陵人,不遗余力为自己家乡的特产搞宣传做推广。其诗中就多次提及银杏为其故乡风物:“鸭脚类绿李,其名因叶高。吾乡宣城郡,每以此为劳。”这里说的“鸭脚”其实就是银杏。因为银杏的叶缘是一种轻快流畅的波状线,而叶片上的叶脉从叶柄顶端辐射出去,普遍出现了缺刻成两裂的,如同折扇的骨架有奔放之感,小巧玲珑更似是鸭掌,“鸭脚”这一昵称便由此而来。不过那时银杏在北方的都城汴京还是稀缺之物,梅尧臣收到故人馈赠,甚至发出了“赠我比珠投”的感叹。而梅尧臣的大力鼓吹起到了效果,后来竟然一跃成为贡品。欧阳修曾在《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中对此有详细记载,他写道:“鸭脚生江南,名实未相浮。绛囊因入贡,银杏贵中州。致远有余力,好奇自贤侯。因令江上根,结实夷门秋。始摘才三四,金奁献凝旒。公卿不及识,天子百金酬。”
“银杏”的得名也与这次进贡有着莫大关系。南方官员以鸭脚子呈奉汴京皇室,皇帝问是何物,进贡官员深恐“鸭脚”名称不雅,惹恼皇上,急中生智,根据形、色对曰:“银杏。”结果,龙颜大喜,厚赏了进贡者,银杏这一雅号也被广泛沿用至今。元代王祯《农书》中也有“银杏之得名,以其实之白”,“鸭脚取其叶之似”,“其子至秋而熟……果如绿李,积而腐之,唯取其核,即银杏也”之类的论述。
天子喜爱,文臣效仿,于是对银杏的颂咏逐渐流行。宋代阮阅的《诗话总龟》记载:“京师旧无鸭脚,驸马都尉李文和自南方来,植于私第,因而著子,自后稍稍蕃多,不复以南方为贵。”这位李文和,据《宋史》记载,就是驸马都尉李遵勖。其人进士出身,很有才华,广交文士。他在成为文人聚会核心的同时,也在自家园林中观赏银杏,甚至还在宴会上将鸭脚子分给文人享用,由此诞生了不少以银杏为主题的诗篇,可以说李遵勖对银杏的文学传播功不可没。
由于其种植地域的限制,银杏虽树不像松柏、杨柳那样为文人熟知,频繁吟咏,具有浓郁的人格化倾向,但银杏树干高耸入云,银杏叶夏绿秋黄,色彩鲜明,寄托了诗人春华秋实之欣喜,节序如流之感伤。可以说,到了宋代,银杏首次占据了诗人的审美视野,宋代文人赏玩银杏也成了时尚。吴芾就写道:“新买湖头十亩园,绿阴罅里见青天。金樱相亚枝枝袅,银杏低垂颗颗圆。仰看乌鸢翔古木,俯窥鸥鹭戏晴川。便须临水营台榭,要与渔樵乐暮年。”
临水的亭榭是休憩之所,银杏临水而栽也颇有讲究。文人凭栏驻足,透过银杏的枝叶仰望青天,飞鸟盘旋,渔樵之乐尽在意外。
此外,银杏因树势雄伟高大,叶形秀雅美丽,树龄长寿千年,与僧侣修心养性的信念不谋而合,具有“法轮常转”、不受凡尘干扰的宗教意境,被尊崇为“佛树”,视为中国的菩提树,而广为种植保护,成为寺院文化的一部分。宋代文人与佛寺的关系非常密切,多喜好去寺院游览、小憩、会友、参禅。银杏自然而然也就进入他们的创作视野,并点缀着宋代文人的生活。宋代诗僧慧空就有一首关于银杏的哲理诗:“蟠桃一实三千年,银杏着子三十载。老僧只作旦暮看,汝莫匆匆宜少待。阶前始芽今出屋,便是携篮走僮仆。伴我东园看菜归,与汝煎茶剥柔玉。”银杏三十年才能结果,诗人种银杏却不能享受到银杏的果实,有人对此事表示不解甚至有取笑的意味,但是诗人却从中悟出了佛教的无差别境界。以佛眼观,亿万年无异于一刹那,何况区区三十年?今天种下,明天摘果也是可能的,若是拘泥于实体的果实,反倒会错过修行上的成果。
银杏因为结果十分缓慢还得了另外一个“外号”——“公孙树”,爷爷年轻时种下的银杏树在他有孙子的时候才结出了果实。明代周文华编撰的《汝南圃史》一书中,就提到银杏有“公植而孙得食”的记述。“玉纤雪椀白相照,烂银殻破玻璃明”是对银杏果色白透亮的最佳写照,它不单在外形上令人赏心悦目,还可入食。而银杏果的味道淡甘微苦,特别符合文人的审美趣味。杨万里就曾写道:“深灰浅火略相遭,小苦微甘韵最高”。古贤嗜好层次复杂的滋味,这种幽淡苦涩与微薄甜美相互交织的体验正能投合文人含蓄雅致的情怀。此时,银杏承载的就不仅仅是食物之味,而是着上了文人特有的审美理想。
银杏在南宋之时是煨熟之后食用的。所谓“煨”,就是把生的食物用余烬、热灰、热沙或热石裹起来慢慢烤熟,“深灰浅火略相遭”就是对这种方法的准确描述。我们现在也会有烤银杏果的做法,在烘烤之前将果壳一个个夹出裂口,以防在加热的时候突然炸开。煨好的银杏很容易脱壳,里面的果肉由翠绿转而深绿,果衣焦红,清香催发,尤其适合与茶、酒相配。银杏入食在当时成为一时风气,诗文中多有体现,例如陈师道《寄潭州张芸叟二首》中有“秋盘堆鸭脚,春味荐猫头”,冯时行《和食筍二首》中有“麞牙鸭脚色相鲜”,张镃《珍林》中有“李枣栗银杏,橙梨柿木瓜”,方回《送郑君举宣城教谕》中有“红花木瓜银杏园,年年包贡入中原。”
银杏也理所当然进入到宋人的茶戏当中。当时茶文化异常兴盛,茶道较之前代已经颇有不同,宋代陶谷《清异录》就记载了名为“漏影春”的点茶方法:“用镂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珍物为蕊,沸汤点搅。”茶不仅要让人品尝高兴,还要让人观赏愉悦。点茶布置很讲究图案的美观,所以宋人想到用银杏等干果进行装点,用匠心求韵致。当然,银杏除了作为点缀物,也可作为茶食,陆游在《听雪为客置茶果》写道:“青灯耿窗户,设茗听雪落。不饤栗与梨,犹能烹鸭脚。”寒夜漫漫,烛光幽幽,窗外落雪无声,屋内品茗有味,间或吃几个银杏果,微微苦涩衬得茶香醇厚浓郁,这是一种多么闲雅的人生情味!
现在我们一般都把银杏的果实叫做“白果”,其实这一称谓到了元代才开始出现。李杲的《食物本草》中首次记载了“白果”一名。当时银杏药用盛行,元代太医忽思慧所写《饮膳正要》十分推崇银杏的食疗功用。到了明朝,银杏被被李时珍收入《本草纲目》当中,他写道“白果生食降痰、消毒杀虫,熟食润肺益气,定喘咳,缩小便,止赤白带下,嚼烂涂于手足治皱裂”,此后“白果”之名大盛。在宋人的“煨”与“烹”之外,银杏还被开发出了更多的食用方法。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记载:“惟炒煮作粮食为美,以浣油甚良”。清代陈淏子《花镜》则记载白果“核形两头扁而中园,或炒或煮而食俱可。”白果可与猪、羊、牛及禽类食物相配,采用炒、蒸、炖、烩、烧等多种烹饪方法,制成各种美味佳肴,如山东郯城的“蜜汁白果”、四川清城山的“白果炖鸡”等等。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孔府菜馔”中色香味形俱佳的“诗礼银杏”。
这道银杏菜品颇有寓意。据传孔子为了教儿子孔鲤学诗习礼,曾谆谆教诲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主。”至宋代,五十三代衍圣公孔治在孔庙内修建起了一座“诗礼堂”以表不忘,并在堂前亲植两棵银杏树,东为雄树,西为雌树。到了后来,两树长成,春华秋实,硕果累累,收获甚多,为孔庙增色不少。这些果实也不同寻常,不仅个大饱满,而且格外香甘。孔府的厨师将树上的银杏摘下,趁鲜去除外壳及果内脂皮,将果仁放入开水锅中氽过,除去异味,放入白糖、蜂蜜调制的高汤中,慢火炖至酥烂,直至色如琥珀再摆盘装点,有人谓之“蜜蜡银杏”。不过,第七十五代衍圣公孔令贻却对此菜不满意,他认为菜品味道虽好,但菜名浅陋。因银杏取自孔子“诗礼庭训”故地,于是他将此菜改名为“诗礼银杏”,藉以纪念先祖诗礼垂训,又可表达孔子家族诗礼传家世代不衰,这道菜也名声大振。
到了明清,提到银杏的诗文增多,例如元末明初的刘基在《次韵和新罗严上人秋日见寄》中写道:“银杏子成边雁到,木犀花发野莺飞”,孙作《送人往宣城》中有“送客宣城郡,吟诗忆土风。雪肤银杏白,火颊木瓜红”,吴宽《谢济之送银杏》中记“错落朱提数百枚,洞庭秋色满盘堆。霜余乱摘连柑子,雪里同煨有芋魁。不用盛囊书复写,料非钻核意无猜。却愁佳惠终难继,乞与山中几树栽。”事实上,南宋以降,由于战事迭起,灾害频仍,人们甚至从银杏树上寻找精神寄托,对银杏产生崇拜并赋予神化。据明代《昆山县志》载,蒲城的一棵白果树系由仙人“掷枝垂生”。同载汴人龚猗,官殿中侍御史,曾护从宋高宗南渡,途经昆山,折了一枝银杏插在地上,祈祷此枝能长成一棵大树,后果然灵验,并得白果七十余颗,据说恰恰是他的子孙嗣世之数。后人称此树为“遇仙树”。人们出于感恩和敬意,会自然流露对银杏树的崇拜。清朝的乾隆皇帝就曾经题诗赞颂北京西山大觉寺的“银杏王”,诗曰:“古柯不计数人围,叶茂枝孙绿荫肥。世外沧桑阅如幻,开山大定记依稀。”
如果说稗官野史记载的是传说轶事,那么在江浙沿海一带银杏树则实实在在成了当地生民心中的依靠。上海吴淞口、杭州钱塘江两岸和太湖岸边,不论村旁和旷野,常有零星高大的银杏树,可为穿行于风口浪尖的渔民指引航向。江苏启东的一些庙宇,多有银杏栽植,挺立在长江岸边,常年江风吹袭之,致其树冠偏斜一方呈扫帚状,人称“扫帚树”。在捕鱼归来的海路上,人们最急切找到的目标就是“扫帚树”,它像渔家的保护神一样,祝愿渔民满载而归,平安吉祥。每次顺利返航,渔民们总要到“扫帚树”下烧香祭拜,敬树如神。
不论是在诗文里、图像上,还是故事中,银杏都是深受尊崇的。只是平日消隐于纷乱尘世间,只在秋日遍染金黄的时候灿烂一现。那一日,虬怒飞扬,舞云千霄;那一日,蠖曲起伏,蟠栖岩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