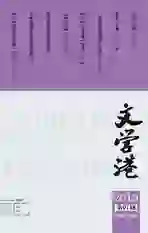大陈
2019-08-26丁真
丁真
星光如此璀璨
船行驶了近两个小时,舱内人满为患。没有呕吐感,也不头疼。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乘客们对自己的状况都很满意。
选择在烈日和暴雨交替之日上岛纯属偶然,但亦属幸运。白天,天空的蓝和天空的白被烈日烤得纯净;傍晚,风卷着如注的雨将一天的微尘洗清。
坐在梅花湾的露天排档,看着夕阳从大风车的背后滑落,排列有序的渔船似乎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倒影长长地投射在海面上,随着水面波纹荡漾,缓缓地,一层一层展开。
热闹的人群,在兴奋地手舞足蹈,当最后一线太阳余晖从每个人的脸庞扫过,夜,终于来了。
一罐啤酒。大盆小海鲜。
风带着太阳余温拂过发梢、耳垂、眉角,坐在躺椅里,大口喝着啤酒,感受着最后一丝光在眼前消失殆尽。
热浪滚滚的白天终于正式结束,晴好的夜晚正式开始。
真正的“鲜”永远且必须是水煮的——为了保持它们的原汁原味,保证鲜汁美肉一滴不漏地全部被吮吸到嘴里。舌头在其中搅动多次,再经磨牙咀嚼后,味蕾能充分享受这其中的温和香甜。
过一会儿,啤酒喝完了,不需要你起身去拿,也不需要纠结于是否该一次性拿两罐啤酒,纯朴的服务員会直接给你带来一箱,或一打。这是大陈的好客之道,也是椒江的、台州的。
在装得盆满钵丰的海鲜面前,哪怕宿醉一回,又如何?
海岛的风,慢慢地,扯开了天上稀薄的云层,深邃的蓝色夜空里出现了密布的闪亮。
长长的队列从梅花湾的排档出来,步行回别墅区,队列里有熟悉的身影,漫步于海岛公路,时而在满天繁星下停驻脚步,时而侧耳去倾听来自自然的声音。
海面有风吹来。海风轻吹树叶,发出簌簌响声,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虫子齐声高歌,聒噪地鸣唱着夏日二重奏。微弱的浪声诱惑着鼓膜,让封闭的世界渐渐打开大门。
浩渺的银河中,为何大陈头顶的星光如此璀璨?
跟上熟悉的步伐,抬头仰望海岛天空,那是夜空中闪亮的星河,是流光溢彩的晶亮世界,星空中,仿佛藏着一张张聪明睿智的脸,咧开嘴冲着你笑。慢些,再慢些走,像醉了酒,用心去感受天与地之间的人。
相信我,当有一天,你遇见大陈星空的时候,请一定要驻足抬头,因为,这些地方蕴藏的奥秘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不禁一次又一次问自己:“为什么这里的星光是如此璀璨?”
渐渐远去队列中,熟悉身影停住,转过身,走向了与队列相反的方向,身影淹没在夜色之中。
星光闪落了下来,一点一点亮晶晶的,撒满海岛的路上,在化学物质和荷尔蒙产物的作用下,夜的草丛,仿佛恢复了斑斓色彩。
于是,穿过大陈岛的海风,慢了脚步。
行进在历史隧道中的垦荒精神
A
椒江东南方向的东海海面上。大陈岛。
黄蜡色的裸露着的岩脊,一条条深邃的岩缝,在蔚蓝色的天空和动人心魄的碧波大海的衬托下,显示出旷远的宁静与永恒。
漂游的蜃气。一条条细长的白浪前仆后继、无声息地翻涌着,彰显其恐怖的力量。生与死仅一瞬间,短暂与不朽却永恒相对。
这是岛上的一块干出岩。
甲午岩。岩壁陡峭,双岩微斜,海水冲击,浪花从双石夹缝中跃起,一遍遍地冲刷着岩壁。这里距离海门县城只有五十多公里,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片片绿地,一棵棵绿树,或成片,或单列,林木葱郁,森林覆盖率达50-60%以上。
这是东海上的绿色森林,是一颗绿色的海洋明珠,也是几代垦荒人创造的出神入化的生态艺术作品,是多少年来他们的精神栖息地。
一双双粗糙且长满厚茧的大手,一张张善良淳朴的面庞,这就是全部的守护么?
B
空白。岛上是一片又一片惨森的空白。
彼时的大陈岛。战争的销烟仿佛依稀可见,地雷、地刺网随处潜伏着。
废墟。令人心惊胆战的荒芜,令人胆战心惊的死寂。没有人,没有路,没有船,也没有声音,除了海岸线上光秃秃的岩石,还有满目的破烂和垃圾。崎岖艰辛的山路,似乎要把这座荒岛以一种冷峻的姿态保护起来。
他们来了。这群热血沸腾的青年,注定将留下宝贵珍藏,子孙后代享用。
下地种田、饲养牲畜、修路盖房……将一块块巨大的空白填满。这座岛经历了战争,经历了炮火的洗礼,而今天,这些苍凉在那一双双满是茧子粗糙的大手中,永远地消失了。
C
每一个垦荒人,都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
62年前:一方孤岛,四周是茫茫的海,身边除了荒草还是荒草……几乎让人失去继续的勇气。可即便是这样,山上所有的地都已经开垦了,小麦种子播下去了,番薯也摘了,花生也摘了,拉网捕鱼也完成了。无数个血泡,磨破了,流出粘稠的液体,来不及长好新皮肤,又磨出一排血泡……周而复始,长期的压迫和摩擦最终在宽大的手和脚上密密匝匝地结出一层又厚又硬的扁平角质增生物——老茧。
今天,在大陈的地上地下,留在60年历史汹涌的浪涛中,镶嵌在岁月高高的陡壁上,熠熠发光的,正是他们的身躯。
我们也许认识到他们的勇敢无畏,但我们仍不算真正感悟到他们留下来的另一种价值。就像岁月之河不可倒流一样,这种历经历史长河淘洗却永不褪色的价值也不会再有。它超越金银,凝炼成一种博大精神又价值连城的信念支柱,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象征。
如果没有这样一群人,大陈的历史将是怎样?我们无法想象。
D
从无到有。
度日如年的朝夕之间,他们在静静地重复着他们的人生。
青春与热血,组成了他们前进的长长隧道。
而死亡之神的灼灼目光,便埋伏于这长长隧道上,寻找每一个机会,伺机而动,无论是风轻云淡的晴日,还是月黑风高的暗夜。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每天都是同样的险恶,每天都必须拿出过人生最后一天的勇氣来面对。
船小。浪大。两天三天四天。呆在茫茫海上。吐,一直吐,吐到胃液倒流,吐到喉咙口的毛细血管也破了,吐出了血。但即使这样,也得吃,吃完,接着吐,吐完,还得吃,每一顿饭都在痛苦和挣扎中完成。你必须自己去适应,没有人会同情和帮助你。因为,每个人都到了生理的极限。
地刺网。遍布。你永远不知道哪块地下会有突然袭来那一声响雷。痛到昏厥,血肉模糊,醒来的时候,也许只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上面粘连了一点皮。
据说,被炸伤的垦荒队员中,失去了手或腿的,已经是幸运了,在当时的海岛医疗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被夺去生命。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失去希望。每一天每一天,当太阳从海平面上升起,就是对他们最大的鼓舞。
E
尽管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叫“大陈”的岛上,有着一段热火朝天的垦荒历史。几年时间,对历史来说,甚至不及沙砾渺小,当这段经历结束,今天的老垦荒者们,能对过往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可在当年,这每一天,都将历经生与死的考验,肉体与灵魂上的磨炼,精神和信仰上的冲击。
是什么支撑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定着,扛起不能用言语描述的苦难,不退缩、不言败、不后悔?
信念。
信念是一种心理动能,也是意志行为的基础。只要你的信念还站着,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你倒下。
信念也是一种情感,是坚信垦荒事业一定能成功的坚定不移的想法,是队员们相互之间信任、信赖的思想状态。
信念引导着他们一路前行,支撑着他们每天都鼓足勇气去面对所有的苦难,每时都承受着常人难以明白的孤独、恐惧。
过去了。
62年弹指一挥。
历史到了二十一世纪。
2018年。
源源不断涌现的高科技产品、别墅、汽车……一切挥霍着和享受着的东西都需要钱。岩石块和摩天大楼之间,如何能找到最佳的沟通和对话方式?在养育我们的这一方土地上,深入骨髓的,除了流淌在椒江乃至东海里的那点精神,还应该坚守那被经济浪潮盖住意志品质。
今天的我们,如何能重新释放我们的垦荒能量?如何能用这股力量,去点燃情感、激发信念?
如果我们肩负不起这一责任,这股能量将永远沉睡不醒。
沉没于椒江之中。
沉没于东海之底。
心灵的贫困,比生活上的贫困更为可怕。
F
咆哮怒吼撕裂而来的台风,从海那头狂奔而来。
巨浪滔天。
巨石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坝向西北平移,成为一堆砾石滩。
浪通门。大自然在它身上留下了令人畏惧的难以磨灭的印记。如今,在这堆乱石滩上,每逢台风季,凶猛的风必将带着巨浪撞击此地,妄图将此夷为平地,一次,又一次。
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
起伏的山体,曲折的基岩海岸,星罗棋布的湾口网箱,远眺可见的鱼船……
1949年舟山岛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残部涌入大陈岛。1954年,解放军完成作战准备,连续轰炸上下大陈岛。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在参谋长张爱萍将军的指挥下,为解放一江山岛,与国民党展开战斗,因是解放军战史上首次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而被载入史册。
1956年,温台等地青年陆续5批467人响应团中央“建设伟大祖国的号召”,投身建设大陈岛。
历史应当被铭记。无论是自然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还是创造的力量,愿这些力量,永远被人们铭记。
愿镶嵌在那无声无息的浩瀚大海中的那颗明珠,闪烁着不灭的光芒,不仅仅是在汪洋之上,更是在人们心中。
永远。
生命的两端
东海有一个岛。公元5世纪始闻。彼时,虽偏远,却坐落于天地之间,名叫东镇山或洞正山的岛屿,却并不与世隔绝。来往朝鲜、日本的船只皆取道于此,成为伟大航线上的重要标识。《郑和航海图》中,正式将岛名记录为“大陈山”。此后500年间,大陈在战争风云中跌宕起伏。明代16世纪中叶,抗倭史使大陈山声名鹊起,嘉靖三十四年,明水军于下大陈岛风岭大败倭寇,“大陈”一词从此惊艳朝堂。
然而,今日大陈的名气,却不是因为抗倭。毕竟,全国有太多令人着迷的岛了。事实上,如果大陈没有成为人们心目中“传奇意义的岛”,也许我也不会再踏上这片土地。
记得那个初夏的午后,漫步于大陈岛。亮丽的阳光照来,一晃眼,几乎有了隔空隔世之感。原本印象中的大陈,天地之间一汪碧水,冥冥大海中一方岛屿,站在甲午岩旁,临海凭风的空旷孤寂感,在如今人群熙攘、人声喧杂、冰冷机器和大量汽车尾气中,这种世外桃源感已成为遥远的传说。如今,在这花木扶疏的季节,在这条大陈岛上十多分钟便可走完全程的唯一街上,却不乏那些时而搔首弄姿、时而故作深沉的拍照人,那些色彩艳丽的身影,便与这朴实的石头房子,一并定格为时空错乱的混搭奇观。
清乾隆年间,岛上居民渐聚,官方设治,至清末民国初期,人口已达万人规模,形成台州湾最繁荣的海上集镇,年获鱼量盛极一时,成为“经济重心”。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封锁沿海,当地武装部队首领王相义活动于大陈海域,狙击日军,并收复大陈岛,人称“海上豪客”。
然,大陈为人熟知的历史,还在于建国初期。彼时大陈,已成为浙中南国民党残部的主要踞点。当时国民党内叫得出名字的头头脑脑们,都亲临过大陈,一时间,岛上机构名目繁多。
直至1955年1月,解放军发动首次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拿下一江山岛,大陈失去外围屏障,国民党被迫实施“大陈撤退”项目,岛上除一位奄奄一息的老人外,人、财、物及庙宇神像,悉数带走。
这是大陈的历史。历史是生命的一端,它代表了過去,不能复制也无法重来。大陈的历史,锻造了它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生活气息,和审美情趣。
打开微信客户端,浏览一番游客对大陈的描述,不难发现,这座岛屿早在“蓝天白云、东海明珠、岩块嶙峋、海水清澈、美丽雄伟、如同仙境”等陈词滥调里,再配以几个经典角度的画面,盖棺定论了!于是大陈岛便成为了一张浅显的风光明信片,一张被冠以最美岛屿的旅游名片。人们在岛上的浏览,按图索骥,或去看甲午岩,或去纪念碑(军事体验区),或在浪通门、少年宫、文史馆、蒋经国故居处蜻蜓点水,也许其中会有人对撤去台湾的义胞故事感兴趣,问上一二,却鲜有人会认真思考大陈重建背后的艰辛。
垦荒。作为一个记载生死的符号,给大陈烙下了独一无二的烙印。1955年2月,我们的政府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大陈:“米面丢进海里,带不走的武器扔进海里,刚修好的水库炸掉,岛上布满地雷和铁丝网”,岛上的每一处,不仅是荒芜,更是生命尽头的陷阱。到了4月,第一批大陆移民进岛,翌年,温台青年组成“垦荒队”,支援大陈。他们用短短几十年,将昔日的童山秃岭,变为今日的林木葱郁,在上世纪60-80年代渔场鼎盛时期,一度盛况有如“海上闹市”。今天人们眼中的大陈、心中的大陈,是那个“阳光洒满石头屋、大鲜小鲜落一盘,甩甩长发放飞心情于碧海蓝天之间”的靓丽风情岛、旅游岛,可是谁能想到,大陈岛优美风光的背后,是多少垦荒人风里来雨里去,生死一线的拼搏?正是在这个充满激情的岛上,他们有信仰、有底气地在死亡边缘线上感受生命的愉悦,书写下这个岛屿最重要的那一段历史。
老垦荒队员金可人创作过一首《垦荒队员之歌》,歌词道:“像矫健的海燕飞翔在万里云天,我们垦荒队员和大陈岛血肉相连,每时每刻心中燃烧理想的火焰,一代一代我们把美好的青春贡献,把荒岛变成乐园……”
这首歌如锋刃一般雕刻出那一代人的模样。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他们也能笑着面对生命的另一端——死亡,死亡属于将来,而现时现刻,他们只顾当下。他们豪情万丈地用一双双肉手拨开遍布地雷的土地,播种下希望的种子。他们用灵魂映红天边的云彩。
大陈的景点,我愿意提一提甲午岩。两块岩礁巍然挺拔,任万千海浪扑击岿然不动。岩壁如神斧劈就,渊底白浪汹涌,涛声雷动。岩礁何时存在,已不得而知,只知道千百年下来,礁身上已呈现风化剥蚀之势,也许在未来的哪一年哪一天,在哪一次海浪的最后一击之下,轰然倒下,乱石击岸,面目全非,不复存在。但无论怎样,哪怕我们已经知道物质永无止境地运动,甲午岩也终会变成碎块、碎屑,它依然会是大陈恒久的支柱,会是大陈岛上最特别的一景。
从甲午岩到大陈垦荒,可以说,在旖旎风光的矫情里混杂着灵魂深处的坚守,才是大陈岛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