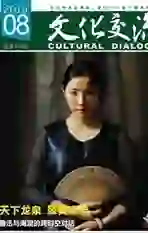《艺术的故事》与背后的故事
2019-08-23陈淡宁
陈淡宁
1984年,为了翻译贡布里希的著作《艺术的故事》,范景中开始与贡布里希通信。两人因此结下了长达15年的真挚友谊,直到2001年贡布里希离世。2007年依照贡布里希的遗愿,其藏书四千余册悉数捐赠给了范景中所任教的中国美术学院。
7月12日,五年一届的浙江省美术作品展览在浙江美术馆开展。在这场以“大潮涌进”为主题的展览中,观众们在600多件美术作品的簇拥下,感受着时代的滚滚浪潮。
而今天笔者要说的,是此次省美展的金奖作品,由画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封治国创作的油画作品《艺术的故事》。
那是一间西洋风格鲜明的书房,红色的编织地毯,浅黄的花纹壁纸。巴洛克风格的书架前,有两个人物,一站一坐。站着的是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学者,有着一张东方面孔。而在他身边的那位高鼻深目的老年学者,泰然地坐在椅子上,膝盖上摊着一本厚重的大书。
画面的玄机,就在青年学者手中的那本书上,黑色的封皮上,白色的字体清晰可见:《艺术的故事》。
画中这位老年学者,是已故的西方艺术史学界泰斗恩斯特·贡布里希((Sir E.H.Gombrich,1909~2001)教授,而那位有着东方面孔的青年学者,正是青年时代的范景中。
1984年,为了翻译贡布里希的著作《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范景中开始与贡布里希通信。两人因此结下了长达15年的真挚友谊,直到2001年贡布里希离世。2007年依照贡布里希的遗愿,其藏书四千余册悉数捐赠给了范景中所任教的中国美术学院。
一
范景中,1951年生于天津。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于1979年入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攻读艺术理论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
他先后担任《美术译丛》和《新美术》主编、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出版社总编等职。著有《法国象征主义画家摩罗》《古希腊雕刻》《图像与观念》《藏书铭印记》《中华竹韵》等,译有《艺术的故事》《艺术与错觉》《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普尔论文集》《艺术与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论文集》《希腊艺术手册》《图像与眼睛》《走向进化的知识论》等,编有《美术史的形狀》、《美术史与观念史》等。
身为学者的范景中极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你很难从媒体报端觅得有关他的只言片语。然而2018年,他却在知名的听书音频网站上开讲《西方艺术史》。如今,这门课更新到了第95集,收听量达到了307万。
在这门课的开篇中,范景中说,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想跟更多的人分享艺术的愉悦,因此开始翻译介绍贡布里希所写的《艺术的故事》。
时光倒回至1979年,为了逃离充满诱惑的北京,带着对江南的向往,范景中来到了杭州。
然而彼时,作为浙江美院美术理论专业的研究生,范景中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当时中国的美术研究,似乎停留在一个枯燥的套路之中:一般是在某个朝代,有什么著名的画家,他有什么著名的作品,编年排一排作品,画家的生卒,再深入一点就是作品的真伪如何鉴定,然后就结束了。
那一年,25岁的范景中想的是,在这个世界的别的地方,美术史是怎么做的呢?
二
恩斯特·贡布里希1909年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其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维也纳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优渥的家庭条件与良好的教育环境,奠定了贡布里希深厚的人文素养。二战的爆发,让贡布里希不得不背井离乡,移居英国。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集历史学、心理学、哲学、文学与音乐学等多种学科于一身的大师。
而对于中国文化,贡布里希所涉猎的也绝非泛泛。他曾与他母亲的中国学生李惟宁交谊甚笃,而李惟宁在上世纪30年代曾担任过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在维也纳留学期间,李惟宁向贡布里希输出了不少传统中国文化,这其中包括唐诗和中国小说。
在贡布里希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期间,学校有个传统,每到期末升高年级时,就要举行一场戏剧表演。贡布里希连着写了两年的剧本,而这些剧本正是改编自中国的小说。当时一位非常有名的美术史家在看了表演后,建议贡布里希放下美术史研究直接去写作,不然有浪费写作才能之虞。到后来,贡布里希的第一篇论文写的是《一首中国的古诗翻译成德文有几种可能性》。
25岁那一年,贡布里希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并因此大获成功。而这本书的成功,让贡布里希从中获得了一种启发:那就是要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用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要让人人都能看得懂,要有趣味性。
这种特质,在贡布里希于二战后撰写的《艺术的故事》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三
就在范景中对美术史研究的现状感到无比困惑之际,他忽然想起了中学时迷恋作词时的往事。对词的研究,应该从哪里入手?从工具书入手。工具书是什么呢?就是目录,你必须了解前人都写过什么,了解研究的发展过程。
于是范景中开始寻找西方美术史领域中最基本、最前卫、最经典的著作。渐渐地他注意到,在一些著名的大师的论著后面,都会附有参考书目,而这些参考书目中,恩斯特·贡布里希的名字出现频率非常高。
这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范景中想。而在读完《艺术的故事》后,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
但范景中并不满足于独自喜悦,他觉得有必要让大家都来见识一下这个崭新的学术世界。于是他开始着手翻译。而在翻译完成后,范景中又花了五年的时间,为这本书写注释。2008年范景中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他当时这么做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为年轻学者在阅读时提供一个更深的门径,另一方面是通过注释扩大阅读者的视野和阅读范围。
《艺术的故事》中文版出版于1986年,但事实上,在此之前,范景中在很多的讲课与讲座中都会提到其中的概念与观点。《艺术的故事》从头至尾就是讲艺术怎样创新,艺术的风格怎样变化,一个新的风格怎样取代旧的风格。而艺术创新对于当时的中国美术现状而言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些思考与探讨最终形成了现象级的“85美术新潮”。而趁着这股热潮崛起的艺术家们,有许多都是受到了范景中与《艺术的故事》的影响。
然而范景中却永远保持着谦恭的态度,二十多年后再忆当时种种,他却说“如果说我跟‘85新潮有些什么关系的话,就是‘85新潮那些非常出名的干将与其感谢我不如感谢这本书。”
四
尽管贡布里希与范景中从1984年就开始通信,两人也早不止一次表达过相会的意愿。但真正的第一次会面却已是在两人相知十年后。
在这十年间,两人多次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擦肩而过。而范景中更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而在他卧病在床期间,贡布里希不仅在经济上给予了范景中支持。或许是担心两人无缘相见,贡布里希还特意为范景中拍摄了一些他和他家庭的照片。
时间终于来到了1994年,在那一年,85岁高龄的贡布里希获得了“歌德奖”。这是一个每四年颁发一次的奖项,获奖者中有著名的作家和科学家,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与其他学术研究不同,美术史研究领域并没有诺贝尔奖或者类似诺贝尔奖之类的奖项。因此美术史家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可能就是“歌德奖”了。1994年歌德奖的获奖者贡布里希,请颁发城市法兰克福市市长邀请范景中以嘉宾的身份去参加他的颁奖仪式。
范景中清楚地记得,他被安排在会场内第一排右边靠中间走道的第一个座位上。整个会场里,只有范景中一個中国人。当贡布里希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向他,而贡布里希却用目光在人群中寻找,当他看见范景中时,他笑了,举起手打了一个招呼,才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颁奖仪式按照流程顺利地进行着,到了最后贡布里希讲话的环节,他上台坐定后,又朝着范景中招了招手,这让周围观礼的观众把目光也移向了范景中。
颁奖后,贡布里希开始了他的致谢。他说,我受邀下榻在你们的宾馆,躺在床上,发现天花板是一个放大镜,把我的头放得非常大,其实我没有这么大;古希腊的修辞老师训练学生,常常让他们赞美不值得赞美的东西,例如要把一个微小的东西写得很大,比如赞美一只蚊子,把它说得如何如何了不起。我现在到这里来领奖,就是这种感觉。我本来没有这么大,却被放得这么大;我本来是一只小蚊子,却要被歌颂一番。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感谢你们给我颁发这笔奖金。贡布里希略微停顿一下,接着说,我也非常感谢在座的一位中国朋友——范景中教授,他把我的书译介到中国,使我的书拥有了中国的读者。
五
2001年贡布里希辞世,范景中万分悲痛。在他撰写的悼词中,范景中这样写道:
“有时,连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也会受制于类似的有害的神话,这一事实促使他特别警觉德国哲学传统中流行的一种陈词滥调,即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为了驱逐这种阴霾,他投人了极大的精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想用真正的历史方法来取代这种轻易而廉价的循环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常常强调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的各种研究都会产生可能影响许多人生活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努力预见并防止我们的研究结果所造成的任何可能的危险。这是一种呼声,是一个正义的学者向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呼声。”
这就是《艺术的故事》背后的故事。
一如油画的作者封治国所说:他想通过这件作品表达一种心愿和敬意。这幅画实际上是在向一代知识分子致敬。它不仅是艺术的故事,是一代学者的故事,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故事。
Story about Translation of The Story of Art
By Chen Danning
Professor Fan Jingzhong is so influential in the art circles of China that one painting that depicts him and Gombrich is now on display of Zhejiang Art Exhibition, an event that takes place every five years.
His nationwide reputation is due largely to hi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tory of Art by E. H. Gombrich.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came out in 1986, eight years after Fan came to Hangzhou and studied as a graduate of art theory at Zheji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the predecessor of present-day China Academy of Art.
Fan was 25 years old in 1979 when he arrived in Hangzhou. At that age, he was experiencing some confusion and uncertainty about his future and discontent about the way Chinese art history studies were conducted. One of the questions he pondered was how scholar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conducted their studies of art history.
While combing western literature on this subject, he became aware that the name of E. H. Gombrich popped up again and again in footnotes and indexes and bibliographies of books. He realized that Gombrich must be one of the best art historians.
After reading The Story of Art, Fan was convinced that the book gave him a direction and he thought it urgent to translate the book into Chinese so that Chinese artists could benefit from Gombrichs perspectives and concepts.
He soon decided to translate the book into Chinese. After he translated the book, he spent another five years writing Chinese footnotes for Chinese readers, in the hope that these footnotes would enable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book better and broaden broader perspectives.
Long before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book came out in 1986, Fan trumpeted some concepts and ideas from the book at various lectures and in his own classroom.
His promotion of the ideas from the book contributed to a phenomenal art movement known in Chinese art history as “1985 New Art Wave”. In the following years, many influential figures in this movement mentioned Fans name on many occasions. However, Fan is modest about the role he played in the art phenomenon. He says that these heavyweights that emerged from the “1985 New Art Wave” into national spotlight should be more grateful to the book.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Fan Jingzhong wrote to Gombrich in 1984 and that it started a correspondence and friendship that lasted fifteen years until Gombrich passed away in 2001. Gombrich donated over 4,000 books from his private library to China Academy of Art where Fan teaches.
It was not until 1994 that Fan and Gombrich met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not that they didnt wish to meet. Fan was sick and bedridden for a long while. Fan struggled to recover for a serious illness. Gombrich sent him money to help him get back on his feet and sent him photos of himself and his family.
In 1994, the 85-year-old Gombrich won Goethe Award, a prestigious honor given out every four years. Fan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award ceremony in Frankfurt, Germany. Through special seating arrangement, Fan sat in the first row. Before making his thank-you speech, Gombrich waved to Fan, drawing all attention to the only Chinese present at the award ceremony. He made a special mentioning of Fan Jingzhong and expressed his appreciation of Fan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his The Story of Art. He said it was Fan that introduced his book to Chinese readers.
The painting highlighting Fan Jingzhong and Ernest Gombrich is an artwork by Feng Zhiguo. The artist points out that his work salutes great intellectuals of the past generation. The painting is not just about a story of art. It is also a story about a whole generation of scholars and intellectu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