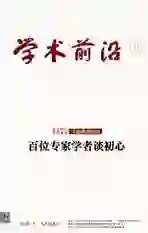马克思政治自由的生成方向
2019-08-22李毅
李毅
【摘要】马克思伟大之处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他将获得政治解放视为其政治自由实现的必要指标,但却不是终极指向。从马克思政治理想的结构的角度出发,以人、共同体以及两者间,两个层次上的关系建构为主线,可以更好地把握马克思的政治理想。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政治理想的主旨:如何克服人与公民之间的分离;而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则是马克思政治理想的基础:克服共同体和政治国家的分离。
【关键词】政治解放 人类解放 市民社会 政治国家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2.011
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
政治解放。在马克思的视阈中,政治解放就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那个旧社会的解体,也就是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确立。其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革命的政治精神的实现。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政治精神在于没有政治地位的阶级渴望着消除自己被排斥于国家和统治之外的这种孤立状态”。[1]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对于力争实现政治自由的人来说,实现政治解放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它使得专制统治手中的那柄剑,从人的社会生活中撤去;使人从政治专权下的被奴役物变成感性的个体。在专制统治下,人只是政治权力博古架上的摆设,人的身份只有一个,即被统治者身份的僵化是自由丧失的表现。人无法作为感性个体代表自己,这是被封建体制囚禁的结果。政治解放就是要将人从已经被异化为不可质疑的、代表必然性的政治统治下解救出来。
对于政治统治这件人类历史的产物而言,政治解放使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根植于世俗而非神权;对于个人而言,政治解放承认了人的个体存在。其一,政治解放的任务就是揭开封建国家统治的“神权”的面纱,将政治统治的合法权交付给世俗;其二,政治解放使得人作为个体,而非仅仅是政治统治下的“顺民”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在政治解放完成前,市民社会没有自主的活动行为。市民的生活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统治目的,被纳入国家的统一意志中。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活是不具有现实性的,无法通过感性的活动显示自己的对象性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解放铲除了专制,摧毁了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的关系,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平等,从而承认个体感性的存在。但是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并不彻底,政治解放在完成了政治统治的世俗化和人的市民化的转变之后,依然有无法解开的困局。首先,对于人而言,政治解放造成了“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人与人之间无法建立真正的联系。政治解放把人从专制的政治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将人划分为两类: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公民和法人。人的存在的二重分裂,使得人在市民状态下,是作为利己的人而存在。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都是作为工具而物化地存在的。人与人之间以“物”作为建立联系的中介,彼此是分离的和排斥的。一个个的人,不过是需要借助“物化”这个一般等价形式转换的存在物,无法真正建立联系。马克思认为,人不只是个体感性的存在,而且还是类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所产生的后果——人与人的分裂和对抗,是无法通过政治解放的旅程而化解的。
其次,对共同体而言,政治解放无法改变虚假共同体的性质,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生活。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中说:“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2]因此,这就会造成,当人还在被私有财产的桎梏束缚时,政治国家已经在形式上以及在一定的事物管理上成为“自由”的国家。国家和国家中的人,走在两条不同方向的道路上。同时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是统治阶级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这就是虚假共同体的表现。马克思批判劳动者的被奴役的地位,反对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处于对立中的共同体。在他看来,只要政治国家是作为有产者实现自由的政治国家存在时,真实的共同体就无法实现。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政治解放,是无法跳出自身的局限性,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
人类解放。马克思的政治自由是与他对人的理想相统一的。人与共同体之间政治生活的实现,是从属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大目标下的。因此,要真正实现政治自由,就需要在“人的解放”的道路上再走远一些。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解放,就是将人类从一切对立关系中解放出来。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面临反封建的大背景下,马克思提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这个命题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就是争取实现社会平等的政治解放,矛头直指将自己標榜为类自然规律般的封建等级制度。第二个层次就是实现人的解放,即为马克思提出的“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是处在人自己的把握中,而不是由任何一种异化的力量来决定的。人的存在,归根结底是类的存在,社会的存在。所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类解放,就是要扫除确立人的本质过程中的障碍,“就是要消灭这些对立,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3]
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人类解放的两个具体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人的身份的统一。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类解放实现时的人是怎样的人——不仅仅是现实的人,同时是抽象的公民,并且是类存在,也就是“现实的人”“抽象的公民”和“类存在物”的合一。这一身份的统一,是层次上递进的合一。所以,人归根结底是要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但在成为“类存在物”之前,人又需要为自己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而创造条件——成为“现实的人”和“抽象的公民”的集合。但对于马克思来说,仅仅是成为“现实的人”“抽象的公民”并不足以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加之政治解放至多只是将人从专制制度下那“使人不成其为人”[4]的情况中解救出来,成为追求私利的“抽象的人”和“抽象的公民”。故此,“人的解放”才是马克思的真正的目标。因为只有真正的类存在物,才能在实践的层次上将政治演绎为一种生活。
第二个目标是人的存在的社会化,即“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5]所谓“自己的‘原有力量”指的就是人的社会性。只有承认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并且以此为本来创建人的生活方式和实现人与世界的互建,才可算是真正把握了人类世界的精髓,也是把握了现实性的来源。因此,将人的社会性作为人之为人的“原有力量”来理解,是对政治自由中的人的根本定位。只有当人是“类存在物”,同时不再将自己的“原有力量”作为脱离了人的人的本质力量使用时,政治自由才真正得到了实现。因此,将人类的解放作为主旨,将政治的解放作为这一主旨中的应有之义,是实现政治自由理应持有的逻辑。
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
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产生于近代的市民社会,是褪去了绝对权威的政治统治辖区外的一片新鲜领域。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宗教对待世俗一样”,它的出现前所未有地呈现出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而这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作用之一就是帮助马克思奠定了思考问题的现实基础。它解决了究竟是该立足于政治国家还是市民社会来思考政治自由的实现。对此,马克思认为应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来思考政治自由的实现。因此,在构建政治理想所需要的背景的选取上,从逻辑顺序这个角度来说,市民社会先于政治国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构建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将市民社会在逻辑上放在政治国家之前的意义。这打破了长久以来,在政治框架内解决政治自由问题的僵化思路。
在政治框架内解决政治自由问题,好比是用病人的基因来对付病态的基因,不可能根治任何问题。在现存的政治国家的范畴内,寻找政治自由被囚禁的原因,只是“被关押者”向更高级别的“关押者”寻求解救的行为,必定要成为一种徒劳。即便智慧如黑格尔,也囿于采取“和解”的方式来弥合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分裂。类似于黑格尔的方式,实则是在保留现存政治状态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现存的政治国家的范畴内,缓和政治领域内的冲突。所以我们要看到,终极意义上的政治问题,是无法在单纯的政治范围内寻得出路的。
在马克思所处的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国家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实现的。现实的政治生活并不是将市民社会视为基础,而是将抽象的国家存在作为基础。与黑格尔所执着的政治国家高于家庭和市民社会不同,马克思的政治国家是“低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国家不是第一产物,而是第二产物,政治国家离开了市民社会将只是一个虚幻的躯壳。因为政治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政治独立不是从政治国家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它不是政治国家赠给其他成员的礼物,不是振兴国家的精神;政治国家的成员不是从政治国家的本质中,而是从抽象的私人权利的本质中,从抽象的私有财产中获得自己的独立的”。[6]市民社会中个体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无比剧烈的尖锐冲突,和调控利益冲突的需要为政治国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因此,市民社会“无法自足”这一致命的缺陷,将随着市民社会的存在而存在,政治国家也会随之而存在。所以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比,构建政治理想的基础应放在市民社会,而非政治国家上。这同时也说明了政治理想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为基础,而不应停留在当时现存的政治范畴内构建政治理想。
市民社会和人的社会。马克思政治理想的实现,不是仅限于针对市民社会中的人的政治自由,而是指向人类社会中的人的政治自由。尽管市民社会是其政治理想实现的现实基础,但却并非是建立政治理想的地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物质生活这种自私生活的一切前提正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7]市民社会是私人的战场。若将这一以“私”字为核心的领域作为政治思想的建造基地,只会相当于是在流沙上建筑房屋。
将人类社会视作政治自由实现的基础——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的观念与西方政治学中传统之一的“主权在民”思想有着相同之处。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市民社会是个体利益的集散地,缺乏统一的利益,因而并不符合一个协调而统一的人类社会的要求。在个体利益的不断冲撞下,要形成一个良性运作的政治共同体是很难的。人只能作为“私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无法满足市民社会这一领域发展的整体需要。这一无法更改的、溶于市民社会“血液”的“先天不足”,就将市民社会排斥在政治理想的“地基”之外了。
马克思要实现的,是在政治生活的开展中促进,并最终完成拥有全面社会关系的人。这个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而非某一放大了的“人的功能”的存在物。所以,政治自由的实现需要全面的、而非片面的社会关系。当马克思呼吁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时,就已经说明人的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是不可能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完成的。要想实现政治理想就需要以人的社会为基础。马克思在谈到政治国家时,曾经说过,“它正像黑格尔自己所想象的那樣是政治国家的‘抽象。这种观点也是原子式的,但这是社会本身的原子论。如果观点的对象是抽象的,‘观点就不可能是具体的”。[8]于是,“人们的结合、个人赖以存在的共同体——市民社会——是同国家分离的,或者说,政治国家是脱离市民社会的一个抽象”。[9]抽象的领地上无法真正实现现实的人的诉求,为了生成现实的政治自由,马克思提出将政治自由实现的基础放在市民社会而非政治国家上。虽然,市民社会弥补了政治国家的抽象性,但“私性”充斥的市民社会,是“私人”的社会,而不是“人”的社会。旨在实现人类解放的政治自由,是无法再以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为存在基础的市民社会中实现的。于是,马克思又提出要越过市民社会的狭隘,在人的社会所提供的宽广领域内,实现政治思想。
注释
[1][4][5][6][7][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88、411、443、378、428、343、34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
[3]江德兴:《马克思社会化理论与政治权力的演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页。
责 编/赵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