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本《困學紀聞》審讀報告
2019-0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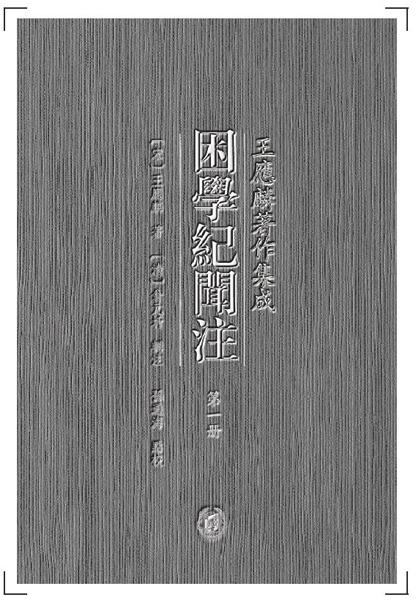
评审专家点评
在刀锋之上的编辑工作
在2019年审读报告研讨会上,中华书局《困学纪闻注》一书的责任编辑李爽引用新儒学代表人物唐君毅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从事编辑工作的感受,即“许多道理都要如从刀锋上说过去一般,乃能入微”。这就说,一个认真负责的编辑,其工作状态就应当像行走于刀锋之上,处处小心,细致入微,稍有不慎,便可能伤及书稿,累及职业。
用“刀锋之上”来形容编辑工作,较之我们用惯了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等说法,似乎更新颖,更有警醒作用。
做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人士知道,《困学纪闻》是宋代学人王应麟的代表作,堪称是宋代学术笔记的卓越之作;清代学人翁元圻为此书作注,条分缕析,博征广引,成了《困学纪闻注》。2007年,中华书局老编审孙通海先生应中华书局之约,开始整理校点《困学纪闻注》,经过四年多的工作,200多万字的书稿于2011年9月交付书局,正式进入审读编辑流程。
孙通海何许人也!中华书局古籍整理著名老专家,独立点校过《陈献章集》《东周列国志》《南北朝文举要》等,参与点校过《张耒集》,可谓古籍整理、点校、研究著作等身。孙先生曾经分别为《儒藏》和“新世纪万有文库”整理出版过《困学纪闻》,在这二种整理本之上再度整理校点《困学纪闻注》,可想而知,必定是一部更为成熟的书稿。形成很大反差的是,承担这部书稿责任编辑的李爽只是一位当时入职不满两年的新编辑,将独立承担这部书稿的编辑工作。新编辑审读老编审的书稿,将在老编审的书稿中说三道四,岂能没有行走于刀锋之上的感觉!然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年轻编辑敬重老编审,但更要做好老编审的书稿编辑。这位年轻编辑在《困学纪闻注》一书的编辑过程中知难而进。《困学纪闻》原文阅读难度本来就很大,加上清人翁元圻注文层级繁复,年轻编辑通读起来需要十分耐心、细心,不明之处只有仔细勤查文献,不敢草草看过。在审读、校对、统理各阶段,审慎处理,严格把关,开列出需要与整理者、复审、终审交换意见的问题达十余页记录。为此,她“刀锋之上”的工作得到了各方面一致的认可。老编审尤其赞赏。孙通海先生在此书的“点校说明”中如此写道:“定稿阶段,责编李爽女士以中华书局传统的学识、传统的责任心和传统的作嫁衣精神处理此稿,使之能够顺利出版。”多么好的“三传统”!专业扎实的老编审的夸赞使得终审编辑受到很大鼓舞,批示“希望在校样阶段更加仔细,把此书做成一个善本”。我想,这实在称得上是出版社对这位在古籍整理出版的刀锋上走过的年轻编辑的最高褒奖了。
初審意見
初审姓名:李爽
职务/职称:副编审
日期:2012年3月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以劄記文累積結撰,是我國古代學術史上的名著,此次予以點校整理,列入“王應麟著作集成”。《困學紀聞》目前點校本有三:新世紀萬有文庫本,1998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儒藏精華編本,200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上述兩種均爲本書整理者孫通海先生點校,以元刊本爲底本,僅有原文而無注文。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全校本《困學紀聞》(以下簡稱上古本),將本稿與之對比,有三點超越之處,一是本稿爲全式標點,便於閲讀;二是本稿標有序號並附有編目,有利檢索;三是建議本稿附録版本序跋、書目著録,以增强資料完備性(上古本僅附録少量王應麟傳記資料)。
一、校勘
本稿以清道光五年餘姚翁氏守福堂刻《困學紀聞注》爲底本,與上古本同;以《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傅增湘藏元刊本《困學紀聞》爲第一校本,以清嘉慶二十四年萬希槐《困學紀聞集證合注》爲第二校本,上古本則用《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元刊本和清嘉慶十二年友益齋《校訂困學紀聞三箋》爲校本。本稿工作本是商務印書館1959年本。
本稿彌補了上古本一些未能校改的錯誤,如卷一第三條“未有夬而不姤”,誤作“未有姤而不夬”,與其義正相反;第十一條“哀公元年”,誤作“哀公二年”;第四十三條“司馬良娣”,誤作“史良娣”。
以下就審讀過程中的幾點問題提出商榷意見,以供斟酌。
1.目録中卷題文字據正文校改,但未出校記(上古本出校,部分條目據正文校補)。
2.改底本而未出校,以前兩卷爲例(末標“※”者點校者鉛筆自注“徑改”):
卷一(13處)
第12頁第九條“王充 論衡 按書篇”,“按”徑改爲“案”(上古本未改)。
第13頁第十一條“皇甫謐 帝王世紀:帝羿 有窮氏……封於鋤……自鋤遷於窮石”,“鋤”徑改爲“鉏”(上古本亦改)。
第15頁第十九條“宋 藍田 呂氏曰:……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頻復”,“致”徑改爲“至”(上古本原文以圓括號、六角括號標改並出校記“據《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一改”)。※
第16頁第二二條“豫上六程傳:……苟能有渝,則無可咎”,“無可”徑改爲“可無”(上古本未改)。※
第27頁第五五條“(魏鶴山奏疏)又曰:……首相章厚”,“厚”徑改爲“淳”(上古本標改作“〔子〕厚”)。※
第31頁第六三條“後漢書 申屠蟠傳:……蟠獨歎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滂等果罹黨禍”,“王”徑改爲“主”,“阬”徑改爲“坑”,“禍”徑改爲“錮”(上古本前兩字未改,後一字亦改。嘉慶本作“錮”)。
……
3.某些漏誤脱衍似可以用圓括號、六角括號在原文標改,不必出校勘記。如:
第43頁卷一第九三條“宋 沈作詰 寓簡”,校勘記①:“喆,原誤作‘詰,據文義改。”(上古本標改。)
4.個别校勘核實底本有誤。如第126頁卷二第一二一條校勘記①:“三,原誤作‘二,據漢書改。”按:底本即作“三”。
5.個别校勘有待商榷。如:
第147頁卷二第一八一條校勘記②:“‘篇上爲墨釘,文字不完整,據文義補‘同字。”按:查核底本,依“篇”字上的墨釘長度,應是缺兩個字,而本稿却只補了一個字。上古本校勘記:“原本作‘□□篇,‘篇上二字刮去,因下引文亦屬《天瑞篇》,而‘篇誤留。”
第179頁卷三第四七條,正文篇末處,清嘉慶本有“全云:深寧此説有感於燕雲之爲禍烈也”。上古本據《校訂困學紀聞三箋》補入此條,本稿未補。按翁注《凡例》:“卷中於閻氏、全氏語皆全録”,由此,翁注於全祖望注間或有重要遺漏。
6.清閻若璩據元泰定二年慶元路儒學刻本對《困學紀聞》進行校勘,翁注原文采用閻箋本作底本,保留了閻氏的校語(“元板作××”)。本稿遇此類文字亦出校,與閻氏校語似重複,如第67頁校記①、第122頁校記①、第141頁校記①。上古本的處理原則是:“若原本注文中已有‘元板作××之類校語者,我們則不再出校記。”(《校點説明》)
7.前後體例不統一
(1)是否注校本的版本不統一(一般均不注版本)
第234頁卷四第六條校勘記①:“據點校本孫希旦 禮記集解校説改。”其他條目出校涉及《禮記集解》則未注版本。
第257頁卷四第四六條校勘記②:“據十三經注疏本周禮注疏改。”其他條目出校涉及《周禮注疏》則未注版本,如第90頁卷二第二七條校勘記①:“據周禮注疏補。”第239頁卷四第一四條校勘記①、第258頁卷四第四八條校勘記①、第259頁卷四第四九條校勘記③:“據周禮注疏改。”
第285頁卷五第三條校勘記③、第391頁卷六第六五條校勘記①、第502頁卷八第七○條校勘記②:“據中華書局校點本漢書改”;第574頁卷十第二五條校勘記①:“校點本漢書 應劭注”,其他條目出校涉及《漢書》則未注版本。
(2)對同一校本的稱謂不統一
第379頁卷六第四三條校勘記①:“據困學紀聞集證合注改”;第382頁卷六第四九條校勘記①、第492頁卷八第三○條校勘記①、第608頁卷十第一二五條校勘記①:“據困學紀聞集證合注補”;第384頁卷六第五二條校勘記①:“困學紀聞集證合注冠以‘何云”。按《點校説明》:“選用質量較高的清嘉慶二十四年萬希槐《困學紀聞集證合注》作爲第二校本,簡稱清嘉慶本。”其他校勘記中均稱“清嘉慶本”。
二、編目
點校者處理方法:“本書每條前的編目均保留,改小字排在天頭位置。”“此編目複製一份,按卷彙集排列,並填入序號、頁碼,爲本書附録之編目。”點校者建議按《四部備要》樣式排版。按:附録彙集排列的具體版式尚有待斟酌。
1.《點校説明》:“我們針對過於晦澀的(編目條文),作了一定的加工。某些失誤,徑直改正。”按:如第十七卷第896頁第九條、第899頁第一八條、第901頁第二一條、第903頁第二五條,點校者依據原文、注文改動原編目的文字。此種情況是否需要出校,待斟酌。另有漏改者如第896頁卷十七第八條“古文苑得於經龕”當移上條;誤改者如第906頁卷十七第三三條,原編目“蕃歆寄宿知子年”,“蕃歆”似當指“陳蕃”、“華歆”兩人,點校者將“蕃”改爲“華”。
2.《點校説明》:“對(編目)條文加了標點,使用了專名號、書名號、頓號和逗號。不使用引號是爲版式整齊。”按:編目條文,類似某段原文、注文的小標題或者關鍵詞,且排於天頭,似以不加標點爲佳。
3.據《編目例言》:“翁注中,原爲疏證本文者,不更列目。其有旁及本類各類諸事者,亦並列目。本類則別以‘本注二字,各類則分載於續編編目六卷中。”按:翁注旁及本類的編目條文,入原分類目録(前二十卷),並標“本注”;而旁及各類的編目條文則入後六卷續編編目目録,這些編目條文《四部備要》本和商務印書館1959年本均不入正文天頭,故《備要》本、商務本以及以商務本爲工作本的本稿,正文編目内容皆不全。建議點校者最好將後六卷編目條文插入正文天頭,以利讀者閲讀檢索。但前二十卷和後六卷編目條文在書末附録中是否彙集,待斟酌,若彙集,則打破了原有的分類;若依原樣不彙集,則同一序號的諸條編目文字則是分離的。
4.《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原書或《四部備要》排印本可能存在的問題:一是編目條文順序與原文、注文順序不合,如下舉(1)、(2)、(3)、(6)、(7)、(11)、(13)、(14);二是有些編目條文據《編目例言》應在目録中標“本注”而未標,如下舉(5)、(6)、(12);三是天頭與目録的編目條文文字不統一,如下舉(8);四是編目條文各條目之間的分合,本稿有與《備要》本不同者,其中涉及較長的條目在雙欄排的目録中是否需要斷句的問題,如下舉(4)、(9)、(10)。建議點校者最好核實清光緒八年《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原刻本。如原刻本和《備要》本確實存在問題,請斟酌是否作修訂。兹以卷十七爲例條舉上述問題:
(1)第901頁第二一條,末條“崔元翰詔令温雅”排列位置似不妥。
(2)第905頁第三○條,編目“二生兩公負所遇”“德裕集鄭李兩序”排列位置似顛倒。
(3)第907頁第三六條,編目“文選爛秀才半”似應前置。
……
三、版本序跋
(一)關於“胡敬序”
書稿“困學紀聞注序”首載清道光六年秋七月“胡敬序”,頁下注:“此序原不載,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困學紀聞》補入。”(第4頁)按:本稿底本即清道光五年翁氏守福堂刻本,筆者所見三本,其中《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本和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本(編號47171-47184)均載“胡敬序”,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本(編號157233-157240)不載,相應書頁爲空白頁。此或是初印本與後印本之别。要之,此序不應據商務本補入,可徑行刊載,不必出注。
(二)附録其他版本序跋、書目著録
除翁注本序跋外,盡可能收集其他版本序跋以及歷代書目著録(參看蘇曉君《約園善本〈困學紀聞〉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年第2期),作爲附録,以便讀者利用。
兹據寓目的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本,並參考展龍、吴漫《〈困學紀聞〉版本流傳考述》(《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6年第1期),張驍飛《〈困學紀聞〉版本源流考述》(《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2期),依時代順序舉隅如下:
(1)元泰定二年陸晉之序,明刻本《困學紀聞》書後載,國家圖書館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亦載。
(2)明吴獻台序,清汪垕桐華書塾刻本《困學紀聞》書前載,國家圖書館藏。又,國圖藏明萬曆三十一年吴獻台刻本,未見,不知刊載與否。
(3)清馬曰璐識,清乾隆三年馬氏叢書樓刻本《困學紀聞》(閻箋本)書後載,國家圖書館藏。
(4)清何焯跋,明刻《困學紀聞》清蔣杲校跋並録清閻若璩校注、清何焯校跋本,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聚秀堂刻《困學紀聞集證》亦載,國家圖書館藏。
(5)清汪垕記,清汪垕桐華書塾刻本《困學紀聞》(二箋本)書前載,國家圖書館藏。
(6)清乾隆五十九年萬南泉序、嘉慶六年陳詩序,清嘉慶八年聚秀堂刻萬希槐《困學紀聞集證》(七箋本)書前載,國家圖書館藏。
(7)清嘉慶十二年陳嵩慶序、嘉慶六年陳詩序、乾隆五十九年萬南泉序,清嘉慶十六年刻萬希槐《困學紀聞集證合注》載,中華書局圖書館藏,編號31061-31068。
(8)清陳運鎮敘、嘉慶十八年仲振序,清嘉慶二十四年胡氏山壽齋刻萬希槐《困學紀聞集證合注》(即本稿第二校本)載,中華書局圖書館藏,編號88118-88133。
復審意見
复审姓名:李静
职务/ 职称:编审
日期:2012 年4 月1 日
孫先生是中華老編輯,古籍整理的路數頗熟,且曾做過兩版《困學紀聞》的整理工作,此次整理,吸取了前兩次整理的經驗,相信會是個後出轉精的好本子。
孫先生在《點校説明》中對版本、校勘、格式、編目的處理作了通盤説明,條分縷析,足以説明工作重點。
責編審稿仔細認真,查核了大量資料,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商榷意見。
一、關於校勘
1.卷題文字可據文徑改。
2.改底本處可逐一與孫先生商榷。
3.方圓括號統一没有使用,可以適當以校記形式出現。
4、5、6、7與孫先生商榷。
二、關於編目
1.編目的目的是爲便於使用,可以徑改,有疑議可與孫先生商榷。
2.編目具有關鍵字的提示作用,標點加與不加兩可。如以提要形式排在前面,可以考慮加。
3.編目後六卷與前二十卷的關係是主幹與分枝,將後六卷插於前二十卷相當於重新編目,但眉目應該更加清晰,可以請孫先生做這個工作。
4.所列諸項實際是編目錯要不要改正的問題。編目非原文,此次作爲附録附於後,具有索引的功能,因此可與孫先生商量完善之。如果後六卷插入前二十卷,並順改原錯,則順理成章。
三、版本序跋
可以增補進來。
終審意見
终审姓名:徐俊
职务/ 职称:总经理
日期:2012 年4 月5 日
以上意見當否,請三審定度。
(1)同意初、二審意見,請與孫先生商處。
(2)請排一兩卷校樣,調整確定版式,再排全稿。
可將初、二審意見一併在編輯室内傳閲。
點校本《困學紀聞》審稿報告
初审姓名:李爽
职务/ 职称:副编审
日期:2013 年3 月18 日
本書是我到歷史編輯室工作後處理的第一部篇幅較大的書稿。目前已經通讀全稿(之前檢讀書稿的《初審意見》亦附後),所做主要工作是:
(1)凡是工作本上改動之處,均核實底本,將點校者徑改底本不當處標出,建議出校,新增校勘記約計173條。
(2)改正常見錯誤:書名綫、專名綫漏標、誤標;個别標點漏誤,尤其各層級引號漏標、誤標情況較多。
(3)原附《困學紀聞翁注編目》不便閲讀,請點校者重擬編目。個别重擬小標題有概括籠統、遺漏信息、措辭不確等問題,但總體上優於舊目。
(4)編輯提供綫索,請點校者輯録了其他版本序跋作爲附録,對閲讀本書有較爲重要的資料價值。
茲列存在的主要問題,提請復審、終審裁示:
一、底本
本稿底本是清道光五年餘姚翁氏守福堂刻本,工作本是商務印書館1959年本。工作本之誤,點校者核實底本有漏改。如:卷一第九條“疆”誤作“彊”(第12頁);卷二第一一九條“苦”誤作“若”(第126頁);卷二第一五一條“淳”誤作“涥”(第137頁);卷十九第一一條“之”誤作“以”(第992頁);卷十九第十六條“都督”誤作“刺史”(第995頁);卷十九第十七條“理”誤作“里”(第995頁);卷十九第二八條“章”誤作“璋”(第1004頁);卷十九第四○條“二十七”小字誤作大字(第1009頁);卷二十第一條“云”誤作“言”(第1018頁);卷二十第二九條“澈”誤作“徹”(第1027頁);卷二十第三七條“夫”誤作“父”(第1030頁);卷二十第一二四條“以”誤作“所”、“氏”誤作“字”、“世”誤作“後”(第1060頁);卷二十第一二五條“叴”誤作“厹”(第1060頁);卷二十第一四二條“天”誤作“夭”(第1068頁)等,點校者皆未改工作本之誤。
建議掃描一部底本,請校對覆核。
二、校勘
1.關於點校者徑改底本之處
與點校者交流此問題,他表示對宋王應麟原文與清翁元圻注文採取不同態度,王氏原文“奉若經典”,無版本依據絶不徑改;翁注則爲避免繁瑣,對某些可以確定的、有唯一性的人名、地名、書名、民族名或者根據上下文可判斷其是非的明顯訛誤徑改。詳見後附《〈困學紀聞〉徑改底本記録》(附件此略)。
原建議“某些漏誤脱衍似可以用圓括號、六角括號在原文標改,不必出校勘記”(詳見《初審意見》相關條目及相應復審意見),這樣既保留了底本原貌,又避免出現並無太大價值的校勘記。但目前全書均未採取上述校勘形式,此涉及全書體例的改變,需斟定。
2.校勘中他校所引之書一般不注明版本
偶有出注的,一是版本不統一,如《漢書》,第285頁校勘記①、第391頁校勘記①、第502頁校勘記②等標“中華書局校點本”,第626頁校勘記①則標“今本”,其他大量的是不注版本;又如《水經注》,第877頁校勘記②③標“通行本”,而同頁校勘記①則不注版本。
二是引用版本或不妥,如第930頁校勘記③、第933頁校勘記①據《杜詩詳注》改,杜詩宋本有《宋本杜工部集》(《續古逸叢書》影印)、《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中華書局影印)、《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杜工部草堂詩箋》(《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等,爲何偏選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又如第22頁校勘記①等引用《四庫全書》本,首先要查有無更好版本(第976頁校勘記①),再者引用時當注明是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或其他版本。
建議請點校者出具一份《引書目録》,注明引書的作者、書名、版本(本書中除版本校外,大量均爲他校,據估測,點校者綫索多是檢索電子版《四庫全書》所得,故有必要核實一遍“善本”)。
3.校勘記引書出據到哪層——作者名、書名、卷次、篇名,全書不統一
如《資治通鑒》,第923頁校勘記①:“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九十後周紀一考異改。”第1000頁校勘記②:“據資治通鑒考異改。”第1053頁校勘記②:“據資治通鑒改。”又如《詩經》,第195頁校勘記①:“據詩經改。”第199頁校勘記①:“據詩經 雄雉改。”
全稿絶大部分引校勘記書只出書名,建議至少出到篇名,且全書體例統一。
三、目録
附全稿編次、目録(附件此略)。與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相較:
(1)上古本分兩個目録,一個是“代前言”之後的《〈困學紀聞〉總目》,二是《總目》、提要、序、凡例之後的《目録》(即底本目録)。本稿只列了一個目録。
(2)上古本《總目》文前各序的定名,是編者重擬,優長在於使人一目了然是何本何序。本稿所列之目,乃依據底本,二級序題是點校者所加,文中已出注,優長在於尊重底本,且層次清楚。
四、版式
附正文、《困學紀聞注編目索引》已排版校樣(附件此略),提請審定後再排全稿。
考慮小標題内容、位置會調整,《索引》最好待正文定稿後再編製(提取各條小標題和頁碼)。
復審意見
复审姓名:李静
职务/ 职称:编审
日期:2013 年4 月15 日
責編非常用心,前期已經提交過初審意見,此爲發稿意見。
《困學紀聞》雖然經孫先生之手就出過兩個版本,但是這版確有許多提升之處,尤其是在責編細緻的加工之下。
同意責編提出的掃描底本建議。
對於徑改底本的處理,孫先生似乎爲了使自己的做法有所依據,特地在《點校説明》做了詳細説明。但是看責編録出的徑改記録,有些確已超過了此界限。古籍整理還是以保留底本原貌、儘量少徑改底本爲原則,最好是改字出校。
引書目録很有必要,也可以避免在校勘記中繁瑣出注。
同意現在擬目方式,請補其他版本序跋的詳目。
版式可以依此排,請把中縫再上提一些。另請注意附録中縫與正文中縫同高。
以上意見請三審再閲。
終審意見
終审姓名:顾青
职务/ 职称:总编辑
日期:2013 年4 月20 日
覆核底本的工作應該做。
不用方圓括號了,可酌情出校。
“引書目録”應當編,但似稱“校本目録”爲好。目録中之主書名與校記中的書名要統一,否則又生出新的錯來。
出篇名,是否工作量太大?只要在“校本目録”中注明版本卷帙,篇名在校記中的作用就減少了。請酌。
索引如何編好,請再仔細考慮。
整個意見我都讀了。責編下了功夫,我很贊成。孫先生在《點校説明》中贊以“三傳統”,然也。希望在校樣階段更加仔細,把此書做成一個善本。
編輯按
《困學紀聞注》是我做古籍整理編輯的“處女作”,六七年之後,再重讀當年的初審意見和審讀報告,有很多意見實際不太成熟、精到,今一仍其舊,並附復審、終審意見,僅供業界同仁參考,並希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