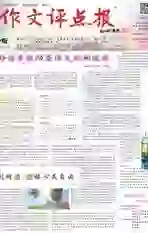零善良反应
2019-08-09胡展奋
胡展奋
【导语】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我们不仅要顺从外在的自然规律,还要遵从内在的道德良知。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道德的天空,正是这一片片天空,撑起了整个社会的蓝天。没有人能把自己的行为隔离于社会之外,每个人都以一个社会人的身份维系着道德的一环。不要让自己的行为毁坏了天空的完美,也不要因为自己的天空塌陷而造成整个蓝天的破损。
如果我们放弃道德的追求而竞相与低俗、丑陋为伍,如果支撑社会的只能靠法网,而不是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樊篱,那么,这样的社会绝不会是和谐的社会,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公民也绝无真正的幸福可言。
报纸忽然进行诚信危机的探讨,从球场到商场,再到考场、情场甚至讲坛、法庭、手术台……总之,一切名利场,似乎都有诚信沙化的阴影。国人总算开始明白,曾经被讥为“几钿一斤”的道德一旦沙化是可以真正“要我们的命”——首先是经济秩序的“命”了。
更要命的是,也许久处“鲍肆”,也许是近朱近墨的缘故,我们对自己的人格沙化早已是浑然不觉的“齆鼻儿”,以至于突然换个环境后,才猛然发觉除了饮食习惯之外,已经不习惯人们对我们的善举了。
那是去年九月一个美好的夜晚,我走出饭店,按地图所示,准备坐有轨电车去欣赏维也纳夜幕下的圣·斯捷潘大教堂。上车发觉没有售票员,也没有投币机,我又不通奥地利语。正尴尬时,一位穿着非常大胆的少妇指着我拿钱的手,摇手示意。
难道是鼓励我逃票吗?或者认为我钱不够?我疑惑着。
少妇见状,干脆走上来,指着我的手要我把钱塞回上衣口袋里去,又指指车,双手抱胸,闭眼,仰头,做一个若无其事状。
啊,我明白了,这环城的电车大概是免票的。到站了,她又示意我七拐八拐地跟她走,街上行人还是很少,我脚步迟疑着,心里又开始七上八下:她是干什么的?“维也纳流莺”吗?看她那么坦然又不像……否则那揽活的眼光也太不职业了,难道是看不出像我这样坐电车的游客身上只有一百多先令吗?要不,是个“托儿”?绑了我当肉票,向代表团勒索赎金?
而且圣·斯捷潘大教堂真那么远吗?静静的巷子里只有她脚步很重的皮鞋声。她比我高出整整一头,看上去像北欧种马一样壮实,虬结的背阔肌将衬衣撑得像藕节一样,真要动手,她的摆拳一定可以把我的左腮打得像“汤婆子”一样瘪进去……
正这么全力将她妖魔化时,小巷一拐,立即一片流光溢彩,大教堂如同一座琉璃山耸立在广场上。
她回过头来,对我阳光一笑:拜拜!
随后迅速消失在夜幕里。我歉疚地看着她的背影,不禁又想起几天前的“挪威雨伞”。
八月的卑尔根什么都好,就是雨多不好,那天也是晚上,我独自在雨夜中行走,没带伞,十分狼狈,只听得背后始终有人不紧不慢地跟着我,我走快,他也走快,我走慢,他也走慢,毛得我头发根根竖起。
走到著名挪威音乐家格里格铜像前,他忽然“哈喽”一声,紧上一步,把伞递了上来,而我居然像被剥猪猡一样地下意识大吼一声:侬做啥?
完全是“沙化”的下意识,本能的“零善良反应”。
那是一个高个儿的挪威老头,路灯下歪着头傻了半天,像瞅怪物似的瞅我,嘴里挪威语叽叽呱呱几句,指指对面的房子,把伞往我手里一塞,就奔进对街的门洞里去了。
原来挪威老头只是执意要把伞送给我这个“巴子”罢了。
圣·斯捷潘大教堂巨大的管风琴响了,我胸中突然涌满一种陌生的热流——我本善良,为什么如今处处怀疑善良?
(选自《杂文选刊》)
【赏析】
走在异国他乡,面对陌生人的善举,心存警惕,总是想着对方企图加害自己,这似乎是人们的“惯性思维”,作者却从这一“惯性思维”里看出了诚信的沙化。久处“鲍肆”,闻香也臭;近朱近墨,竟至色盲,这实在是可怕的事情。生活中不讲诚信的事情经历多了,于是整个世界变冷漠了,可以理解。但是,当你总是用警惕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戒备之心诚然可以理解,但你到底玷污了善良,歪曲了世界,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一个对世界高度警惕的人,你不会在别人需要善良的时候慷慨地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