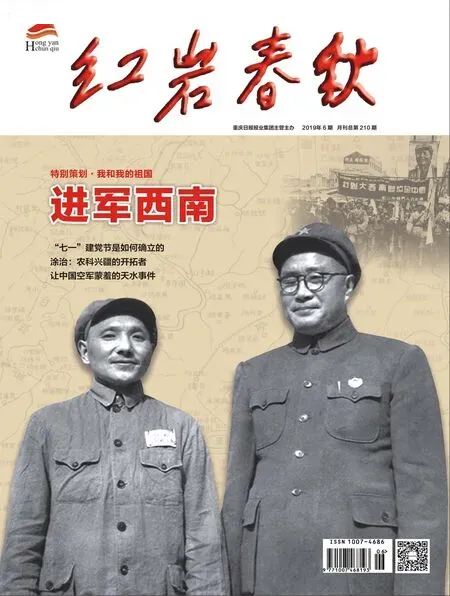一个印度记者的重庆之行
2019-08-01刘志平
■刘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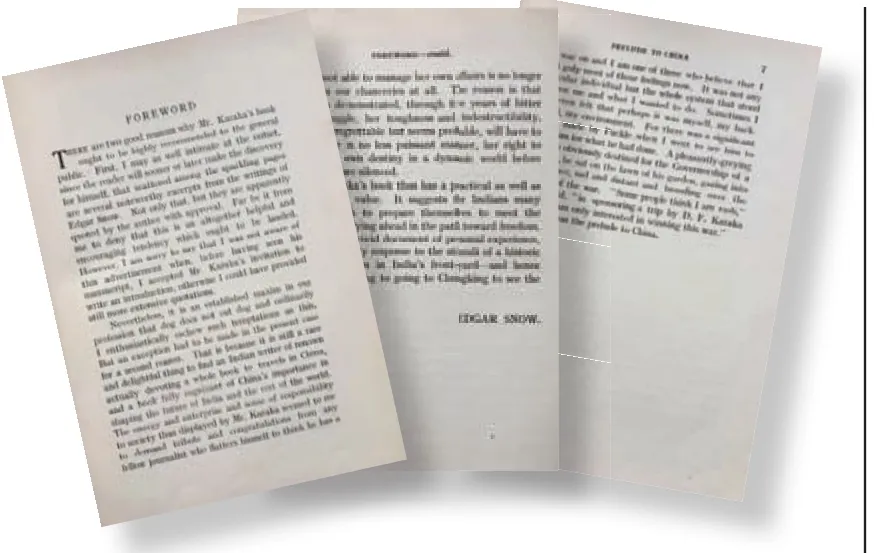
◇《重庆日记》原著
本书的历史背景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政机构撤至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中心,先后有24个国家在重庆设立外交使馆,世界各大新闻媒体也纷纷迁往重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席卷东南亚,香港、新加坡、马尼拉、西贡、曼谷相继沦陷,各国记者陆续从战区、缅甸、印度迁至重庆,重庆顿时成为亚洲陆地战场的新闻中心。
美国的合众社、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法国的法新社、哈瓦斯社,苏联的塔斯社,德国的德新社等世界大通讯社都在重庆建立了分社或派驻记者。美国的《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芝加哥日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及《时代》《生活》《幸福》《读者文摘》等新闻单位也有驻渝记者。1942年夏,美国政府在上清寺设立美国新闻处,年底在两路口建立办公楼。1944年10月,美军新闻机构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建立广播电台,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的美军官兵收听新闻和娱乐节目。派驻重庆的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法国的《巴黎日报》《人道报》,苏联的《消息报》,瑞士的《苏利克日报》和加拿大的《新闻报》等报社的记者,以及澳大利亚、意大利、波兰等国记者。与此同时,一些由外国机构和外国人主办的报刊也在重庆出版发行。
新闻广播在抗战时期也呈现出国际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中三国决定成立反侵略国家联合宣传委员会,以重庆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为会址,开放国际广播电台部分时段,供各国记者对外广播新闻、通讯,并建电台供外国记者发稿。外国记者经国民党中宣部介绍,可以到中国中央国际广播电台(XGOY)直接播出自己的节目,并通过本国电台定时转播交换XGOY的外语抗战节目。
为配合和服务各国新闻媒体在华新闻报道,1938年底,重庆国民政府在两路口巴县中学校园内设立了国际宣传处和外国记者招待所,每周五午后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1942年,重庆成立了外国记者俱乐部,拥有会员30多人,由纽约时报记者艾金森任会长,美国《时代》杂志的白修德、苏联塔斯社的叶夏明、英国路透社的赵敏恒任副会长。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本书作者棵拉卡来到重庆,《重庆日记》是他驻重庆期间的一部日记体著作。
本书说了什么
多索·弗兰杰·棵拉卡(Dosoo Framjee Karaka 或D.F Karaka),1911年出生于印度孟买,1930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林肯学院攻读法学。在校期间,棵拉卡开始着手撰写纪实类文学作品,后从事新闻工作。1938年棵拉卡回到孟买,任《孟买记事报》记者,后升任该报编委。
二战期间,棵拉卡作为战地记者赴欧亚战场进行了一系列深度报道。他的首次外派是在1939年尼赫鲁访问重庆和1942年春蒋介石回访印度,中印两国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进一步加强联系的背景下成行的。之后,他作为英国第14集团军随军记者深入缅甸,见证了科希马战役和英帕尔战役的战前准备。1945年初,棵拉卡被派往欧洲,报道英美印联军在意大利的作战。他是第一批到达并目睹贝尔根·贝尔森纳粹集中营惨状的记者之一。同年5月8日,棵拉卡在法国兰斯亲眼见证了纳粹德国的投降仪式。
作为首位来渝采访的印度战地记者,在当时的背景下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印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尼赫鲁亲自致信印度驻中国领事馆,为棵拉卡在渝采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重庆,除蒋介石由于前线视察未能受访外,棵拉卡采访了国共两党各个层面人物,如周恩来、董必武、陈家康、龚澎,并应邀到访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村,见到了邓颖超;采访了宋美龄、孔祥熙、顾诩群、蒋廷黻、吴国桢、杭立武等国民政府高层人物,应邀到访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等地。棵拉卡得到国共两党高规格接待,处处受到重庆人民的欢迎,这些情况在《重庆日记》得以真实反映。
作者在重庆仅仅一个月时间,以日记的方式,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发生在中国的“历史性抗争”——抗日战争。《重庆日记》一书对盟军轰炸东京、盟军作战计划、印缅战事、1942到1943年日军战略意图、重庆的防空系统暨大轰炸下重庆人民遭受的苦难、重庆人民对大轰炸表现出的坚强和淡定、国民政府战后计划、中国共产党暨中国人民对抗战抱有的必胜信念等等,均有生动记录。作者富有极强的洞察力和政治远见。在1942年上半年,凭借一个月对重庆各界的短暂接触,便预见到战后中国的发展趋势暨国共两党的政治前途,不禁令人惊叹!
作者在书中对中国面对强敌独立苦撑及其坚定的抗战意志表达了由衷的敬佩和赞赏:“从军事角度而言,中国军队没有重型装备和有效的空中支援,也缺乏坦克和大炮,前景看似暗淡。但是我确信,中国人绝对不撂挑子,他们绝不会投降。”“在重庆,人们不得不放弃很多,放弃那些仍然被印度人视为‘必需品’的东西。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自我牺牲是如此的不同。……但是这里没有对困境的埋怨,没有悲悯,没有任何时间被浪费在自我同情上。”“没有人能夺走这些中国人在艰苦卓绝的保家卫国之战中所取得的功勋,他们往往在胜算很小的境况下奋起抵抗。正是鉴于他们的坚毅和笃定,盟国理应在远东投入更大的精力。我身处于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民族之中,深感震撼和鼓舞,哪怕时间很短暂,也足以让我从他们身上吸取到这种向上的精神。”

◇1940年的重庆
作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说:“这些共产党人让我有些着迷。当我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为亚洲而战》的时候,每当我读到他描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精彩片段之时, 我总是迫不及待地翻看书中三人的照片。眼睛炯炯有神的毛泽东,面容威严的朱德,还有欧陆风范的周恩来,都促使我想进一步了解他们。从几乎所有的报道来看,毛泽东是三个人中最伟大的——一个为未来而生的人。他不仅务实,而且具有惊人的直觉。他的很多预判都实现了,往往超乎大家的预期。他似乎考虑的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他的思考言简意赅,而且往往最初看似美好得不真实。”“当全世界都完全错误地评判《慕尼黑协定》的时候,毛泽东的认识非常透彻,就像苏联所认识的那样。作为一个出身农民的领导者,一个未在正规学府接受过政治思想指导的共产党领导者,毛泽东如此般的思想和洞见,体现了中国的共产党领导者们的远见和恰当性。”

◇顽强不屈的重庆人民,坚守到了最终的胜利
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者也给予了高度赞誉。“八路军从未停止脚步。相信我,这不是一支在战争中身着漂亮‘制服’而幡然起舞的队伍。这支队伍将是中国未来的核心。当你发现,这支军队是依靠着从敌人缴获的武器而继续奋战,在药品短缺的情况下,伤病往往依赖自然恢复或者上苍的眷顾,而非科学和药物治疗,你将开始相信,这些人注定将掌握中国的命运。”
作者不仅旗帜鲜明地赞扬中国的抗战,还批评印度对于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说,“任何针对日本人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都太不了解日本士兵了”,“非暴力不合作作为理想非常伟大,但是在面对日本人的子弹和装甲部队时是毫无作用的”。作者视野广阔,对战事进程十分了解,他将战时中国与印度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广阔的背景之下进行观察、对比和记录,对印度的现状进行反思和批评。书中,他阐释了中国抗战对于印度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意义,并以自己的报道向印度人民展示“在通往自由道路上披荆斩棘的种种不懈奋斗”。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一名渴望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的印度青年,作者怀揣着对祖国命运的深沉关切和忧虑来观察中国、观察重庆。他说:“我知道得越多,越感到印度距离战争实在是太过遥远,以至于难以意识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在命运的齿轮和战争的漩涡中经历着什么。”“当我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感到所处的世界对印度的了解正在提升。能在《星期六晚邮报》读到埃德加·斯诺的这篇文章,作为一个印度人,我感到非常欣喜。埃德加·斯诺还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和《为亚洲而战》两部著作。我相信终有一天他的笔头会转向印度,撰写出一部具有独特视角和思考的著作,我很确信这一点。”
全书文辞流畅,且颇具幽默,不愧为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的书写。
价值何在
战时对外关系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战时中国与美英苏等大国关系研究成果颇丰,但关于战时印度暨中印关系的成果鲜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太平洋战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成为中英日外交角逐的焦点,更是中国抗战海外物资惟一通道。因此,战时中印关系理应是抗战对外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课题。
《重庆日记》第一版于1942年在印度出版,即将出版的中文译本是中国大陆首次翻译出版。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对书中的人物、事件、地点等作了大量注释,翻译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因此本译作在学术上颇有价值。
本书的翻译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译者利用繁忙的工作之余,星星点点积累时间翻译;同时作为一个非历史专业人士,尽管此前很喜欢读历史,但要做一部著作的翻译,则完全是两个境界。不仅需要以认真的态度学习历史,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还要尽可能秉持直译的原则,以忠实于原文。历经艰苦,《重庆日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80周年之际付梓,也是历史的眷顾。
可以说,该书是继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白修德的《亚洲的惊雷》以及奥斯卡获奖彩色纪录片获得者、美籍华人李灵爱的《苦干》(Kukan)》等作品之后,外国人记录战时中国暨战时重庆的又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