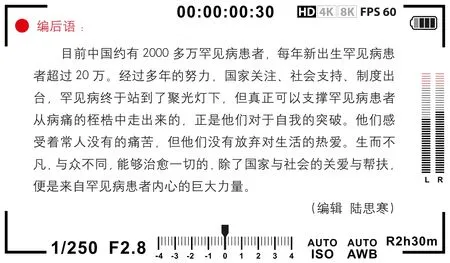生而不凡
——镜头下的罕见病人
2019-07-31吴靖肖涌刚
■ 文 吴靖 肖涌刚
她逐渐明白,对路人注视的猜测是基于自己的心理经验,“人家可能只是好奇看一眼,可能没什么歧视,但我也没有问人家,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然后自己在那里怄气。”于是,她学会了减少愤怒……


罕见病患者凌子
镜头中,一个头戴一顶鸭舌帽的短发女孩在做仰卧起坐,双手支撑起整个身体的那一刻,脸涨得通红,紧蹙的眉头上冒出了几滴汗珠。这是公益纪录片《生而不凡·人物志》中的一个画面。她叫凌子(化名),刚刚结束一段时间的轮椅生活,身体正逐渐恢复知觉和力气。
凌子今年33岁,曾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患上了一种无法被确诊的罕见病。从2006年到2017年,她失聪4次、呼吸衰竭4次、病危6次、瘫痪11次。而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是一对大学毕业不久的表姐妹,姐姐叫闫潇,妹妹叫王赛。她们选择了12位罕见病患者作为拍摄对象。这些罕见病患者有着不同的社会身份:除了自由职业者凌子,还有学生龚、漫画家翟进、医学生亮亮(化名)、徒步爱好者潘龙飞、外企工作者美好、8岁东北男孩马浚祖等。他们所得的病,是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的医学名词: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X-连锁股脊髓延髓肌肉萎缩症、脊髓性肌萎缩症、白化症、粘多糖贮积症一型、的兰氏综合征、庞贝氏症、卡尔曼氏综合征、成骨不全症、神经母细胞瘤等等。

纪录片导演王赛(左一)、闫潇(右一)和罕见病粘多糖贮积症患者张笑(中)

闫潇与罕见病患者在一起
镜头后的初心
2012年8月,刚要上大一的闫潇被查出患有重症肌无力,此前她的生活与常人无异,直到某一天,她的右眼忽然无法转动。而后几次,眼皮突然下跌,眼睛用力往上看,看到的反而是自己的眼皮。她没当回事,以为是备战高考累的。
高考刚结束,某天和弟弟闹着玩,弟弟轻轻推了她一下,她一下就倒下了,感到全身没有任何力气,难以起身。辗转了几家医院后,她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而由于没有特效药物,医生建议吃激素缓解病情。之后的日子,她每天都需要吃8片激素,而其所带来的副作用是一上午四节课要睡上三节。更糟糕的是,她几乎无法控制情绪,常常坐在座位上听着歌,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在走上拍摄纪录片道路之前,闫潇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要做什么,“我生病以后,想得最多的就是,当我突然死去时,依然一事无成。”2016年6月,闫潇毕业后和妹妹来到北京,妹妹是编导专业毕业,这部公益纪录片的拍摄就被闫潇提上了日程。闫潇曾在参加“I CAN(我可以)协力营”活动时,认识了创办人王奕鸥。而王奕鸥已经是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的创始人,听说她有拍纪录片的想法,愿意拿出资金支持。
王奕鸥还叫上了同事张皓宇,由张皓宇负责招募和接洽被拍摄对象、后期宣传、对接平台、筹集资金;穷拍姐妹负责拍摄和剪辑;王奕鸥自己负责审核每期拍摄主题,提出修改意见。
“生而不凡”这个主题,是张皓宇想出来的。他突然发现,“我们之前一直在宣扬,我们一定要跟别人相同,因为我们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罕见病患者就是不同的。”
镜头前的痛感
14岁的某天,他突然发现自己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要靠轮椅代步了。“原本写字稍微慢一点但是不费力,到了现在,胳膊开始逐渐没劲。”他用两根手指夹住一个芥末豆,头快倾斜到轮椅的桌子上,手指微微一抬起,豆子刚好停在了嘴边。“患这个病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生活。我们肌肉没有力量,上厕所都不能自己上。”因为离不开护工,他甚至错过了一次出国读研的机会——办理签证时,对方不同意他申请,其理由是不能带护工。
社交对于他来说也很奢侈。虽然是硕士毕业,但投了简历石沉大海,在长达近1年的时间里没有找到正式工作。而因为长期吃激素,凌子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的状况,晚上常感到疼痛,睡不着觉,这在医学上是不可逆的,后来,她干脆换了人工关节。
24岁的张笑,一位粘多糖贮积症一型患者。2017年,她开始感到手部发麻、手指更加不灵活,去医院做了很多检查,结果都指向一种名为腕管综合征的病。患该病的人在纸上写字,慢而费力。
王赛记得,某次在笑笑家里拍摄时,笑笑在接到一个电话后,叫停了拍摄,那次电话是病友去世的消息。在访谈中,笑笑对着镜头说:“我害怕突然有一天就再也见不到她们了。”
生活中的拒绝
多数罕见病患者第一眼看上去确实是不同的。那些坐着轮椅的、说话有些吃力的、走路微跛的、身形很胖的人,或者是头发全白的、身形矮小的人……如果身体特征与外界认知年龄或性别特征不相符,常会被侧目和注视。这些来自外界无形的评判压力,让他们曾一度难以接纳自我。

罕见病患者小虎,患有“的兰氏综合征”
第一次倒下开始坐轮椅那会,凌子不敢出门,“害怕人家看我”。她脾气冲、性子急,推车去路上,路人一看她,她就特容易生气,一定要骂人家,“看什么看”,跟自己较劲。那会儿,她对自己的描述是,“内心戏特足,画面感特别强”,总是会臆想:在一个场景里,不停地有人告诉她,她受到的这些注视和目光都是恶意的。
纪录片拍摄的那段时间正是凌子“最迷茫的时期”,一开始,她不愿意面对镜头。镜头前的访谈,不论对于罕见病患者本人还是这个家庭,有时仿佛是再次揭开伤疤。
纪录片中,医学生亮亮的访谈也曾一度难以进行。亮亮是一名白化症患者,因为皮肤及其附属器官黑色素缺乏,亮亮的头发全白,这让他在人群中显得尤为特殊。第一次和亮亮聊的时候,闫潇想让他回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他不愿意。他只记得,小时候在农村,没有一个医生告诉他病因,没有给他一点鼓励,让他一度很自卑、“生无可恋”。那个时候,他头脑中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最极端的一次,他想寻短见,最后被母亲用绳子捆住拦下,关在房间。
31岁的小虎(化名)是一名患有的兰氏综合征的罕见病患者。这种病经常会出现行为、沟通交流问题以及发育迟缓等症状。
小虎的妈妈曾面对过不少媒体,但那些报道有时会与她真正想说的话有距离。她问小虎的意见,小虎有些犹豫,但最终表达了自己的信任,“他太希望能拥有朋友了”。她考虑再三后同意拍摄,一是觉得这种病需要更多人知道,二是因为她和小虎曾与闫潇、王赛在一个项目接触过,小虎和她们玩得很开心,她觉得这是两个很朴实的小姑娘,“心地特别纯洁”,才减轻顾虑。
接纳自己与他人
凌子意识到自己开始逐渐接纳自己“罕见病”身份的时候,是在“习惯”被旁人注视的那一刻。有一次她出门,突然很疑惑“为什么周围没有人看我了,大家都怎么了”?看了看自己,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已经不坐轮椅了,“大家不看我,我倒觉得纳闷”。
后来,她逐渐明白,对路人注视的猜测是基于自己的心理经验,“人家可能只是好奇看一眼,可能没什么歧视,但我也没有问人家,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然后自己在那里怄气。”于是,她学会了减少愤怒。
有一次,她坐着轮椅去商场,保安拦住了她,指着车不让进。凌子解释这是残疾人用的车,保安还是说不行,指了指商场门口的标志,标志显示带轮子的车不能进。她没有像以前一样认为这是歧视,“那你把领导叫来,我和他说”。最后,领导过来,双方沟通后,凌子顺利进入商场。“要是以前,早就爆发了。”她回忆起这次经历,偷乐着,“我也很诧异自己的变化”。
起初,张皓宇也害怕轮椅。他是成骨不全症患者,走平坦的路都能跌倒,常年坐轮椅。研究生毕业后,他选择做北漂。直到有一天,为了看音乐会,他摇了7公里到一个酒吧,“轮椅可以带着我去我想去的地方,爱好自由这种感觉,感觉很爽”。
纪录片中24岁的美好(化名)在一家外企工作,她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常年坐轮椅。好多病友会劝她: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不容易,找一个男朋友或者回家结婚才是最好的归宿。她很失落:“好像因为坐轮椅,就放弃了自己的整个人生,就放弃了自己选择的权利。”
她面对的人群是残障朋友。她发现那些病友还是处在一个固化的模式当中,每天过着消极、重复单一的生活,还会把残障这个标签过于放大化,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残障。“与其残障人士抱团取暖去议论社会大众的不关注或者歧视,倒不如真的出现在大众面前,告诉他们,我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美好笑着说。
纪录片中的翟进是一名成骨不全症患者。因为少年画漫画成名,一直被当成励志典型,家里常被媒体光顾。“我特别不喜欢那个感觉,就是别人先看到我的身体,再看到这个人。不关心我画的是什么样的,就说我这个状态画成这样,很厉害。”他内心想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翟进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在漫画里,画各种各样性格脾气的残障人士,“画里的残障人士不是必须正义的”。
真实的转变
现在的凌子,一个人居住在一居室里,买了两个小音箱,经常会放英文歌曲给自己听,听着听着会一个人跟着音乐跳起来,“那一刻觉得特别开心。”凌子开始参加一些戏剧工作坊,和别人分享她的感受。她决定未来当一名婚庆策划师,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那种幸福感,“现在人幸福感太低了”。笑笑偶尔还会感到手麻,会需要他人帮忙。但她开始根据医生建议,坚持锻炼,缓解病痛。美好在试图走出舒适圈。她此前一直在公益圈里,久而久之产生一种疑惑:“难道我的圈子就真的局限于这些人了吗?重复地生活,永远在做那么几件事,接触几个人,就会影响到我去探索真正的自己。”翟进换了一辆新轮椅,正在学习从依赖电动车到靠双手摇行,他开始习惯想出门就出门,习惯承担各种家务,习惯和朋友热热闹闹聊天,龚开始进入北京美儿SMA(脊髓性肌萎缩症)关爱中心工作,开始有更多时间和周围的人交流。“推出去好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