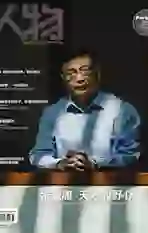樱花开的时候,我们再见
2019-07-30童道明

“这样,我们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都能见到了”
快70岁了,童道明开始写爱情。年轻的朋友失恋了,他就写一部戏,讲一对男女怎么相遇,又怎么分开,让这位朋友去导。演出的夜里,观众围坐,两位演员就在圆形舞台中间。剧场里挂了许多白纱,朦朦胧胧的,台词里有普希金和李白,有《安魂曲》和诗。刚好停电了,现场点了蜡烛,风一吹,白纱飘了起来。隔了好多年,演员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晚上,“大家都傻了,太奢侈了。”
童先生也跟人聊爱情。他什么都能看得明白,能体恤人最细的感情。“爱情是会让人痛苦的”,他说,“契诃夫的《三姐妹》早就说过了,200年之后,可能我们还是会像现在这样痛苦,但是痛苦能让人思考怎么活着。”
朋友们感慨,老爷子真浪漫啊。现代人之间有许多信不得的承诺,比如“咱们下次再约”,“咱们找机会再见”。童先生不这样说,他会告诉你:“咱们樱花开的时候再见面。”等到樱花快开了,他的电话真的就打来了。去年中秋节,他和戏剧制作人刘海霞约吃饭,说我们下午先去喝咖啡,晚上再吃饭,吃完饭就坐在长椅上看月亮。“这样,我们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都能见到了。”
潘家园附近那栋社科院家属楼的四楼,就是童道明先生的家。你会觉得这屋子老了,家具是旧的,沙发、镜子、水杯都是老式的。书塞满了整整三面墙,有些是半个世纪前的装帧,泛着深浅不一的黄色,提醒你流逝的光阴。它们堆得没那么整齐,不过爱书人一看便知,那是常常翻阅而造成的凌乱。
但只要踏进门槛,稍作交谈,你就知道,这屋子的主人还年轻呢。
60岁之前,童道明是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沉默地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写剧评,不为大众所知。退休后,他反而爆发了创造力—60岁完成了第一个剧本,75岁时出版了第一个剧本集。他说自己常在心里默吟契诃夫的一句话:“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生命的脉搏跳动得愈加有力了。”
两年前,他80岁了,开始更新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童道明札记”,每周两期。他不会用电脑打字,每回都是手写了,发给在国外读大学的外孙,外孙再打好字,传上去。最开始童道明刹不住车,洋洋洒洒一篇写好几千字。外孙抗议了,这工作量太大了啊,他只好把篇幅缩短到了每篇不超过400字。
今年春天,在自己的82岁,童道明写完了最后一部戏。距离戏上演不到半个月的日子,6月27日,他在北京病故。八宝山的追思会上,有好多泪眼汪汪的年轻人。演员濮存昕在现场说,“童道明真心热爱戏剧和戏剧行业里的人,对戏剧有很多浪漫的想法,但同时又对应该坚持的,坚决捍卫。”
每个受访者都说起他温柔的坚持。他如何在60岁之后,与快速流逝的光阴斗争,通过创作获得自我实现,也让自己自由浪漫的天性舒展。
与这样一个人交朋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年轻的朋友张子一想起,有一年她循着童道明的指引去俄羅斯旅行,在海参崴的海边看到几个身材健美的俄罗斯少年在海里扎猛子,爬上来跳下去,爬上来再跳下去,一直扎了一个多小时。黄昏里的这一幕她久久不能忘怀。她觉得童道明也是那个“啪啪”扎猛子的人,只不过少年有的是体魄,他有的是丰沛的情感和创造力。
“一方面你会很欣喜,感觉世界上有这样的人的存在可真好啊。另一方面也会觉得很害羞—哎呀,我和这个最好的人、就在身边的人,差得可真远啊。”
自由
这些年,只要天儿好,跟人约在家里见面,童道明总会提前很久下楼候着。有一回戏剧制作人刘海霞提前20分钟到,想到点儿再上去,发现老爷子已经在他家楼下的长椅上坐着了。每到节日,就算是只见过一两面的朋友、报社约稿的编辑,也会收到他的信息。他在短信开头庄重地写上对方的名字,让年轻人们受宠若惊。
与人交往,他永远有老派的得体。2017年,台湾剧评人李立亨带了老家基隆的凤梨酥去拜访他。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他要回赠礼物。可是除了已经给的新书之外,实在找不到东西。他很腼腆地说,“我弟弟送了我一个牙膏礼盒,你可不可以收下?”
看一个写作者是否温柔,是否善良,文字是最诚实的。他这样写卞之琳先生—卞先生去世前好几年就不出家门了。热心的年轻人张晓强倒不时去看望看望他。回来还告诉我们一个他的发现:“卞先生喜欢吃炸马铃薯片。”“为什么?”“他喜欢听马铃薯片咬碎时发出的响声。”我听了一怔,心想:卞先生好寂寞。
这种强大的共情能力,从契诃夫身上来。他总说:“契诃夫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是我一生的幸运。如果没有契诃夫那少有的善良,他就写不出他后来的作品。”
童道明一生受契诃夫影响。1956年,他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上学。文学系三年级时,进入契诃夫戏剧班,写了一篇论文,《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毕业前老师嘱咐:“童,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放弃对于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这句赠言像金子般珍贵,直接决定了他一生的追求。


在当时,契诃夫、文学、戏剧,都是脱离现实的梦。回国后,他很快遇到“文化大革命”。1970年初夏,他所在的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被集体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离开北京前,他珍藏的所有文学书籍都被迫当废纸卖了。漫长的劳动岁月里,他就靠反复背诵莱蒙托夫的诗歌支撑自己。
翻译的欲望强烈得不可遏制时,他便称病,用检查身体的短暂三天,躲到招待所译完了剧本《工厂姑娘》。多年后他回忆那个晚上,“六年来,我头一次动笔翻译,头一次感受到了精神劳动的欢愉。我不知道那天怎么吃的饭,我只知道我坐在那张暗红色的桌子前,一直翻译到熄灯睡觉。躺在床上一时难以入眠,我很兴奋,也很痛苦,我想到一个道理:在文化大革命里当知识分子是很难的,但让一个已经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再当知识分子,那可能更难。”
终于到了60岁,挣脱了所有社会角色的枷锁,他获得珍贵的自由,开始埋头写作。
他是出了名的温和派,说话不点破。他曾经向李立亨解释创作的缘起,是因为看到契诃夫讲过: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内心的平静。而他的生活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平静。他觉得现在可以把生命的顺序倒过来,开始创作了。
与他同辈的剧作家林克欢,理解他的选择。林先生在悼念文章里写:“童道明、王育生和我这一代人,刚踏出校门不久,即遭遇十年磨难,经历不尽相同,却都是这场创深痛巨的灾难的受害者与盲目跟从的加害者……童先生晚年舍理论著述而近舞台实践,何尝不是想借艺术语言模糊的诗性,撞开历史无意识背后的一方象征空间,纾解外部与内部的多重压力,使精神得以自由呼吸。”
童道明的剧写老所长冯至,也写爱情,还有4部是为了致敬契诃夫。编剧史航读契诃夫,也读童道明。他认为他们相似,都是那么内向的、羞涩的、容易受感动的人。
童道明曾跟后辈、台湾剧作家李立亨讲起,契诃夫是个心很美的人。“因为他的小说跟剧本,即便说到许多人心的不堪,还有时代所堆叠出来的恶,里面所闪烁出来的光芒,永远都是美,都是善。”
李立亨至今记得,童道明讲到契诃夫剧本《樱桃园》的结尾“远方传来砍伐木头的声音”时,眼里有泪。“这个故事,他读过多少遍,这个场景,他跟别人提到多少遍了。但是我相信,他每次说到这里,一定一次次受到剧作家笔下灵魂受苦的震撼。”
契诃夫推崇弱化戏剧冲突,童道明的剧本也是同样的气质,从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李立亨说,“跟他本人的性格一样,平和温暖而没有火气。想要在他的剧作里发现‘戏剧性冲突,最多也就是累积到剧末的死亡和无尽的惆怅。”
他想表达的不过是: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所有的选择都是缓慢形成的;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彷佛什么事情也都没发生,只不过,大家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都变得不一样了。
最开始排戏,童道明就告诉导演张子一,电影没有留白,电影也没有当众独白,但是戏剧有,戏剧可以当众独白,戏剧也可以有留白。演员对着舞台,就可以直抒胸臆。
“童老师,这很土啊!”受现代戏剧影响的年轻人最开始受不了这个,但后来张子一想明白了:“后来我觉得,它必然是土的啊!它就是不合时宜啊。童老师的浪漫是上世纪60年代的浪漫,它是往哪儿放?它是没地方放的啊。”作为导演,也许她要做的就是保留这种不合时宜。
刘海霞记得,他非常少有地给一部戏提过意见,是在《一双眼睛两条河》里头,一对男女相遇了,但他们都各自有家庭,所以就是在文学艺术里拥抱一会儿,最终还是要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去。排戏时,另一位导演不想像剧本安排的那样让他们拥抱,他觉得要维持那样一个朦胧感。老爷子激动了,说一定要拥抱,“他们是人啊!他们是人啊!”
“我以为我能写三部,但是呢,我又写了五部”
生命的最后10年,童道明喜欢跟大家待在剧场里头。他总是慢慢地拖着步子,走到舞台中央,再慢慢地说出沙哑的、带着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因为有强直性脊柱炎,他没办法低头,就一直直着脖子,看着天。“他很诗意,也很害羞,所以在讲很多话的时候,他是不愿意把话都讲全的。”
但人们都能感受到他的纯真。张子一说,他是一个很少被外界惊扰到的人。“所以他跟你交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就是盯着你的,在跟你说话,外面的人就沒了,世界也没了,他专注,是因为他比较纯粹。”
在他逝世后,张子一开始重新审视这位老朋友,才想明白了,他身上最感动人的是什么。“他不轻视和怠慢他生活里面的任何人和任何东西。比如他有一张烤鸭兑换券,就会兑换给剧场里的人吃,我们可能吃饭吃一半,烤鸭剩在桌上就扔了。但对他来说,他不随意地去轻视任何一件东西,不随意怠慢任何一个人,就是这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给我的特别大的冲击。”
演员郭笑觉得,在上世纪60年代,童道明这种浪漫和诗意的性格,一定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这种不合时宜的浪漫得到了尊重和舒展。他是他们中间很自然的一份子,中秋节的时候,他可以和年轻人一起吃月饼,喝红酒,聊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到了这两年,他身体机能慢慢下降,走不了太远的路,去剧场的次数比以前少了。年轻朋友都忙,慢慢忘了他。他寂寞了,有自己的法子—就是出书。出了书,他就有理由挨个打电话,让他们去家里拿书。
他是敏感的,他家客厅挂着一个大钟,每回只要刘海霞抬头看钟,他就会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这样吧。”他怕耽误他们太久。
死亡这事儿,总是不经意就冒出头来。几年前,北师大的童庆炳教授去世。消息不知道怎么传错了,大家以为去世的是他。媒体的电话打到家里来,他接了,对方一阵错愕,连忙道歉。还有的觉得尴尬,什么都不说就挂了。好朋友王育生也听说了,电话打过来,哈哈大笑,“有人说你死了!”
有时候,他也会得意洋洋,觉得自己跑赢了时间。张子一的记忆里,他就是那样梗着脖子坐着,沉默一会儿,然后细细的声音开口:“其实我不知道我还能写几部戏,我以为我能写三部,”他顿了顿,一双狡黠的眼睛,举起一只手隔着桌子晃了晃,“但是呢,我又写了五部。”
实际上不只5部—60岁至今,他一共写了14个剧本。今年春天,他完成了最后一个剧本《演员于是之》。
演员于是之,是北京人艺原第一副院长。在《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等话剧里塑造过不朽的角色。童道明写过许多文章纪念他,他觉得于是之是他认识的人里,最像契诃夫的。“我像爱俄罗斯作家契诃夫那样地深爱着于是之。我常对人说,于是之和契诃夫有几分相像的,他们两个人都是极其善良的人,而且他们的文学的、艺术的成就,都是与他们的善良天性分不开的。”
后辈刘戎,是这两年见童道明最多的人之一。他觉得童道明写《演员于是之》,是有话要说。他是在话剧演员素质衰落的当下,呼唤伟大的演员。也是在提醒戏剧界,不要忘记上一代大先生们留下的传统。
今年春天,童道明把这剧本给于是之夫人李曼宜看过,便联系了剧场和导演。他秘密策划了7月的首演,想等一切尘埃落定,再请李曼宜去看。而如今,话剧还未首演,先生先去了。蓬蒿剧场的工作人员在微信文章里写:“两位先生,相会于天堂去论戏了。”
他一定是反复思考过死亡之事的。刘海霞想起去年秋天,最后一次与童道明见面时,他突然聊起死亡。他说自己读到一本关于俄国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回忆录。书中讲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弥留之际,一直在读莱蒙托夫的两句诗:
“在大海的蓝色的湾里 / 一叶孤帆在闪着白光”
他反复咂摸这两句诗,想知道导演为什么在那个瞬间要读它。后来他想明白了—这两句诗写出了生命逝去的时刻,那种孤独之美。导演与世界告别时是平静的,像一叶孤帆,要去远航。
女儿童宁说,父亲告别世界时也是平静的,他说,自己没有遗憾了。一叶孤帆,就此启程,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