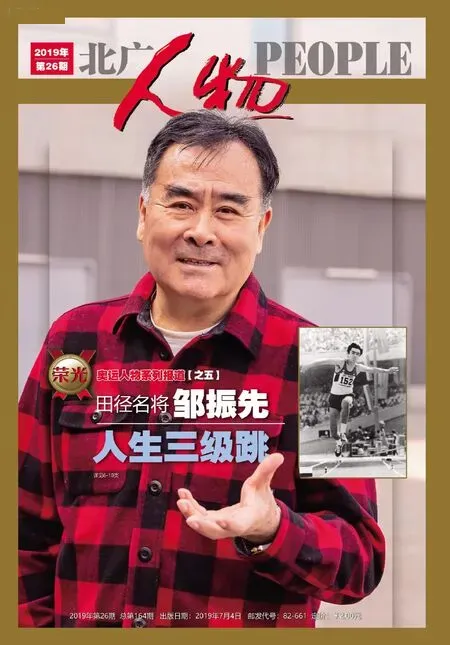民间工艺大师赵伟一蛋三绝
2019-07-22
独家专访本刊记者彭立昭

“天气热了,画几把小扇”,“晒晒近期学生的画,最小6 岁,最大9 岁。朋友们给我们的小伙伴们鼓励鼓励吧”,“昨日新作——金榜题名——祝所有考生”,“非遗走进老干部局”,“老大姐们画得认真,年龄最大的76 岁”,“非遗进小区”,“非遗进国际关系学院站”……曾创作出“一蛋双画、一蛋双雕、一蛋双绣”,被誉为“一蛋三绝”的民间工艺大师赵伟几乎天天在我们微信朋友圈里晒她的“小陶醉”——蛋壳上绣花。她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她的获奖证书,荣誉证书……当然也有她练习没完工的遗憾,比如有次她在鸽子蛋壳上刺绣一朵白牡丹,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活竟然没成功,“这个蛋壳像鸽子蛋壳一样薄,刺绣到这,完了……一针一针的把握好,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如今赵伟的名字已经入选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大辞典》中,作品也被入选《中国当代民间工艺名家名作选粹》。她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要用我的毕生精力,把老祖宗留下的手艺不仅传承下去,更要发扬光大。”
说起赵伟与彩蛋的结缘,还要从她的父亲说起。小时候,赵伟看到父亲在蛋壳上画画,觉得非常漂亮,便开始跟着父亲学习,自己动手画。她从厨房拿来一个煮熟的鸡蛋,用红蜡笔在上面画了一个红太阳,再找来一个装满白醋的透明玻璃罐子,把鸡蛋放了进去浸润两小时。等到把鸡蛋拿出来的时候,她发现鸡蛋壳慢慢地软了,她画的太阳不但没有掉色,且更加坚硬了一些……她逐渐对这门手艺痴迷起来,并决心将这门艺术发扬光大。
现在说起当初学艺时候的艰难,赵伟还是很感慨。“我父亲是个极其要强的人,掌握了许多技法,口传心授。”她说,父亲对她要求很严格,“一天不练习不行,三天不练习,就没感觉了。技艺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艺术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高不可攀。任何事情只说一遍但要求必须记住……”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赵伟深深地爱上了这门艺术。一晃中学毕业了,她去了“北大荒”,也没丢下过画笔。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她在油灯下继续画彩蛋,凛冽的寒风吹透了窗户也没让赵伟停下画笔。“越是这样,我越是要学。”她说。
有一次,有位老乡问赵伟,“你能不能帮我画一对儿彩蛋?”她想,只要能找到一模一样的蛋就可以了,但去哪找呢?思索中,她突然有了灵感,“盘古能开天地,我就不能开蛋壳吗?”功夫不负苦心人,她成功地将一个整蛋均匀地切割成两半,一半是天,画上“自强不息”;一半是地,画上“厚德载物”。将不同的蛋壳均匀地分割两半,这便成了她的“一绝”。
2008 年奥运会,赵伟用妹妹剪下的长发在蛋壳上绣下了“喜迎奥运爱我中华”八个字,一经亮相就惊艳众人。在蛋壳上用头发刺绣,便是她的“第二绝”。
最绝的,便是这蛋壳上的刺绣。
首先挑选白色的鸡蛋,大小均匀。她介绍,“为蛋打孔,力度要均等,下针要果断。抽干蛋液后反复沥清。切分蛋壳,需要逐层分割。蛋分四层,一层红色,二层酱色,三层白色,里层为膜,膜破即碎。然后打磨光滑,曲面构图,飞针走线。”
古时,蛋承载着原始生命繁衍的想象。《楚辞·天问》有言:“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浑然孕育,几多欢悦。在当今日常生活中,人们只会留意清软黄腻,至于蛋壳,敲碎即丢。但世间万物,没有谁生来就属于垃圾箱。何为腐朽?何为神奇?有之为利,无之为用。将世俗之物,化为非凡之美,方为创造无穷之道。
“蛋也是有性子的。”她说。每个蛋壳上要穿针千百次,若次次都按预定的图案,精打细算、分毫不差的话,结果往往是蛋破图毁的下场。“这就得发扬包容精神喽,遇到特别硬的地方,就要换地下针。除了绣彩蛋,赵老师还精通彩蛋绘制,并在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小蛋壳,大世界。这几年,赵伟作为文化使者随国家和北京市的代表团先后到泰国、俄罗斯、阿尔巴尼亚、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地展示彩蛋作品,传播中国非遗文化。这小小的蛋壳,已经成为了宣传大使,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那极具创造力的优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