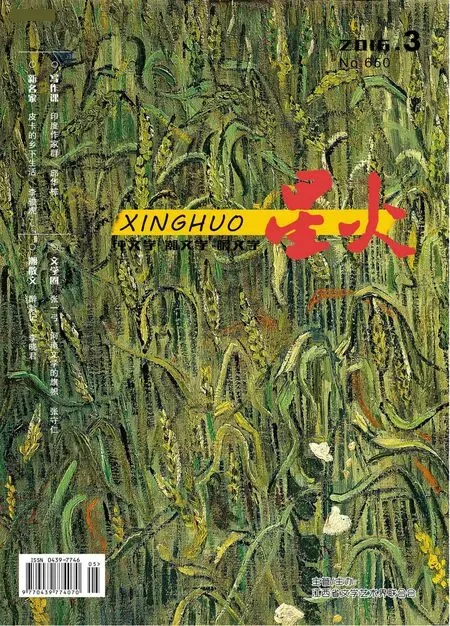逃 离
2019-07-17谢志强
○谢志强
一
在一个深秋的上午,我被分泌过剩的忧愁困扰,想去往一个空寂的地方透透气。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几乎不假思索地步入家后面的那个山谷,那个可以让我暂时忘却一切烦忧的所在。
深秋的山谷里,密密麻麻地开着大片大片野菊花,这些小巧的花朵,金黄金黄的,随意蔓生在路旁。两侧山坡上生长着大片粗壮的松树,也夹杂着少量低矮的落叶灌木,它们的叶片大多成了橘黄色,零零星星的橘黄色闪烁在松林之间,像是一篇文章里零星分布着的标点符号。
当我即将走到山谷的尽头,一块熟悉的澄澈水面缓缓出现在眼前,这是一口早已废弃了的山塘。由于塘底多为岩石,极少淤泥,即使无
当那口山塘完全显露她的轮廓,我突然发现里面竟然游弋着一只大鸟。我的忧愁随即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些许兴奋。
我慌里慌张地掏出手机,试图捕捉住这只大鸟的优美姿容。可它似乎有些害羞,抑或是戒备,总是撅着屁股背对着我。我好不容易才拍到一张它的侧颜,拍出来的画面却不够清晰,也许是距离有十余米,手机的像素也很一般。
通过这张照片,我大致推测,这只大鸟属于某种鹅类,甚至也有可能是某种雁类。
我站立在离它最近的一块岩石上,努力调整自己的眼球,想以最佳的视角仔仔细细把这只鸟的外观辨认清楚。可是,我的视力已大不如前,面对眼前的这个目标,再怎么努力,看到的也仅仅是一个略微模糊的样子,它身上的很多细节都无法捕捉到。此前,我并没有在现实中观看过天鹅或者大雁,从小到大,家养的鹅也几乎没有接触过。对于上述鸟类,我的脑海里只存有一个大概的形象。其中,天鹅的图像我见得多一些,它们有修长的脖颈,雪白或者深黑色的羽毛,气质优雅高贵。而眼前这只大鸟,体型与天鹅有几分相似,可脖子并没有天鹅那么修长,羽毛则是灰白相间的,并不是纯白或者纯黑。这只大鸟虽不及图像上的天鹅那般漂亮,可依然有一种不俗的美吸引着我。
从这口山塘往北三四百公里,就到了候鸟天堂鄱阳湖。每年秋冬季节,会有大批珍禽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前往那里过冬,其中就包括天鹅和大雁。也许,有一部分天鹅或者大雁向往更加温暖潮湿的南方,在往更南的栖息地飞行途中,个别队员体力不支,落单后停留在这一片小小的水域,也不无可能。
我用手机搜索了一通资料,也没搜出一个结果来。因为没有近距离观察,我还是不能够判断它到底属于何方神圣。我存着一些疑惑又与这只鸟对峙了一会儿,随后便生出一丝忧虑来。如果它被别人发现了,如果那个人对它怀有叵测的居心,那么它将命不久矣。我有想过向一位从事过候鸟保护工作的朋友求援,可是照片不甚清晰,而他远在外省,不可能为了这只来路不明的鸟大老远跑过来,况且我不得不在下午离开这里,去往一百多公里外的赣州城上班。
我捡起山塘边的石子,向它旁边的水面砸过去,一个接着一个石子在水面砸出一朵朵水花,一圈又一圈涟漪荡漾在这片原本平静的水面。可它似乎并不在意,没有动身展翅高飞的意思,一会游到这边,一会儿游到那边,始终与我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像是在跟我玩游戏。我又装出狰狞的表情来,发出一阵阵急促而尖利的恐吓声,试图将它驱离这里,它依然如故。
我多么希望它能马上飞起来,飞向更高更远的天空,飞向那人迹罕至的荒野,逃离这个人类居民区附近的山谷,逃离可能出现的灾祸。可是,任凭我累得气喘吁吁,它还是贴着水面优哉游哉地缓缓游移着。
折腾了十多分钟,无可奈何,我终究还是放弃了,带着遗憾走出这个山谷,回到不远处的家里。下午两点,我坐上了开往赣州的大巴,远离这个山谷,远离这只不知底细的笨鸟。惟愿上帝保佑它。
二
两年前,我们家从县城中心城区搬到了这个城郊的村子。这个村子与县城的东城区仅一山之隔,兼顾了乡村的风景和城镇的便利。我们一家从此过上了开窗可见青山、田畴,聆听松涛、鸟鸣的乡村生活,告别了城区那个拥挤、逼仄而有些压抑的老房子。
时间往前倒退十余年,父母把年幼的我寄养在二伯父家,背上行囊远赴广东深圳打工。打工五六年后,他们用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血汗钱在县城买下一套两居室的二手房。我们这个三口之家便从那个叫做椒坑的小山村搬进了县城居住,过上了村里人艳羡的城镇生活,父母从此逃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而那个承载着童年时代笑声和泪水的地方,永远成为我回不去的精神原乡。
在县城居住的日子里,每当我在他们面前表露出对于乡村生活的怀念时,他们往往会严肃地呵斥我,并以自己在农事上的种种辛苦来举例教育我,试图以此来打消我对农村生活的留恋。
在我快要大学毕业的那年,父母为了寻求一个更为宽敞舒适的居住环境,几经挑选,在城郊一个叫丁家陂的村子买下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新房子。
他们终究还是喜欢乡村的,即便脱离田地十余年,农民身上所具备的某些品质依然顽强地烙印在他们身上,就像人的胎记一样,将伴随一生。
住到这个村子之后,母亲在工作之余,会带着新买的镰刀和锄头,到新家后面的一个山谷里开荒种菜。经过一两年披荆斩棘,母亲在这个山谷里已经占有五六处菜地,家里一年四季基本不用花钱买菜,自家种的绿色无公害蔬菜吃不完还能送人。
在这几处菜地中,最晚开垦、离家最远的,在山谷尽头一个废弃山塘边。这里原先杂草丛生,荆棘遍布,经过母亲近一周的辛苦劳作,以一双手的血泡换来一块长条形的旱地,母亲在这块田地上种上了豆薯和番薯。到豆薯成熟的时节,我一回到家里就会跑到山塘边,亲手从土壤中挖掘出一两颗新鲜的豆薯,扯着豆薯藤,把豆薯往山塘里滚几下,洗净表皮上的泥土,揭开黄褐色的表皮,享受甘甜的豆薯肉。
即使不为口腹之欲,我每次从赣州回到家里,也喜欢跑到这口山塘边来,就算一个人在附近发发呆,吹吹山风也是一件相当快活的事情。
我最喜欢晚春时节的山塘,它会比之前变得更大,更加饱满,就像蓄积着一池勃勃向上的能量。这些能量释放出来,让附近的草木都铆足了劲,肆意地生长。这时的山塘边,红的杜鹃花开了,白的金樱子花开了,黄的过路黄开了,各种花开了,热热闹闹的。鸟雀忙着求偶,蜂蝶忙着采蜜,只我一人忙里偷闲,把手伸进山塘里,逗弄水里的小鱼小虾,或者恶作剧般把水泼到空中,观察滞留于空中的水,变成大大小小晶莹剔透的水球落入塘中。
很多时候,这个山谷是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我享受着与世隔绝般的宁寂,会情不自禁遥想此地在太古时的景象。在那个时候,这里或许生活着犀牛、大象以及羽毛艳丽的鹦鹉。
三
时隔半个多月,我又一次从赣州城返回县城东郊的家。刚放下行囊,便从母亲那里得知两个坏消息。那只被我拍摄下一张侧影的大鸟,被父亲伙同几个邻居抓获,并成为了他们的下酒菜。母亲告诉我,那是一只来路不明的家鹅,由于无人认领,被父亲他们宰杀后拿到饭馆里做成下酒菜吃了;他们原本想拿到家里让母亲烹调的,她以怕被失主找上门来为由拒绝了。第二个坏消息便是那个山谷附近的区域被开发商买走了,包括那口山塘和山塘边的菜地,他们打算把那里夷为平地,建起一栋栋楼房。母亲在说这则消息时脸上写满了无奈和悲伤,她心疼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菜地。
当我怀着复杂的情绪走入那个山谷,首先迎接我的是一阵阵刺耳声响,嚓嚓嚓嚓嚓,轰隆轰隆轰隆,我分明听见大地在痛苦地呻吟。
在山谷尽头的一处山体上,挖掘机和开山钻石的机械正以其拥有的强大动能,揭开山的皮肉,敲碎山的骨骼;一辆辆小货车繁忙地运转着,不知它们要把这座可怜的山移到何处。
山塘里的水已不再清澈,浑浊的水面倒映着残缺的山体,水面上一大片红褐色的区域像极了大地裸露着带血的伤口。
我拿出手机,找到那张半个多月前拍摄下的照片——在一大片苍翠的松林下面,一只灰白色的家鹅侧身浮游在一片澄澈而平静的水面上,宛如一只遗留在人世间的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