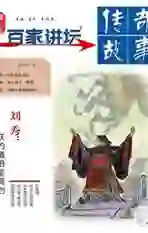不予良辰
2019-07-16薛浅
薛浅
今年的春日来得极早,程昇在京师耽搁久些,自从回到戎城,就不停地给易卿卿赔罪。其实易卿卿并不在意,偏他内疚得不行,偷偷找了数十家戏班,单拣那些欢喜的戏唱,只求逗她一笑。
台上传来咿咿呀呀的戏腔,易卿卿裹着狐裘,端坐在檀木椅上,也未细听,只是痴痴地盯着那翻飞的傀儡,想起初遇许安平那年,他唱的也是这场戏。她缓缓笑了起来,笑得无比凄凉。
记得那日,她就站在听雨楼的堂内,怯怯地倚着鸨母,瞧着台上的傀儡,惊奇不已。鸨母说,许安平是戎城傀儡戏的第七代传人,妙音绕梁,就连梨园的老先生都曾盛赞过,她若能随他学几出戏,日后必能一举夺魁。
她虽无夺魁之心,却真的很喜欢唱曲,听到他的婉拒时,难过地低下了头。正欲离去时,他偏又收下了她。后来,她问过许安平很多次,为何独留下她。他只是淡淡一笑,无论如何都不肯说。
听雨楼每月不过几场戏,日子过得很拮据,清粥野菜,自然无法与吹笙阁相比,然而她不曾抱怨,日日狼吞虎咽,仿佛吃的是世間珍馐。每到听雨楼开戏时,她就帮忙倒茶,然后站在远处的角落里,看着戏台上的傀儡行云流水般的动作,听许安平用婉转的戏腔道尽平生。
许氏素有不收外徒的家规,所以许安平不许易卿卿称他“师父”,也不许易卿卿碰他的傀儡,只是教她唱曲。他平日待她极好,独在戏上万分严苛,若错了半句,戒尺便毫不留情地落在她的掌心,等她唱好这支曲子,许安平才心疼地为她抹药。
直到两年后,易卿卿唱曲已是炉火纯青,许安平才将戒尺收了起来。
惊蛰这日,易卿卿正在抄写曲谱,看到许安平走过来,连忙捂住了字。他皱着眉掰开她的手,看到她的字后,那难以言述的表情,仿佛眼睛都受到了侮辱。察觉到她的窘迫,许安平没再说什么,绕到她的身后,握住了她的手。
温热的气息洒在耳垂上,她觉得脸都烧了起来,再无暇顾及他说的书法要领,感受着他掌心的温度,思绪早已飘远。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她终于明白了自己心意。
易卿卿学成归去的那晚,许安平饮了许多酒,脸色潮红地坐在听雨楼楼顶,陪着易卿卿看戎城夜景。 “安平,你以我的模样做个傀儡好不好?”许安平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道: “我的傀儡可是要给未来娘子的,你还要吗?”
“安平若是偏要给我,那我不要岂不是伤了安平的心。”易卿卿的脸上满是笑意,才略带调皮地说完,就被许安平搂在怀里。她羞涩地闭上眼,他的唇便落了下来。那是他们的第一个吻,也是此生最后一个。
“安平,不如我们私奔吧?”看到眉头紧皱的许安平,易卿卿突然笑了出来,“我逗你的。”说罢便转过头去看万家灯火,好似方才真的只是开了一个玩笑。
16岁那年,易卿卿回了吹笙阁,因唱许安平所作的《叹良辰》,成了新晋花魁,一时风头无两。如此绝色美人,卖艺不卖身都成了妄想,鸨母虽疼易卿卿,却迫于程异的淫威,默许了他,芙蓉帐暖,一夜春宵。
她走的那日.许安平曾送给她一只信鸽。他说,若是不开心了,便写信给他,他一定会去看她。她想见他,却又不忍让他破费,直到程舁之事,她将一腔委屈述诸笔端,等到写好后,纸都被泪打湿了。可惜等了一日又一日,许安平都杳无音讯。
后来,易卿卿每日都会写一封信,从泪眼婆娑地诉说委屈到追忆往事。许安平一定没看到这些信,否则为何不来看她呢?
半个月后,易卿卿终于寻到机会,收拾了细软,从吹笙阁逃了出去,因跑得太急扭伤了脚,她只好一瘸一拐地走到听雨楼,最终在听雨楼楼顶找到了许安平。
“安平,带我走好不好?”易卿卿费力地爬到楼顶,看到散落在他身旁的信,强压下心中的委屈,低声乞求道。许安平眸光微暗,坐在那里沉默不语。她突然红了眼,“安平,你不是说好来看我的吗?”
“卿卿,我去了又能怎样昵?”许安平对她苦涩一笑,便又低下了头。他幼时曾勤学苦读,本欲考取功名,却因许氏一脉单传,被父亲逼着入了下九流。程异乃戎城首富,便是在京师中也颇有人脉,若得罪了程异,那戎城傀儡戏岂不是毁于他手。“卿卿,等我赚好多好多钱,赎你出吹笙阁,好不好?”
“许安平,难道你要我等你一辈子吗?带我走吧,去哪儿都好。”易卿卿满眼是泪地站在楼顶,看着许安平沉默地坐在那里,直到淅淅沥沥的小雨将一袭春衫打透,最终踉踉跄跄地下了楼。
那一夜,她不记得是如何回的吹笙阁。冰凉的雨打在身上,无数次跌倒在水洼里,然后带着满身的污泥爬起来。回到吹笙阁后,她便生了一场大病,等到痊愈时,嗓子已经毁了,她与许安平的最后一丝牵扯也仿佛断了。
她依旧写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她想,只要他肯来带她走,她就不怪他了,可惜他从不曾来过。
程昇浪迹欢场多年,身旁的女子更是不计其数,故而易卿卿毁了嗓子后,不知有多少人等着看她的笑话。谁料程异却仿佛动了真心,不仅为她请了最好的大夫,还时常守在她床边嘘寒问暖。绫罗绸缎、胭脂水粉,更是一箱一箱地送。
旁人都道易卿卿好福气,只有她冷眼旁观,很少与程异说话,更从不曾对他笑过,程异也不勉强。他曾经亏欠过一个人,如今只能将这些温柔都给这位与她眉眼相似的姑娘了。
第二年初春,程异下聘,强娶易卿卿为平妻。花魁高嫁,整个吹笙阁都透着喜气。鸨母笑着清点聘礼时,易卿卿漠然地坐在楼梯上,看到许安平抱着一个木匣走了进来。一年不见,他的下巴上有了很多胡茬,眼神也是疲惫不堪, “这是我的贺礼。”
“多谢许先生。”易卿卿脸上挂着笑,接过他手中的木匣,随手递给身后的鸨母,再不肯多看一眼。许安平静静地瞧了她许久,然后转身出了吹笙阁。
易卿卿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她出嫁那日,许安平躲在吹笙阁旁的垂柳后,哭得像个孩子。他一直都记 得,父亲跪在他面前声泪俱下地求他将戎城傀儡戏传下去的样子,就连弥留之际都还死死抓着他的手,直到他拿起身旁的傀儡,才肯闭上眼睛。
他也不想啊,可他又能怎样呢。那年,他之所以会留下易卿卿,就是因为看到了她眼里的难过,让他想起自己被迫放弃诗书时的苦。他本想在揭开她盖头的那一刻,才将那个似她模样的傀儡送给她,如今却是不能了。
这一年,17岁的易卿卿嫁给了26岁的程异,明媒正娶,十里红装,不知羡煞了多少人。只有易卿卿知道自己心里有多难过。
“谢老爷、夫人打赏。”听到许安平的道谢,易卿卿才回过神来,一身红衣的他正对着席间作揖,身旁还站了个孩子,正怯生生地打量着她。听说许安平娶了个盲妻,有了儿子,想必就是这个孩子吧。
程昇见易卿卿眼圈通红,忙道: “卿卿,那年我就说了,以后的春日都有我陪你,我断然不会再爽约了。”程异郑重地举着左手起誓,看到易卿卿点了点头,笑着将她搂在怀里,回了内室。许安平将赏钱都放到许行手中,随着同行们出了程府。
他听说,易卿卿怀过一个孩子,只是深宅大院里有太多见不得光的事,不过才三个月,就流掉了,自此伤了身子,再不曾有孕。
他还听说,程异年少时寻花问柳,处处留情,但自从娶了易卿卿之后,除了过年时回京与原配、独子团聚,便极少在外留宿了。
自那日别后,纵然浮生漫漫,他的人生想再与她相关,也都只有“听说”了。
“爹爹,明明是一场欢喜的戏,为什么程夫人却哭了啊?”许行跟在许安平身后,不解地问道。“许是想起故人了。”许行还想再问,却看到许安平眼里有了湿意,便没敢开口。
许安平常常在想,许氏一族最初唱傀儡戏时,必是出于喜欢,只可惜累世经年,到他时却已成了负担。如今他收了众多弟子,若是有朝一日,许行有了所喜之事、若爱之人,他定顺从其心意,许行再不必似他那般,为许家所累了。
转眼已过数十载,多少爱恨都随风而逝了。只可惜那一年,春寒料峭,细雨如丝的深夜,他终究辜负了深爱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