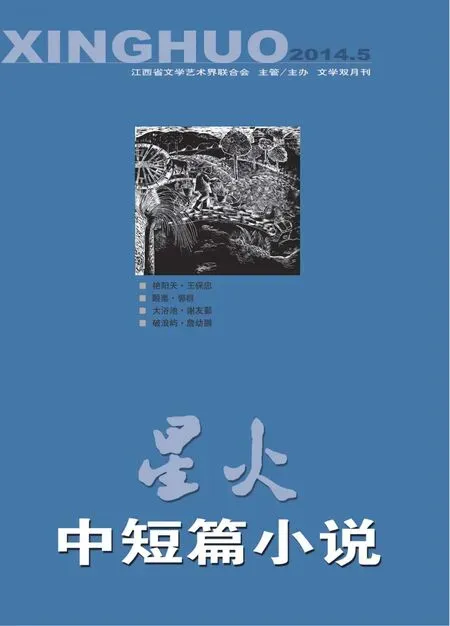眺 望
2019-07-16○言子
○言 子
吃罢午饭(一碗面条),她在雨声里小睡,醒来。雨还在下,她拉开床背后的半幅窗帘,翻开一本读了多日的书,听着雨声,进入博尔赫斯的世界。书是1996年冬天买的,三本,小说卷已经被她翻烂,内页一叠叠脱落。她想,装订不过关的缘故!1996年,她还年轻,不到三十五岁,这个年龄,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但是,生命和年华不成正比,她的日子艰难,皱皱巴巴。一个下岗的单亲母亲,无依无靠,日夜为生存犯愁、奔波,怎么会活得滋润!1996年,她只是慕名想读博尔赫斯,对于博尔赫斯建构的文学世界,似懂非懂。似懂非懂,她还是喜欢,隔上一年两年,要拿出来重温。一起重温的,还有卡夫卡的小说,这两个创建了不同文学世界的作家,细雨一般滋润着她贫瘠的生命。那是她阴霾日子里的阳光雨露!绝望中的微火!
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喜爱博尔赫斯和卡夫卡。
现实千疮百孔,喧嚣浑浊,博尔赫斯和卡夫卡建构的世界,远离生活,只在文学世界里发生。她看见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文学世界,又看见现实里的每一个人都存在于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每一个人有可能都是圆形废墟里那个做梦者,曲径分岔花园里的一个影子,穴居的永生者。同时,每一个人又可能都是到不了城堡的土地测量员K,是莫名其妙受审判的约瑟夫·K,是某天早晨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她的文学审美随着年龄发生着变化,讨厌那些复制生活的所谓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也应该有别于生活,作家应该在文学作品里创建一个不同于现实生活的世界,博尔赫斯和卡夫卡即是。雨声里,她读完了博尔赫斯的三个短篇小说。这部小说卷,去年春天她才读过,自1996年的冬天以来,她记不得自己读过多少遍了,书页翻脱,每次重读,每一篇小说都像从来没读过一样。都似第一次阅读。这样的感受存在于她常读常温的每一本(个)经典小说(作家)。常读常新就是这样罢?她想。她的梦想,就是做一个穴居人,远离世俗,以思考和做梦为生。
—那座建筑是永生者屈尊俯就的最后一个象征;标志着永生者认为一切努力均属徒劳,决定生活在思考和纯理论研究的一个阶段。他们建立了城市,把它抛在脑后,然后去住在洞穴里。他们冥思苦想,几乎不理会物质世界的存在(《永生》第四节第一段第七行)。
用半生时间读懂一个作家,她想,够漫长的。
第四篇小说读了不到三行,淅淅沥沥的雨声不再敲击雨棚。她望了望窗外,灰色时空里没有雨丝,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停了。她看了看手机,下午5点15分。雨是昨日天亮前开始下的,伴着大风,时急时缓,时密时疏。她放下书,穿衣上楼。经验告诉她,风雨过后,天空不同于往日。
窗外的天空,大多时候同她的日子一样灰蒙蒙白茫茫,雨后的天空,将呈现另一种色调。
她上完楼梯,跨出进入楼顶的木门,一脚踩在水淋淋的水泥地上,迈步向东,望见天地像一张黑白照片,城市像一张黑白照片。她喜欢这种色调,不是单调的灰色,也不是单调的白色,城市上空的云层,汹涌着堆积着,黑的灰的白的。弥漫成一个丰富的世界,气象万千。天地是一张黑白照片,城市是一张黑白照片,像她刚放下的书上的黑白封面,博尔赫斯的半张脸,在黑白时光里沉思,光洁的额头如白昼,挺拔的鼻梁如黄昏,发白的头发和眉毛,如秋霜,被幽暗笼罩的隐隐约约的脸颊耳朵下巴嘴唇,如黑夜。她想,博尔赫斯也许就躲在某块云层里,躲在幽幽时光后面。下午5点15分,雨后,她站在高楼上,看到了一个黑白世界,看到了被云层笼罩的黑白城市。看到了,博尔赫斯的世界。那是白天和黑夜,是正在流逝的时光。
她的目光,由近及远,越过河谷横坐竖立的楼房,抵达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些年,她看见的太阳,都是从楼房升起,日出离她远去,青山离她远去。楼房背后的东山,曾经在她远眺的时候郁郁苍苍,太阳从松林上升起,这样的早晨不再出现。河谷是安昌河谷、涪江河谷,越来越高的楼房把两条河谷连成一个整体,无限制地向着流水之上,向着流水之下,向着两岸的坡地延伸。她的目光环顾左右,云起云涌的天空下,只有一种颜色——灰色。天地是一张黑白照片,云海奔涌的天空,此时,离她很近,地上的建筑物,离天很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她想起这首南北朝的蒙古民歌,头上的天空真似穹庐,笼盖的不是四野,是望不到尽头的城市,此时天也苍苍,大地灰茫茫,没有牛羊。以前,她看得见的四周苍山,被层层叠叠的楼房遮蔽。雨后的世界一片寂静,仿佛只有她独自站立天地之间,观赏云天上的万千气象。
真是万千气象啊!
东边的云乳白色,像开锅的牛奶,向着她沸腾;东南的云黛色,像一座座山丘,点缀的白云,似怒放的云花;东北的云乌黑,像一盆盆泼洒的墨汁,流淌着,浸染着,在参差的楼房上铺展。坡上的三竿吊塔,在烂尾楼上看了六七年的云天,还在原处,被墨云染黑。城市是一张黑白照片,天地是一张黑白照片,绵实的云彩,从天边升起,向着四周汹涌、滚动,天空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灰色,单薄的天空丰富起来,厚重起来,层次分明。那些在她的眼里看似静止的黑黑白白的云层,分分秒秒都在变化着流动着,此消彼长,一如人的生命。她的双眼看不见云的变动、流逝,犹如她看不见一个人生命的变动、流逝。看似无变化的生命,如天上的云一样,分分秒秒都在变化着,流逝着。这么多年,她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怎样变化、流逝的,但它,年年月月,日日夜夜,都在变化、流逝。
变幻莫测的云天,一如变幻莫测的生命。
她的目光离开吊塔,从北至南,缓缓移动。
东边的一锅牛奶下,有条涪江。这条从王朗雪山流下来的碧色的江,两年前,逆流而上,她看见深谷里奔涌的江水碧蓝碧蓝;这两年逆流而上,江水不再奔涌,也无碧色,南坝库区波平浪静的水面上,深秋路过,她看见水上是漂浮的垃圾,那条在深山峡谷流淌着碧色的江水消失。她想,龟山下涪江东岸那座依崖而建,唐朝名“水阁院”,宋代为“碧水寺”的古寺,应该是来自涪江的色彩吧?唐宋的涪江,流到绵州的龟山颜色未变,不像几年前,深山峡谷才见碧色。而今,逆流至平武,涪江都不见碧色,大大小小的水闸让涪江流动不起来。东南边的团团云花下,是安昌河,王子大酒店和万达的摩天大厦遮蔽着一条形如彩虹的大桥——飞云大桥。前些年她在南窗,看得见飞云大桥的,现在站在楼顶,看不见了。
她记得某个初冬的夜晚,放下写作中的一部长篇小说,夜幕中,她顺流水跨过御营大桥,逆河至飞云大桥。那时河对岸寂静,尤其夜晚,难见人迹。她在寒风里踽踽独行,一路荒芜,心里充满恐惧,担心出现意外。开始是不慌不忙,后来是疾走,黑漆漆的河道上没有一个人影。踏上飞云大桥,她放慢脚步,悬吊吊的心有了着落。飞云大桥灯火辉煌,卧在水上的拱桥真像彩虹。一路逆河走来,上桥,她没有遇见一个人。让她踏实下来的不是大桥上的灯光,是天边一轮正在升起的红月亮。那时城市建筑还没有占据两河河谷,市中心的建筑也不高大,走到大桥中央,她侧头,目光越过黑夜里的灯火和建筑,望见了天边的红月亮。她停步,伫立扶栏边,面向茫茫夜色,眺望远天的红月亮,不禁泪光闪烁。桥上无人,偶尔有一辆货车飞驰而过。她想,这个冬夜,没有人像她一样在寂静的黑夜,在荒凉的河道上独行,没有人像她一样在一座无人的大桥上眺望红月亮。此时,有没有人看见红月亮从天边升起?有没有人看见黑暗里升起的红月亮泪光闪烁?她一再问自己。没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在一个荒凉地带独行,没有人像我一样在黑夜独自眺望红月亮,这黑夜,黑夜里的红月亮,属于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在今夜,在此时,在安昌河的飞云大桥上看见了红月亮,她对自己说。寒风吹着茫茫夜色,整个夜空,整轮红月亮,整条河流,都属于她。她对红月亮说,我们又相遇了!她和红月亮对望着,一个在天边,一个在流水上;一个要竭尽全力从暗夜升起,一个要在荒凉地带找寻绿荫。没有人看见红月亮是怎么冲破黑暗,艰难地从寂静中升起!她望见了红月亮的艰辛和寂寞。她想,红月亮也看见了她的艰辛和寂寞,看见了她一路荒凉,无依无靠,独自在暗夜在寂静里跋涉。自她与红月亮初遇的那个夜晚,时光像桥下的流水一样流逝了许多年,她仍一个人在荒凉地带踽踽独行。身边一些努力钻营的投机者,借助权力,借助自己制造的种种名目改变了身份和地位,她却一如既往踽踽独行,年复一年走在荒凉地带,独自在无人迹的暗夜眺望一轮红月亮。逆河走来,她没想到会在流水上与红月亮相遇,会看见一轮红月亮从天边升起。
这一生,她只想在寂静地带眺望红月亮。
只想,在夜色下独自做梦,就像圆形废墟里的那个做梦人。
她记不得自己与红月亮相遇多少次了。前些年,她和它,在寂静夜晚,常常相遇,常常对望。这些年,城市的建筑年年增高,坡脚几家国营企业变成房地产商的地盘,一幢幢高楼耸立天空,她看不见红月亮了,红月亮也看不见她了。
红月亮是她做的一个梦?她是红月亮的一个梦?或许,他们是彼此的梦境。心心相印。彼此温暖。
她转身向西,边走边想,谁是谁的梦?或许,天地都是一个梦境,城市连同此时的她,都是一个梦境。
此时,雨后的天空,就是一个梦境。一夜两天的雨水将天空虚幻成一个海洋,层层叠叠、铺天盖地的云团如海水般覆盖整个天空。波涛奔涌的汪洋大海,笼罩着灰蒙蒙的城市,城市在一片汪洋之下。天空不再是天空,是虚幻的海洋。她在汪洋下眺望、行走。大海不是清一色的蓝色,她见过夜色一样的海水。天上黑的白的灰的以及黛色的云层云团云花云线,真如大海一般。各种各样的云气象万千,把平日单调的天空虚幻成波涛汹涌的海洋。
她望见了海岸线。
刚才,楼宇之上,天际的海岸线如潮水一般绵延,后浪推前浪。流云虚幻出来的海岸线,谁说不是真实的?此时,如果她站在海边,天上的海岸线和地上的海岸线,哪个更真实?自她离开家乡,来到这座城市,三十多年,一切都不是从前。从前的河谷只存在于她的记忆,从前的家乡也只存在于她的记忆。记忆里的世界和天上的世界,哪个更真实?记忆里真实存在过的一切已经消亡,就像一个梦一样,留在记忆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会模糊,也许会由记忆生发更多的细节。
天上的海洋和地上的城市,哪个更真实?她望着天边终将会消散的海岸线想。
那座她的目光躲不开的水塔,矗立在前方的山坡上,与她站立的楼房在一条线上。一个在何家山的那边,一个在何家山的这边,隔着早已不存在的粮机厂上空的树林,直线距离,几分钟可到达塔下。她的人生没有捷径,也不借助外力为自己铺一条捷径。一个独行者,一个卑微、与世无争的独行者,爬坡上坎,弯弯曲曲可以走到水塔下。此时,她站在何家山六层楼顶上,与不远处的水塔对望,她借助何家山,借助坡上的六层楼房,得以同水塔对望,同水塔四周的天空,同城市缝里的天边对望。矗立何家山的水塔,是旧时光里的一件遗物,一件老古董,它一成不变,自她看见它那日起,独立于山坡上,粮机厂消亡,它还独立云天下,一成不变。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像一个梦。水塔是大地造的一个梦,它的梦境直通天宫。她想,她和水塔都是借助山坡眺望天空和河谷,正如有的人借助外力掠夺名利。这些人,只不过是山坡上的一棵小树,看似高高在上,实质矮小。她敬重那些凭借自身的力量和强大,在谷底成为一棵大树的耕耘者,他们历尽风风雨雨,独立于世。
那些年,水塔是山坡上的庞然大物,是河谷的庞然大物,没有哪个建筑物可以与它相提并论。它借助山坡,高不可攀,河谷及坡上的建筑,都在它的俯视之下。这些年,连河谷的建筑都要俯视它了,不要说坡上的建筑。树林下低矮、破败的棚户,哪天被开发商开发,高不可攀的水塔终将会被楼层湮没,那片掩映曾经是一个国营企业家属区的香樟林,也会被机械吃掉。无用的水塔,随着工厂的倒闭,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开发商还来不及顾及它,他们正在河谷公路边的废墟上建造商品房——那个曾经叫粮机厂的厂址上,两座顶天立地的电梯大楼已经竣工、出售,另外几座还在装修。那棵弯曲的松还在,芭蕉和墙柱上的牌子不知去向——河谷的房子建好,就该轮到坡上了,香樟林和水塔,它们的命运同大门口那棵芭蕉,那块牌子一样,终将被毁灭,不留一丝痕迹。早晚的事,有那么一天,她上楼,转身向西,云天下的水塔消失,香樟林消失。她拍下了不同时间段的水塔,水塔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出不一样的背景——西天的背景。她酷爱黄昏的背景,夕阳映照下的水塔,橘黄,水塔背后的西天,是一幅金碧辉煌的油画,云彩幻化的大地山川湖泊让她着迷,尤其是那条由霞光组成的弯弯曲曲的天路,灯火明亮。这种日子一般在夏天,7点25分,太阳在水塔背后,金光灿烂,即将沉落。她站立天空下,眺望夕阳沉落,眺望天边的晚霞流逝。水塔在沉落的夕阳下,褪去橘黄,一身暗淡。夜幕降临,天地被黑暗笼罩。更多日子,水塔背后的西天灰茫茫,水塔也灰茫茫,她知道,灰茫茫背后,苍山绵延。
乱云飞渡的天空下,水塔是暗黑色,水塔的背景,下边灰白色,上边暗黑色。乱云飞渡的日子可遇不可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气象万千的天空下眺望乱云飞渡,眺望黑白城市,眺望被一张云幕覆盖的水塔。她用相机,留下了这样的时刻。乱云飞渡下的城市、吊塔、水塔,天际浪涛滚滚的海岸线,她都留下了。流云如生命,变幻莫测,转瞬即逝,今日看到的云彩跟昨日不一样,昨日看到的云霞形成的西天景色,跟明日不一样。没有一片相同的云,也没有一片相同的霞。而今,大地都是一天一个样,何况天上的流云。
乱云飞渡。
气象万千。
她的目光由西至北,碰撞建筑物上。
一对斑鸠,栖息楼角生锈的路灯杆上。它们安静地待在高空,与天地城市楼房融为一体,孤零零的。这对斑鸠从哪里飞来的?她举起相机时想,将取景框对准斑鸠和路灯。镜框里,是一张黑白画面,路灯和斑鸠在茫茫天幕上,通往天幕的河谷上,高高低低的楼房灰茫茫。镜框躲不开一根钢丝绳,它紧靠路灯,斜插大地,将路灯和斑鸠分割。没有那根绳子,画面干净,她想。这些年拍照,总是躲不开这样那样的建筑物,躲不开这样那样的线绳。各种各样捆绑的线网将各种语言各种声音连接起来,人与人之间,却是隔离的,陌生的,像镜框里的线绳,分割着完美的画面。拍第二张,她看见取景框里只有一只斑鸠。按下快门时,她想,另一只斑鸠什么时候飞走的?举起相机时还在,转眼间,镜框里只有一只斑鸠。两张照片相隔一分钟,第一张是一对斑鸠,第二张里是一只斑鸠。第一张里的两只斑鸠,向西,第二张的一只斑鸠,向东。相隔一分钟,镜框里的画面发生变化。她没有看到另一只斑鸠是怎么飞走的。她想,它们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的相机,看见了我在拍它们,那只飞走的斑鸠,以为镜头是枪口。这种情况,常常出现。留在路灯杆上的斑鸠看来比较有经验,知道镜头不是枪口,没有跟随那只飞走的斑鸠。它独立茫茫天幕下,孤零零。她看斑鸠,斑鸠有时也看她,隔着距离,站立茫茫天幕下,彼此看着。她想,我在斑鸠的眼里,也是孤零零的,是茫茫宇宙下的一只呆鸟。她以为只有她一个人站在湿淋淋的水泥房上看雨后的黑白天空和大地,原来还有一对鸟儿与她同看。现在,留下一只鸟儿与她同看。云幕低垂的茫茫天幕下,不要说一对鸟,一只鸟,一个人,就是一群鸟,一群人,看上去都是孤零零的。
那只斑鸠同她一样,不怕孤独。
先前是两只,一分钟后是一只,时间流逝得真快。
真的是转瞬即逝!
她不知道两只斑鸠是从哪里飞来的。云雾幻化的?一对斑鸠,一只斑鸠,都似一个梦境。路灯也是天幕下的一个梦境。天空和大地是一个梦境。她自己,也是一个梦境。
所见的已经流逝,此刻,黯淡的路灯杆上,什么也没有。
那只孤零零的斑鸠,什么时候飞走的?
她没看见它们什么时候飞来,也没看见它们什么时候飞走。之后飞走的那只,去云雾里追随另一只了?
她再次将目光转向西天,天际背后,她知道有众多绵延起伏的群山。此时,西天茫茫。
她想起《城堡》里的开头——真是经典的开头啊!——卡夫卡与K梦游到一个村子,这段经典的开头是这样的:
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亮光也看不见,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凝视了好一会儿。
此刻,她也像K一样,对着头上空洞虚无的天空,眺望着云雾笼罩的西天,望不见一星儿可以显示绵延群山的痕迹。但她知道,一脉脉群山起伏着,隐藏在天际背后,看得见看不见,那些群山,一直在西天绵延。
对于她来说,它们是一个遥远的梦。
是天空和大地共同创造的一个梦境。
她凝视灰茫茫的天际,想,说不定云遮雾绕的山顶上,有座她看不见的城堡。
她又想,不,不是城堡,是南山。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云遮雾绕的山顶上,有座茅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