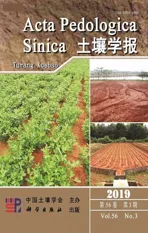植物残体向土壤有机质转化过程及其稳定机制的研究进展*
2019-07-13汪景宽徐英德高晓丹李双异孙良杰安婷婷裴久渤李张维俊
汪景宽 徐英德 丁 凡 高晓丹 李双异 孙良杰 安婷婷 裴久渤李 明 王 阳 张维俊 葛 壮
(沈阳农业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土肥资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沈阳 110866)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质量的核心,维系着土壤肥力、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关乎地球和人类生存发展的诸多要素。在全球尺度范围内,土壤生态系统有机质总含碳量高于大气和植被含碳量的总和[1]。土壤有机质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区域环境变化十分敏感,这个巨大碳库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平衡发生微小的波动都会对大气碳库产生显著的源汇效应影响[2]。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和稳定性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压力、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3],当前亟待解决的核心科学问题是正确认识并理解土壤有机质的形成、周转和稳定等关键过程及其影响机制。
植物残体是土壤有机质的主要初始来源,在土壤微生物的介导下,经由复杂的腐解过程转化为土壤有机质而稳定存在[4-6]。长期以来,土壤有机质和碳循环领域的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限于土壤体系的复杂性及研究手段的制约,目前对于土壤有机质的形成过程、赋存形态和稳定机理等问题仍然认知不足并存在分歧,例如经典的有机质形成理论——腐殖化过程便受到了一些新研究结果的质疑[7]。土壤有机质和微生物的时空分布均具有非常强的异质性,并受很多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8]。传统研究的精度很难去定量检测碳在植物—土壤—微生物之间和土壤不同有机组分之间的流动;土壤这种“黑箱”特质使大多数研究只能关注最终结果而忽略实际的有机质变化过程,尤其是微生物在其中的枢纽作用。此外,微生物在土壤有机质周转方面存在两方面的作用:通过分解代谢促进土壤有机质的降解,同时也能通过合成代谢将土壤中可利用碳源转化为更稳定的有机质[3]。但到目前为止,大量研究都集中在微生物对有机质分解矿化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到微生物代谢过程在土壤有机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9-10]。近年来,随着同位素示踪、分子生物学和先进的成像观测技术在土壤学领域的快速发展,使探明植物残体在土壤中转化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全面认识植物—土壤—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成为可能,这对于建立科学的农田管理制度、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碳截获潜力、实现土壤的可持续利用意义重大。
基于此,本文对近年来植物残体向土壤有机质转化这一关键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总结了传统腐殖化理论面临的新挑战,分析了植物残体向土壤有机质转化的微生物机制及其贡献,剖析了土壤有机质的几种稳定机制假说,最后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1 经典腐殖化理论的局限与新进展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土壤有机质的形成过程具有高度复杂性,因而对该过程的认知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在Kononova[11]利用酸、碱浸提的方法提取出土壤腐殖质后,腐殖质被看作是土壤有机碳的主要承载者,并且土壤学界逐渐形成了土壤有机质形成的经典腐殖化理论。该理论认为植物残体完成向土壤有机质的转化必须经过腐殖化过程——微生物合成的多酚、含氮物质、糖类物质和来自植物的木质素聚合转变成结构更复杂的高分子多聚物(腐殖质)。长期以来,腐殖质的概念及腐殖化理论已经在各种文献和教科书中广泛存在,被广大土壤科学工作者认可并沿用至今。然而,经典理论所定义的腐殖质具有非常强的复杂性和高度模糊性,传统的研究手段尚不足以对其建立较明确的“白箱”模型。
纵观腐殖质相关研究的历史,其局限性和争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7,12-14]:(1)提取方法还存在争议:提取腐殖质过程中加入的碱液会改变土壤的电离环境,使有机质氧化而改变了自身结构与化学组成[15],可能已不能客观代表土壤中真实存在的有机质。(2)提取不充分:土壤有机组分因与矿物质胶结在一起,单独分离土壤有机质的过程非常困难[7]。因此,利用能提取出的这部分腐殖质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代表整体难免会降低其可信度[14,16-17]。(3)腐殖质真实分子结构的困扰:明晰腐殖质的化学结构历来是腐殖质相关研究的难点。近年来,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方面的研究,但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得出较为详细的腐殖质分子结构信息。(4)腐殖质的形成过程不完全明确:不仅形成腐殖质的来源物质众说纷纭[18-19],而且微生物在腐殖化过程中的作用尚未形成统一观点,目前存在微生物合成学说、微生物多酚学说、厌氧发酵学说等多种理论假设,但在土壤中究竟何种有机化合物通过怎样的途径逐步转化为腐殖质尚无定论。
一直以来,这些质疑并没有得到完美的解释,并且没有任何独立的实验能直接证明腐殖质是土壤中单独存在的有机组分[7]。近年来,逐渐应用到土壤学领域的X-射线光谱显微镜等原位分析手段可以在土壤不受扰动状态下进行直接观测,识别出土壤中有机物形态特征及空间变异性[17]。基于该项技术,Lehmann等[17]在土壤微团聚体表面并未发现与化学浸提出的腐殖物质类似的富含芳香/羧酸盐化合物的特征,而识别出的土壤有机组分多是植物或微生物体碎片。此外,Myneni等[20]也利用光谱证据证明了碱性提取物中的有机物质是以较小化合物的组合形式存在。Kelleher和Simpson[12]则通过核磁共振分析得到分子混合模型,发现传统意义的土壤腐殖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微生物、植物分子聚合物以及它们的降解产物所组成的复杂混合物。通过这些研究可以初步推断,土壤有机质实际上可能是生物小分子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分子缔合物或不同大小有机碎片组成的混合物[7,21]。此外,Lehmann和Kleber[7]总结认为新的研究所定义的“有机质”(以小分子有机化合物为主)所表现出的特征同样能够完美解释碱液浸提“腐殖质”具有的性质(如颜色、分子量、芳香性和氮杂环数量等)。
在土壤腐殖质概念受到广泛争论的同时,其形成的腐殖化过程自然也受到了质疑。植物残体分解产生的小分子化合物再次形成大分子的腐殖质这一过程至今并未在自然土壤系统中被证实[7];且一些研究[22-23]表明土壤腐殖质也可以拥有较快的分解速率。基于土壤有机质研究的最新成果并综合植物残体腐解过程中的不同保护机制,Lehmann和Kleber[7]提出了土壤有机质连续体模型(Soil Continuum Model)的概念,即植物残体向土壤有机质的转化是从大的植物生物聚合物到小分子化合物的微生物逐级分解过程,因而土壤有机质的存在形式是从大的植物碎片到逐渐分解成的小分子化合物的连续体(图1)。在该模型中,外源有机物料在被微生物利用的过程中体积不断减小,热动力学梯度逐渐下降,而极性组分、可溶性组分和离子化组分相应增加。并且,随着分子复杂程度的逐渐下降,有机化合物更易于与矿物表面结合或进入团聚体内部而增加其稳定性。但也有研究认为尽管土壤微生物可将腐殖质完全或部分分解,与此同时也会产生新的腐殖质使有机质得以更新[18]。总之,传统的腐殖化理论和有机质连续体模型均承认动、植物碎片在输入土壤后,会先经过物理化学作用而破碎,进而通过胞外酶等降解成相对更小的组分。但在后续的过程中,有机质连续体模型更多的是基于原位光谱显微技术[12,17]所得到的证据进行考量,因此提出了与腐殖化过程不同的理论模型。

图1 腐殖化过程与土壤有机质连续体模型对比[7]Fig. 1 Comparison between humification process and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inuum model[7]
综上,虽然化学提取法存在很多不足,但该方法在很多学科领域中(例如农业、环境)已被广泛的采用,且通过该方法提取的腐殖质,在大量研究中均被认为是土壤有机质的实验代用品。因此,在没有足够且确凿的证据下,还不能否定腐殖质概念及腐殖化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应继续探索腐殖质的形成机理及组成特征,并尽可能排除人为的干扰,获得土壤真实状态下的“腐殖质”,或者通过室内培养微生物和添加碳源的方法获取更接近于土壤腐殖质的微生物产物[18];另一方面,还需利用先进的现代研究手段进一步探寻有关土壤有机质组成的实验证据,以揭示化学提取的有机物质仅仅是“碱性提取物”,还是真实存在的“腐殖质”(图2)。
2 植物源和微生物源有机质对土壤有机质的贡献
以往大部分研究均将植物源有机质看作是土壤有机质的主要贡献者:植物在生长—死亡的循环中不断以凋落物、根茬等形式进入土壤分解,并通过腐殖化作用和土壤胶体的吸附作用使这些植物源有机质贡献于土壤有机质[24]。土壤腐殖质中含有大量芳香环,与源自植物的木质素酚结构相似,这也是土壤有机质以植物来源为主的早期理论的依据[6]。此外,活体微生物生物量的库容较小(占土壤有机质的比例<5%)、周转速率较快,因此微生物源有机质对土壤有机质库的贡献常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10]。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活体微生物生物量并不能代表通过微生物周转而在土壤中积累的有机质总量[25];而微生物死亡残体在土壤中具有更长的周转时间,对有机质长期的固持和积累意义重大[26-32],是表征微生物源有机质对土壤有机质贡献更好的指标[30-34]。Simpson等[28]通过核磁共振分析了黑钙土及相应植被的化学结构,发现土壤有机质中微生物来源的化学基团(protein/peptide)的贡献达到了50%以上。该研究所应用的13C核磁共振技术可直接测定有机质中的官能团组成,避免了化学试剂对有机质结构的干扰,测定结果更接近土壤有机质的真实存在状态[35-36]。此外,Liang等[33]利用吸收马尔科夫链(Absorbing Markov Chain)首次模拟并估算出微生物源有机质贡献的相对比例;结果显示,土壤中微生物死亡残体有机碳量是活体有机碳量的四十倍。此后,Miltner等[30]利用扫描电镜技术发现土壤矿物表面多是200~500 nm的有机拼接碎片(破碎的细胞壁),这为微生物以残体形式在土壤矿物表面直接沉积并贡献于土壤有机质这一假设提供了直接证据。以上研究表明微生物来源的这部分有机质在土壤中逐渐累积的作用效果不容忽视。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微生物标识物这一新的研究手段被用来探讨微生物残留物在土壤中的累积情况(图2)。越来越多的研究通过微生物标识物技术认识到微生物残体对土壤有机质库的重要贡献[37]。其中,氨基糖和膜脂质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两种标识物。氨基糖是微生物细胞壁的关键组分,通过分析不同种类氨基糖的比例可以得出细菌与真菌对土壤有机质的相对贡献[38];而古菌的膜脂质与真菌、细菌有所差异,也可以作为土壤中的微生物标识物[39]。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菌残体也在土壤中大量存在[40]。还有一些报道同样证明微生物代谢产物(胞外聚合物,如酶、胞外多糖、脂类、糖蛋白)也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41]。
尽管微生物胞外聚合物和微生物各组分对土壤稳定有机质库的支配作用逐渐被重视[26-28],但是这些微生物代谢产物和残体的组成和降解过程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42]。虽然目前尚未揭开微生物介导的固碳过程的真实面纱,但采用更高分辨率的测定方法准确测定土壤有机质不同来源的构成,并且更详细表征微生物在土壤有机质积累及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显著提升我们对土壤碳循环的预测能力(图2)。
3 植物残体向土壤有机质转化的微生物驱动机制
3.1 微生物驱动机制研究手段
微生物是主导、驱动植物残体向土壤有机质转化的引擎[43];土壤微生物群落及生活策略的差异明显影响外源有机质的分配和存留。当前,每克土壤包含的数以亿万计的微生物中,尚有99%还处于未知状态,这也成为研究其物种、功能以及土壤有机质形成关系的屏障。土壤有机质与微生物随时空变化的高度异质性和可变性使得将二者建立起联系还存在一定困难[8]:输入土壤碳源的组成及数量均会促使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及群落组成发生变化,而微生物的演变反过来又会影响植物残体的腐解[13]。这意味着土壤有机质与微生物一直处于不断相互作用与动态变化之中,使研究者很难抓住微生物的整个参与过程。在传统的研究中,均一化、均质化的研究没有全面考虑到土壤有机质和微生物的高度异质性。此外,受研究手段的限制,大部分研究并没有把研究尺度放在土壤微生物生长、代谢的微米或毫米等微环境中,往往只关注了宏观的结果而忽略了微观尺度实际的动态作用过程。
近年,稳定同位素示踪与分子生物学技术(如DNA/RNA/PLFA-SIP、高通量测序等)被逐步引入到土壤学研究领域,其耦联分析方法为深入探究微生物在土壤有机质更新、稳定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手段[44]。其中,稳定同位素探针(SIP)为研究微生物的功能和对底物的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经过碳同位素标记的PLFA、氨基糖、DNA、RNA等化合物为研究这个微生物代谢“黑箱”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45-46]。13C可以追踪植物—微生物—土壤系统中的碳流并识别该过程中的关键微生物功能群(图2)。
在微观研究尺度(纳米、微米等)方面,超高分辨率显微镜成像技术与同位素示踪技术相结合的纳米二次离子质谱技术(NanoSIMS)的出现,为实现有机质转化过程中微生物过程的原位观测和可视化提供了崭新的机遇[47-48]。该技术能将研究的空间分辨率将到几十纳米以下,弥补了传统研究手段不能分析土壤基质与微生物接触的物理—生物界面过程的缺陷。在具体应用过程中,需要利用稳定或放射性同位素对目标微生物进行标记,并与透射电镜(TEM)、扫描电镜(SEM)、荧光原位杂交(FISH)、催化报告沉积荧光原位杂交(CARD-FISH)、卤素原位杂交(HISH)、X射线能谱仪(EDS X-ray)等耦联使用以确定参与碳循环过程的微生物种类和功能[49-50]。NanoSIMS既能提供土壤微生物的生理、生态特性信息,也可以识别具有复杂组成的土壤样品中代谢活跃的微生物细胞及系统分类信息,这对于从微观尺度上理解微生物对植物残体的转化和土壤有机质的形成等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具有重要意义[48-49]。

图2 土壤有机质形成及来源的研究模式Fig. 2 Research mode of soil organic matter formation process
3.2 微生物作用过程
土壤微生物对植物残体的利用、转化过程均与自身的群落特征、活性和生理特性密切相关[6]。土壤微生物对植物残体的利用和固持过程一般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微生物分解所接触到的植物残体,并同化分解过程中所产生的部分低分子量化合物(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以满足自身的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将植物残体转化为土壤微生物量碳;其次,通过自身的进一步代谢将微生物量碳转变为微生物来源的有机质[51]。微生物在这样反复的生长—代谢过程中不断以代谢产物(如胞外酶、胞外多聚物等)或残留物(如几丁质、肽聚糖等)的形式将植物残体彻底转化为土壤有机质[3,52]。不同微生物种群的代谢产物和残留物的释放模式、种类及数量均有所区别。而微生物释放出的不同种类化合物也会反作用于残体碳的固持过程,例如胞外酶具有保证养分供应的作用,能破碎植物残体和微生物大分子碎屑,产物可被微生物再次利用[53];而胞外多聚物能够起到连接微生物和底物的作用,可促进或抑制碳的释放[54]。
除微生物自身生理功能外,土壤环境也是影响微生物对植物残体碳转化的重要因素。首先,土壤不同颗粒组成、结构等会影响微生物对植物残体的可接触性[55]。被团聚体包被的有机质必须先经过团聚体破碎过程才能被微生物利用。同样,土壤有机质与矿物质的结合也会降低微生物接触的机会[55-56]。其次,土壤含水量、水分的流动性和异质性,以及干湿交替等均可以造成微生物呼吸活动和生物量的变化,也会影响微生物对底物的同化能力,从而引起土壤各形态含碳化合物的再分配[57]。再次,在受到外界的胁迫下,土壤微生物会同化更多的底物以满足自身生理功能的需要;同时,不同类型的胁迫条件会使微生物释放出不同的物质(如渗透物质、低温保护剂等)以提高自身的适应性,在满足自身压力耐受性的同时,也调节了对残体碳的利用及转化速率[58]。此外,全球气候变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微生物的活性和群落演化,并增加了植物残体的输入量,从而加速有机质周转,形成全球升温的正反馈。
最近,Liang等[3,10]提出土壤微生物对土壤有机质形成和转化的作用包含体外修饰(ex vivoModifcation)和体内周转(in vivoTurnover)两个方面。其中体外修饰作用指植物残体输入土壤后,不易被微生物利用的组分会经过胞外酶的分解转化过程,而最终还不能被微生物利用的植物源碳则在土壤中沉积(即植物源有机质贡献于土壤有机质的途径)[3];同时,易于被微生物利用的有机组分会进入由不同种类微生物组成的“微生物碳泵”(Microbial Carbon Pump),并通过细胞摄取—生物合成—细胞生长—细胞死亡的途径转化为微生物源有机质(即微生物源有机质贡献于土壤有机质的途径)[3]。由于土壤微生物周转速率快、生长周期短,经过周而复始的世代繁衍和同化过程导致不同活性和数量的微生物残留物在土壤中迭代持续累积(即续埋效应,Entombing Effect)[33]。因此,体内周转过程成为植物残体向土壤有机质转化和累积的重要途径。该碳泵的概念同时强调了植物源有机质和微生物源有机质在土壤中的形成和累积过程[9,33],为明确土壤有机质的形成和不同来源相对贡献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详细地确定微生物碳的利用效率,并将该方面的研究更多地纳入建模工作[59]。
4 土壤有机质(碳)的稳定性
有机物质在土壤中受到微生物驱动转化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抵抗干扰及恢复到原有水平的能力,即土壤有机质的稳定性。土壤有机质是有机碳的赋存场所,土壤有机碳则可作为机质的化学量度,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割;土壤有机质的稳定性在很多方面也是通过有机碳的稳定性来表征,因此本文将二者进行统一,综合考量。以往针对外源有机质输入土壤后土壤有机质(碳)的稳定性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通过分析腐殖质的组成反映新、老有机质的转化和稳定情况;二是通过“新碳”与“老碳”自身化学组成及不同结合、保护状态进行探讨。由于土壤有机质(碳)的稳定性取决于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并随不同时空尺度而异,其真实的稳定机制至今还不能完全明晰。
4.1 有机质(碳)化学组成和分子结构能否解释有机质(碳)长期稳定性?
土壤有机质(碳)的固存时间取决于植物残体的化学组成和有机碳分子结构的抗降解性这一观点已被广泛认可。通常,植物残体中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类物质被认为在土壤中最先分解,而一些难分解组分(例如木质素、具有烷基结构的碳等)则在土壤中富集并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化—缩合成难分解的腐殖质而长期存在[60]。因此,木质素、烷基碳或芳香碳等有机组分或分子结构的多寡常被用来表征土壤有机质(碳)的稳定性[13,61]。但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断进步,一些新的研究得出很多冲击以往“固有思维”的结果[13,21,62-63]。例如,Xu[64]和Wang[65]等研究表明,输入土壤的不同植物残体只在分解初期才具有不同的降解速率,而在后期则差异不大,这暗示着植物残体自身的抗降解机制可能仅在有机质分解初期起作用,但其在土壤中固定的长期稳定性似乎并非受自身分子结构影响。也有研究认为黏粒的吸附和团聚体的闭蓄作用可能是主导植物残体分解后期稳定性的机制[16]。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发现木质素、黑炭和腐殖质等传统意义上的抗分解有机质在土壤中也能拥有较快的周转速率[66]。木质素可能会比一些活性有机碳物质(糖类、蛋白质等)更易降解[14,26,67]。Klotzbücher等[62]认为木质素所呈现出的这种“快速分解”机制可能是细菌和真菌在初级代谢和次级代谢等不同阶段相互配合的结果。同样,黑炭这种具有高度浓缩的稠环芳香结构有机质也被发现是分解较易的。近期研究表明新鲜有机质的添加会加速黑炭的分解[21]。此外,有报道在河流中检测到较高数量的黑炭源溶解碳,印证了黑炭易被氧化降解的存在性[66]。而对于腐殖质,疏水性和氢键被认为是其稳定性的主要机制[63],但其稳定性是相对的:环境条件的改变、简单有机分子在腐殖质结构中的穿插等均有可能破坏其稳定结构[13,21]。再加之目前关于腐殖质分子结构及其形成过程的多种猜想和不确定性,也直接导致其稳定机制的真实性受到了很大质疑。因此,土壤中任何形态的有机质(碳)均有可能被分解,其真实稳定机制绝不是由有机质(碳)的结构、分子抗性单独制约的。
4.2 物理、化学保护与微生物代谢的共同作用
显然,土壤微生物在长期的繁衍、进化过程中已经具有了分解各类型有机组分的能力,只不过在分解过程中会优先选择更易分解的物质,但这并不代表其他抗分解能力更强的有机质不能被矿化[16]。因此,有机质能否顺利接触到微生物(即空间不可接近性)以及周围环境条件是否适宜于微生物的分解则成为有机质(碳)稳定存在的重要限制因素。近些年,基于土壤团聚体尺度的研究逐渐发现有机质(碳)库的保护与稳定机制存在多样性及差异性,是团聚体的物理保护—土壤矿物的结合—微生物代谢过程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结果。
土壤对有机质(碳)的化学保护作用主要指土壤无机分子与有机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使有机质(碳)难以被微生物利用。其中,黏土矿物和金属氧化物是有机质(碳)结合的主要载体[56]。有机质(碳)以配位交换、氢键、阳离子键桥和范德华力等多种形式与土壤矿物的结合被视为土壤有机质(碳)最重要的稳定机制[56,68]。土壤矿物的化学保护作用因矿物类型、理化性质和有机质(碳)性质的不同而异。通常,黏土矿物比表面积和带电量越大,对土壤有机质(碳)的吸附能力也更强。但比表面积不是评估有机质(碳)固持量的绝对因素,还要考虑多价阳离子、铁铝氧化物的协同作用。铁铝氧化物不仅含量较高、氧化还原性质活跃,还具有巨大的表面积和大量的表面电荷,对机质(碳)具有较强吸附能力[69]。有报道指出,水合金属氧化物可以同时与黏土矿物、有机质结合,形成黏土—金属氧化物—有机质复合体[70],因而在考虑化学保护机制时应充分考虑黏土矿物和金属氧化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土壤环境中的金属阳离子的影响。从有机质(碳)种类看,来源于植物及衍生的芳香碳主要富集在土壤的粗粒级组分[26],而通过微生物产生的烷基碳与羰基碳则主要分布在黏、粉粒组分[71]。这表明植物来源碳和微生物来源碳与土壤矿物结合的机制存在差异,而积累在更细粒级部分的微生物代谢产物可能具有更长的驻留时间。
土壤团聚体是土壤有机质(碳)主要的赋存场所,能通过自身的物理保护作用将有机质(碳)包被起来,从而免受微生物的分解[72]。因此,团聚体保护能力和容量是土壤固碳潜力的物理基础。不同粒级团聚体保护有机质(碳)的机制和效果均不同:大团聚体虽然能包裹更多的有机质(碳),但微团聚体中有机质(碳)结构不易遭到破坏且周转周期更长[21]。目前普遍认为新输入的有机质促进大团聚体形成,而微生物和植物的碎屑形成微团聚体的核,降解程度更高、体积更小的“老”有机质(碳)则封存于黏、粉粒中[73]。该理论符合Lehmann和Kleber[7]的有机质连续体模型。团聚体对有机质(碳)的物理保护与团聚体的形成发育过程密切相关[74],研究土壤团聚体的形成机理对了解其物理保护作用至关重要。植物残体输入后为土壤团聚体的形成提供了胶结物质,大幅提高了微生物活性,在促进土壤颗粒团聚化过程中也提高了自身稳定性。因此,土壤表层的有机质(碳)稳定性可能更依附于团聚体的物理保护。但团聚体对有机质(碳)的物理保护存在饱和点,因此掌握有机质输入—输出平衡十分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团聚体对颗粒有机碳的包被(即物理隔离作用)和有机—无机复合体的结合(即化学吸附作用)是同时存在且相辅相成的,这因不同级别(或尺度)团聚体而异,还受制于微生物的接触与分解,这也增加了团聚体物理保护机制研究的复杂性。
微生物对有机质(碳)稳定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能通过分解作用将土壤中稳定有机质矿化,也能通过同化作用将土壤中的可利用碳源以代谢产物的形式贡献于土壤有机质,还能通过影响团聚体的周转而间接作用于土壤有机质(碳)稳定性。由于土壤微生物存在“多重身份”,以往研究较少从微生物自身角度探讨有机质(碳)稳定机制。土壤微生物对有机质的利用因不同生活史策略而异,K策略微生物(例如真菌)主要分解较难降解的有机质,r策略微生物(例如细菌)则偏好利用一些活性有机质[75]。K策略微生物虽然对有机质的利用速度缓慢但利用效率较高。此外,微生物在土壤中的分布因土壤结构及微环境的制约而具有较高的空间异质性;这种空间异质性一方面导致了微生物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使微生物与有机质(碳)的可接触性因空间而异[13]。而这些均显著影响着有机质(碳)的生物稳定性。此外,微生物也是某些稳定有机质形成的驱动者,换言之,微生物的同化是外源有机质在土壤中稳定固存的关键。如前所述,土壤微生物的死亡残体、代谢残留物、分泌的多聚化合物等均属于较难分解的有机质[16]。不同土壤生物群落对土壤稳定有机质(碳)库的贡献有所差异,K策略微生物生物体更难分解,对土壤稳定有机质库的贡献值也更高[38]。鉴于微生物在分解和合成有机质这两方面的作用,有必要评估并权衡土壤有机质积累和生物分解过程之间的平衡,以达到植物残体归还的最大固碳效益。
5 总结和展望
植物残体在土壤中的腐解过程调控着土壤有机质(碳)的化学组成和空间分布。了解并定量土壤有机质的化学起源和赋存状态有助于明晰土壤碳汇潜力。近年来,以同位素示踪、分子生物学和高分辨率成像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研究手段被应用到土壤学领域,突破了传统有机质研究方法的局限。以此为契机,土壤有机质周转和碳循环的相关研究已经趋向于形成以固碳减排、地力提升、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将地上—地下不同空间、宏观—微观—纳观等不同尺度、有机—无机—生物等不同界面研究相融合,地学、生命科学和农学等不同学科共同参与的前沿交叉研究领域。当前,无论是在新输入残体在土壤中的腐解和分配过程、土壤有机质的稳定与矿化机制,亦或是土壤有机质和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关系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展。然而,土壤是一个多种物质并存、多种过程同时发生、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开放的、复杂的系统;土壤有机质的转化同样具有非线性、非平衡和非理想的特征。毫无疑问,这些让我们很难去完全捕捉并明确发生在其中的各过程,我们仍面临许多困难、争议和挑战。此外,各项新的研究技术并没有得到完全普及,研究方法也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结合本综述内容,认为未来的研究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图3):

图3 未来研究架构Fig. 3 Future research framework
1)精确区分不同有机组分碳源。植物残体在腐解过程中将不同化学组成、腐解程度的有机组分与土壤原有机质混合在一起,增加了有机质组成的复杂性。因此,精确区分土壤中各有机组分是土壤有机质周转研究的瓶颈。这也成为不同学者对有机质形成理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到底是植物本身的化学差异导致了土壤有机质化学组成差异?还是微生物的代谢作用重新布局了土壤有机质的化学组成差异?土壤有机质到底是以什么形式赋存?是以腐殖质为主,还是以微生物代谢产物或植物难降解组分为主?土壤中CO2的排放主要来自哪些有机组分?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以准确区分土壤不同有机组分为前提。当前,碳同位素技术对碳元素在各有机质库的迁移具有良好的指示作用,可以起到一定的区分作用;也可以选择具有一定特异性和稳定性的标识物(如氨基糖和磷脂脂肪酸等)作为区分植物源和微生物源有机质的手段。此外,还需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明确土壤有机质库的不同来源。
2)深入探究植物残体向土壤有机质转化的微生物作用机制。土壤微生物在有机质合成和转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对土壤有机质库的贡献是未来研究的关键。但由于土壤微生物数量、群落组成的易变性,分布和生理特性的异质性,加之土壤有机质本身赋存的高度异质性,给相关研究带来很大困难。在非常复杂的土壤理化环境中将土壤微生物过程与有机质周转过程对应联系起来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些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将同位素示踪与分子生物学技术结合,在微生物种群结构和功能层次上探讨碳的流通过程与微生物相互作用机理。并利用NanoSIMS等现代土壤表征技术探讨植物残体碳在土壤中循环的微界面过程,从微观尺度(纳米、毫米、单细胞)解析微生物过程与有机碳异质性的耦联互作机理。此外,在考虑微生物对土壤有机质转化作用的同时,还需深入了解微生物代谢产物和死亡残体的化学组成及其分配、周转和稳定机制,以期更充分地认识微生物在土壤有机质累积过程的作用。
3)加快基于多因素共同调控的有机质(碳)稳定性研究。目前,对于土壤有机质(碳)的稳定性还未形成统一的主导机制。但毫无疑问,影响土壤有机质(碳)稳定性的因素不只是某种因素单方面的作用,并且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如最近研究提出的糖类、蛋白质等同样能在土壤中长期存在的机制是什么?土壤中木质素也能较快降解的机制又是什么?此外,团聚体的物理闭蓄和土壤矿物的化学吸附被认为是有机碳稳定最主要的机制,但还需对其微生物稳定机制做更深入的研究。除传统研究所侧重的土壤自身所能提供的物理、化学和微生物稳定等“内在机制”外,土壤有机质(碳)的稳定性还受到气候、人为土壤管理措施、土壤类型和土壤环境等多种因子共同作用[13]。因此,必须客观、全面地评价与理解土壤有机碳固定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子以及各因子间的协同作用与权重。
4)从更微观尺度探索土壤碳平衡机理及植物残体输入阈值。植物残体的输入所产生的最终固碳效益将通过土壤有机碳的收支平衡体现。土壤对有机质的固持能力有限,植物残体的输入在满足微生物生长需求的同时,多余的碳源将通过异养呼吸方式损失,对土壤和环境均产生负面效应。因此,探索植物残体输入与土壤有机质输出之间的量化关系十分重要。但以往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较大尺度的农田固碳潜力与碳收支平衡研究,而忽略了微观尺度尤其是基于微生物代谢视角的土壤碳平衡研究。土壤微生物过程控制着土壤碳库的输入—输出平衡、截获与更新[4],未来应加强该领域研究。这对于增加外源有机物料添加后碳固定的正面效应意义重大。
5)加强多环节土壤有机碳循环过程研究。土壤有机碳循环过程是碳在植物—土壤有机质—微生物间流动的过程函数,而之前大部分试验均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目前,迫切需要对植物—土壤有机质—微生物系统中不同来源碳的分布及其输入、转化和稳定等环节进行定量研究,从而明确植物残体输入后外源碳在土壤中的流通、稳定和矿化过程之间的关系,确定土壤碳累积/矿化速率,认识土壤固碳本质。此外,气候变化、环境变化及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于植物残体碳在土壤中的循环过程,应尽快推动建立多因素耦合作用、多环节相互交叉下包含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碳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