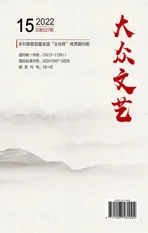杰克·伦敦《白牙》与沈石溪《双面猎犬》生态主题的对比研究
2019-07-12汪莉雅贵州大学550025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00081
汪莉雅 (贵州大学 550025;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00081)
美国20世纪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的《白牙》讲述了一只叫“白牙”的狼成为一条忠实的家犬的故事。百年之后,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于2010年撰写小说《双面猎犬》,讲述了一只叫“白眉儿”的豺狼成为人类社会得力猎犬的故事。两部作品均以野兽被驯化成狗的成长过程,以细致入微的环境描写推动了动物从荒野走进人类居所的情节,与第一、二次生态批评浪潮中以荒野、动物和人类居所为视角的生态关怀相呼应。而在全球化的第三次生态批评浪潮提倡的跨文化的“地域整体观”的大背景下,这两部作品在生态主题上的联系的有待挖掘。这两个作品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体现出荒野与人类社会的对立统一,但生态主题有所侧重,由此阐释这两部作品在生态主题的关联。
一、《白牙》和《双面猎犬》的不同文化背景及对生态关怀的呼应
本节以作者的文化背景及小说的大体情节为主要内容,阐释作品的生态关怀。
《白牙》的作者杰克·伦敦1876年生于旧金山一个农民的家庭,出生时正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城市转型期。因家境贫困,自幼当过童工,装卸工和水手等,后经历一次经济大萧条,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反思逐步成形,又受赫伯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超人哲学”等具有人文精神和个人主义色彩的思想所影响。尔后他在加拿大的育空淘金热的影响下参加淘金,虽收获甚微,却为其文学创作《野性的呼唤》和《白牙》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灵感,促成其商业成功。《白牙》于1906年出版。伦敦在创作时,生活也经历了从年少的不羁与闯荡走向婚姻的稳定,因而有学者也指出《白牙》从荒野走向人类社会的情节是伦敦自传式的表现。《白牙》的情节凸显生态关怀:通过讲述了一只有四分之一狗血统的狼被驯化的历程,串联了二十世纪初的加拿大西北部的荒野,和美洲原住民部落、克朗戴克的淘金前线及已经高度工业化的加州大都市,对加拿大西北部极圈附近未开采的荒野及狼群的习性做了细致描写,尔后转到主人公“白牙”以个体为单位审视对手的力量以认识弱肉强食的世界。在一次靠近人类篝火被美洲原住民捕获后,领会了人类主宰动物与工具的能力,由此串联了荒野与人类社会。又由印第安人的豢养而偏爱人类通过工具制造改变世界面貌的能力及其带来的便利,随主人来淘金前线,被一个丑陋的白人投机者买下,实现了生活环境的第二次次跨越,自己也被工业化下的疯狂牟利的人性塑造得充满仇恨。而白牙在一次战斗中遭遇强敌,几近死亡,却被颇有声望的上流社会斯科特所救,斯科特以慈爱与鼓励唤醒白牙内心的友好,白牙遂对其产生了不可分割的依恋,使得斯科特将其带至在加州靠近大城市的家族别墅,达成了生活环境的第三次跨越。最后通过白牙对于所有居住环境形成整体的的认识,通过白牙走到当时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顶端、直面社会矛盾的情节反映了工业化下的生存环境。
《双面猎犬》的作者沈石溪于1952年生于上海,生活时代正值中国农业社会的城市化渐进转型。他17岁赴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插队落户,其对荒野的源泉便源于18年的云南生活,尔后他在当地当过小学当教员,后应征入伍,并凭借优秀的文笔加入省级和国家级作家协会,期间迎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陶冶与西方文学的洗礼。现为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业创作员。《双面猎犬》是沈石溪的中篇小说,出版于2010年,在写这部小说时,沈石溪已经离开西双版纳,在成都军任区创作员18年,出版了大量成功作品,在中国儿童文学界享有一定声誉。《双面猎犬》的背景设定在滇北高原上,以混血豺狗“白眉儿”的视角,连接了怒江一带的荒野与一个传统的人类社会。故事亦从主人公的父母展开,奠定了之后白牙在其社会群体中的地位,亦细致描绘豺群及其他野生动物的习性。作品通过白眉儿被逐出群,无奈成为一位卑微的山民的狗,连接了荒野与人类居所。着重描写了荒野的群体生活与人类社会的群体生活的异同,以体现生态关怀。与杰克·伦敦《白牙》的姊妹篇《野性的呼唤》相似的是,沈石溪也为《双面猎犬》写了一部类似《野性的呼唤》的后续《混血豺王》,讲述白眉儿被迫再次从人类社会回归荒野的故事,在写作形式与生态关怀上与百年前的杰克·伦敦相呼应。
二、《白牙》与《双面猎犬》中荒野与人类社会的对立统一及其生态主题
(一)《白牙》个人主义视角下对工业化产生的生态忧患意识
《白牙》的荒野设定是加拿大西北部靠近极圈的地区,开场便是笼罩着阴霾与极寒的冬天,以无尽的死寂嘲笑着被饿狼尾随、驾着六条雪橇狗的两人运输队伍,展现着荒野的弱肉强食、人类渺小的存在及其不屈的意志。尔后白牙生于一个只有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核心家庭,兄弟姐妹在饥荒中的死去让他审视自身的力量,而他也学会不断扩充自我个体的力量,学会弱肉强食的法则,以个体为主要战斗形式不断战胜弱小,却在见到人类那神秘莫测、主宰万物的智慧时感受到一种超越了战斗的生存方式,因而无计可施,诚惶诚恐。尔后见到赶来营救的母亲臣服于人类、看见人类搭建的帐篷、生起的火、制造的工具,坚信了人类能够改变世界智慧与力量,视人类对自身的主宰及对动物的主宰为“神性”。这便是《白牙》中的荒野,强调了以个人主义审视个体内部所蕴含的力量的思考方式。
白牙入驻印第安人的居所后,逐渐在人类对其生活方式的调节下对人类充满生气与互动的社会产生偏好,亦或许是因为逃回荒野后回归受到主人的嘉奖,他甘愿牺牲自由意志而服从于人类的意志,终在具备生存荒野的能力时选择了人类居所。在第一位主人一丝不苟的“胡萝卜加大棒”式的豢养下形成了一味服从于强者的性格,由原来被狗群欺负逐渐长成为欺负狗群。尔后又去到另两个北美大陆上业化程度更为发达的地方——育空堡的淘金前线和美国加州的大城市附近,他的性格在新的环境里得到调整和完美的适应;在淘金前线,白牙被卖与一个面相丑陋、阴险狡诈的白人淘金者“美人”史密斯,此人的性格亦是工业革命资本积累者疯狂争夺资源的真实写照,他以营利为目的诱骗印第安人,用酒精使其丧失意志,臣服于自己的不公平交易,又对白牙的意志进行强烈的压迫,用人为地折磨使其充满本不该有的强大仇恨与破坏力,将白牙塑造成了一个攻击与破坏一切的角斗士,成为了供前线穷苦人们取乐、富人区为一睹“荒野之性”的牺牲品,也让史密斯这个能力卑微的人赚取了更多利润。尔后白牙终遇角斗劲敌,在被咬出致命伤时受史密斯的嘲讽时,又被有名望的、家境殷实的矿学研究专家斯科特及其车夫马特所救,养在其育空地区的小屋中,他们察觉了白牙的对人类活动的敏锐判断,通过鼓励引导白牙不再充满仇恨,在感化中斯科特与白牙之间逐渐形成了友情的纽带,以致白牙见其而喜、不见其则悲。而正是这种鼓励和纽带的不断深入,使得白牙在主人的引导下能够融入多阶级共存、条框约束的大都市,在故事的最终,他与一个受环境压迫、有因为警察做手脚而被斯科特法官父亲误判的、无力回天而充满仇恨的亡命之徒展开搏斗,最终战胜这强大的敌人,挽救了主人及其家人的性命,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且不论白牙这一行为正义与否,作者正是留给读者这一开放结局:一方面白牙完美地融入了三个工业化程度相异的人类社会,个体能力得到升华,而另一方面则又成为人类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阶级不断分化下人类压力的释放物及其建立的所谓的“正义”的执行者,处于底端的人不断被歧视被牺牲,而造成这一切的则是不可逆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
因此这部小说中荒野与人类社会的对立统一集中在美国20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下人类社会的多元发展,通过串联白牙以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出发、以个体自身力量审视三个工业化迥然不同的环境形成统一,而其对立又是愈发不可调和的,体现在以人类为首的动物的力量和精神与人类所创造的机械力量所形成的极端社会分化。白牙虽然战胜荷枪实弹的亡命之徒,却又在梦里害怕着人类制造的、自己难以理解的骇人机械;而在工业化背景下处在底层、生活原始的人与处在工业化顶端的人之间确乎有着一条“鄙视链”,正如也淘金者史密斯鄙夷和利用生活原始的印第安人,斯科特鄙视在社会底层投机的史密斯的不齿行径。这种工业化下荒野与人类社会的日益对立正是作者借白牙视角所想表达的惶恐与失望,注重反映了对工业化的生态忧患意识。
(二)《双面猎犬》:群体视角下对城市化的生态拯救意识
虽说大体情节与《白牙》相似,作为对其致敬,《双面猎犬》中的环境设定则是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的中国云南北部的山区,开篇即点出人类及其猎狗在荒野环境中的优势地位,又通过猎犬与母豺斗败“野猴岭”霸主猴群后获得优势地位,再到后来主人公白眉儿降生在豺群凭借社会内部协作获取捕食优势,可见其不是白牙以个体为单位其他个体内部力量的思考方式,而是以群体为思考角度,争取群体内相对优势地位的思考方式展开。而主人公是比狼弱小而更狡猾、更擅长社会分工合作的豺,相比狼群的松散,豺群的社会十分稳定,崇尚以捕猎实力与计谋称王,凭借实力获取层级地位,却将牺牲群内老弱病残者当作铁律。主人公生于豺群,却因为受母亲罪行影响成为孤儿,自小遭受群体的鄙视,苟且长大,后被当作牺牲品去试探类的陷阱,却意外暴露超强捕猎实力,从此看到自己的在这个群体地位晋升空间,而殊不知豺王这一地位能对其造成的压迫,豺王恐其实力威胁便设计其在一次行动中对其错误发号施令,使白眉儿破坏行动而受群体所恨,遂将其逐出豺群。这便是《双面猎犬》的荒野设定,强调群体及其层级制为生存依附,形成了审视个体在群体层级中拥有的地位的思考方式。
《双面猎犬》主人公入驻人类社会的过程则与白牙截然不同,相比于白牙视人类为超越丛林法则的“神”,带有《圣经》的宗教色彩,白眉儿受豺群中对人类刻板印象的缘故,视人类如神秘未知的“鬼”,这一描写与中国农村的传统的对未知异类的认识所产生的教化趋向一致。而这个弱小的豺,则是受到冬天荒野生存条件恶劣的影响而被迫靠近人类,而当被这个老头将其拴住时,他出于对集体的依附感和安全感而放弃抵抗,就此选择人类社会。因而相比《白牙》的不断适应,《双面猎犬》主人公选择类居所则是出于为依附而存活的委曲求全。而《双面猎犬》中人类社会的设定则更加单一,是一个传统农业村落,依据地理优势发展捕猎,全篇不见任何工业化发达的痕迹,却见村委会,推知城乡的连接,由此推出城市化发展的背景。在这个人类社会中,依然存在着以实力和领导力彰显地位的等级制,正如村长被描写得有勇有谋,带领大家共同打猎致富,而又存在着猎狗地位与主人挂钩的情形,因此村长的一条黑狗虽然老,却饱受村民的爱戴,在来自豺群的白眉儿看来,人类社会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差序格局与豺群崇尚捕猎实力、牺牲老者的传统是相悖的,而这种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并没有出现在个人主义萌生的《白牙》中。凭实力争取群体内优势地位的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延续和狗与主人地位的挂钩更加明显地表现在白眉儿的主要经历上,一开始白眉儿服从于卑微懒惰、沉沦于失败而拒绝打猎的主人,才美不外现,并且在主人指使偷鸡后还得背负主人的过错,受村民责备,可见在传统社会中人狗的道德捆绑,呈现出《白牙》没有的人类社会纲常伦理。最后白眉儿在被卖与屠户的千钧一发之际向村长求救,获得了村长的认可,并在村民的再次错怪下忍辱负重挑战了自己在荒野中的生存极限,最终捉住了真正的偷鸡贼,为村除害,不辱使命,真正展现了自己作为村长的猎狗的资格,凭实力获得群体内的地位和认可。
因此《双面猎犬》中荒野与人类居所的对立统一更注重通过主人公在荒野的和人类社会的两个群体塑造的品格的对立,在其凭实力不断争取地位的过程中趋于统一,强调的是和个人主义截然不同的集体内部文化。虽说是一部歌颂传统社会田园生活的儿童读物,没有深入城市的工业化,却在推动对中国自然与人文社会深层结构的了解中具有深层意义,写作时间与中国上下日益重视“绿色发展”的趋势相呼应,是新时代中国文化的产物。如果说杰克·伦敦在19至20世纪空前发展的工业化中对对荒野与人类居所不可调和的对立抱惶恐与失望态度,《双面猎犬》则在新时代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以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这不可调和的对立注入了新的希望,以儿童文学的形式助新一代人树立对自然的认识,呼吁人们亲近自然,弘扬了自然背景下形成的中华民族长久稳定的人伦观、传统美德与和谐共生的理念。,以科普为实际行动,突出了照应新时代城市化进程的生态拯救意识。
三、结语
两部作品虽然都是讲述动物从荒野融入人类生活,但生态主题通过文化特色呈现不同侧重:《白牙》更注重展现工业化进程对自然面貌的改变,通过白牙的驯化,强调了人类所创造的机械力量与动物的肉体力量间的不可调和,反思了19至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工业化的剧变导致的人类性情的剧烈分化;而《双面猎犬》作为对杰克·伦敦《白牙》结构上的延续,扎根中国文化,更注重展现荒野生活与中国西南边陲传统村寨生活的和谐共生,通过白眉儿的驯化,强调了人类与动物在处于猎捕的对立关系下思维达成的统一,以中国的城市化为写作背景,用远离都市的叙事架构映射了荒野与人类居所的和谐形态,通过描写群体中不同角色所呈现的不同心理,让读者了解人类社会与动物群体间的共性与个性。如果说《白牙》注重对20世纪美国工业化空前发展中形成荒野与人类居所不可调和的对立抱惶恐与失望,突出生态忧患意识,《双面猎犬》则是在这不可调和的对立中,以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根基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新时代为背景、以歌颂田园为手段,给荒野与人类社会的日益对立注入了新希望的生态拯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