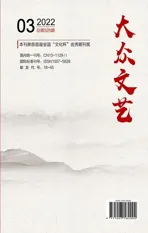沈从文湘西文学世界中的人性与命运
——读《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
2019-07-12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210037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 210037)
沈从文的作品以其清新质朴的语言风格,对理想的人性和生活方式的描绘,在现代文坛中独树一帜。沈从文先生有自己的一套创作理念。在那个社会动荡不安,人朝不保夕的年代,他着眼于底层人民人生进行发生着的一个个阶段,喜怒哀乐中的那一点人情味,在人生的没有答案的艰难中,发现人性中的美与善,描绘了一个动人的湘西文学世界。
一、艰难人生,美好人性
人性的美与善是沈从文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在他的笔下,小人物的卑微、生存的艰难和人性最美好的东西相伴相生。正如他说“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怀着一个艺术家的感情,却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在他的湘西世界里,塑造的是一种特别的生存形式,也自有一套美与善的标准。
在《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中,牛保和夭夭是主要人物,也是沈从文的湘西文学世界里极具代表性的两类人。牛保是船上的水手,在辰河上起早贪黑,换取微薄的口粮,每辛苦十天半月后,再将剩余的气力和钱财尽数交给吊脚楼上的女人。但这样一个没有文化、满口野话的水手,却具有着单纯率真的气质,会在作者同他搭话时“害羞”起来,并慷慨的赠予作者核桃。得到苹果后,又飞奔的跑去献与吊脚楼上的女人。而他与女子那通常为伦理道德不齿的肉体的交易,在沈从文的笔下也显得温情脉脉。“牛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记着吗?”“唉唉 我记得到!......冷!你是怎么的啊!快上床去!”“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这样的对话,近乎爱人间的别离了。但作者也并不会理想地将之上升为两个人的爱情。这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原始而粗陋,真诚而朴实。这温情支持着男人和女人坚韧的生存着。“想到这些眼泪与埋怨,如何揉进这些人的生活中,成为生活之一部时,使人心中柔和的很!”
夭夭则是吊脚楼上怀着更多幻想的女子。她对年轻的城里人存着那一点少女的羞怯和梦想,打扮地“像个观音”似的美丽,轻手轻脚地出现,抿着嘴笑,轻轻的说话。被唤走时做一个爱娇的表情,自言自语地抱怨一句。她格外的年轻,格外的美丽,命运也就显得格外的残忍。但她不会沉重地自知和哀叹,始终维持着自己的一点情致,一点向往。沈从文没有看轻她,也无法帮助她。只是怀着真诚的同情了解和描写她。就在读者以为夭夭离开了,故事也要结束时,河边又传来一阵歌声,“曲调卑陋声音却清圆悦耳”。何止沈从文站在寒风中痴上许久,看到这里的读者又怎能不为之深深触动呢?
二、无意识命运的悲剧感
身处在那个时代,沈从文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纯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者。他的作品的深刻性在很长时间内都被低估了。沈从文出生在中国近代最动荡的时期,川、湘、黔、鄂的交界地。年少入伍,看惯了许多迫害和杀戮。二十一岁即独自到北京闯荡,自学写作。这些经历使他在早年就对社会、人生无常的一面有了很深的认识和体会。沈从文自己曾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都欣赏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够欣赏我的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过早的见惯愚昧和残酷使他以后将残酷和愚昧写入作品时消除了任何炫耀猎奇的可能,反形成了一种追求美好人生、善良德行的品格。”如同参禅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三重境界。这样的追求与人在未曾认识到残酷时对美好希望单纯的相信有些相似,但其实要深刻和坚定得多。
尽管本意在展现和歌颂人性的美和善,沈从文在描写湘西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时,依然不可避免一种命运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在他的多数这类作品中都可以捕捉到。美和落后同时存在,“自然”的背后带着一种无意识的循环往复。夭夭向往与她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我”,却只能停留在对一夜情缘的幻想。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命运的沉重。虽然作者的描述止步于动人的歌声,我们却不得不想到夭夭的后来。虽然作者的笔触止步于美,我们却也会感受到隐伏的悲剧性。
作为沈从文本身,未必不曾试图去做些什么,想要去给水手一些钱,对夭夭深刻的同情,然而最终只能化为一点沉默。既明白自己的无力,同时感到“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的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类似的想法在他的《虎雏》和《虎雏再遇记》里更突出,虎雏是个乡下孩子,作者试图“用最文明的方法试来造就他”,他却打了人逃走了。沈从文明白到自己做的不过是件“傻事”,“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审美性与悲剧感共存在沈从文的心中,糅合成了他看待湘西世界的态度,也造成了他的清新质朴而又包含着寂寞感的笔调。
三、沈从文:湘西世界特别的观察者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的寄托。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读了生活这本大书。而当他拿起笔,又自然地站在了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更多地脱离出来,在反观中,对湘西人那一套生活方式以及鲜活的喜怒哀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沈从文经验素材的丰富,是为许多作家羡慕而不得的。但如果说前期他在经验上是得天独厚,那么后期他的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自觉就更突出了。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讲述的两件事,先是听见那一声声“牛保”,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他听着,且在心里补充上没听到的部分,并有意的想认识这个人。有机会,“就冒昧的喊他,同他说话”,接触了那颗快乐多情的心。分别后,他遇见了邮船水手,很想知道他到了那里做些什么事情,于是跟着去了吊脚楼,这才见到和了解到了年轻的小妇人夭夭。沈从文对社会人生的丰富体验离不开他那颗敏感温和的心。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是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却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品评者。沈从文以独特的审美视角看待这些湘西底层的人民。他不着意于揭露社会的黑暗,也不打算如何批判这种生存方式的落后或道德性。只是忠实地记录着历经磨难而又倔强生存的底层人们的生活。
他关切俗世的情趣,对人怀着深沉的同情和热爱,在这自然的人性中发现着最真实的善和美。
沈从文处在乡村和城市的相交点。在城里人看来,他是乡下人,在乡下人眼里,又已将他当作城里人。但他自己,尽管在这其中感到寂寞,却从未感到分裂。他一生以一个“乡巴佬”自居,怀着诚挚的态度平等地接触、关心那些下层人民。他的审美眼光也是温和、怀着热爱的。因此他才能真正明白湘西世界形形色色的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爱恨情仇和喜怒哀乐。
四、结语
个体的命运或许可以改变,群体的命运却自有其道路。沈从文身处乡村和城市的交汇处。在城市的背景下,他强调湘西“优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活形式”。而真正着眼于湘西世界时,一方面他看见生命的坚韧,人性中的美和善,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这种生存状态的无意识性和落后性。这造成他的复杂情感,他对湘西世界和其中的人亲切,热爱,却又充满同情,哀婉,含有命运的沉重感。但无论如何,湘西世界,依然是沈从文永恒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