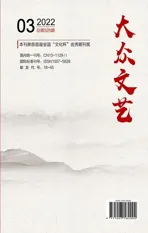《安娜·卡列尼娜》的影视阐释
2019-07-12河西学院文学院734000
(河西学院文学院 734000)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自1875年在《俄罗斯公报》上连载以来,它就“不仅属于托尔斯泰,而且属于全人类。”1苏联电影理论大师米哈伊尔罗姆称托尔斯泰为“最具电影性的作家之一。”在当今经典改编热潮的簇拥下,这部小说也成为被搬上荧幕次数最多的俄语电影之一。托尔斯泰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却在小说中无意运用了很多类似电影的叙事技巧。历代的电影工作者对他都格外钟情,作品改编类型包括电影、电视剧、芭蕾舞剧、话剧等。本人拟以小说和1997苏菲·玛索版的电影为例,分析电影文本对文学作品做出的阐释。
一、传记史诗
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均属鸿篇巨制,具有史诗风格。相对于编年史诗的《战争与和平》、旅程史诗的《复活》,笔者遂将《安娜·卡列尼娜》看作“传记史诗”。这种看法绝非牵强附会。一方面,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场面宏大,出场人物众多,据统计,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150人之多,还不算那些几笔带过的无名氏,对俄国19世纪70年代的生活可谓做了全景展现。作品由两条情节线构成,一条以安娜和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的纠葛,展现了彼得堡、莫斯科上流社会达官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另一条以列文的精神探索以及他与吉提的家庭生活为线,展现了宗法制农村的生活画卷。总之读者完全可以将其看成是托尔斯泰为安娜和列文两个人作的传记。另一方面,在高扬个人本位的西欧,自文艺复兴运动后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始,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从政治上推翻封建制度后,思想家、作家遂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聪明才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传记文学不断涌现,到19世纪更是走向了一个新高峰。崇尚人文主义思想的托尔斯泰在创作初期完成的《童年》、《少年》、《青年》自传体小说也从侧面展露出作者对于传记文学的钟情。不管是自传还是他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真实。托尔斯泰正是本着真实这一原则,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冷静客观、纤毫毕现地展示了安娜、列文的内心世界。作品中托尔斯泰主要采用作者叙述和人物叙述两种方式,作者叙述有利于以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的角度掌控全局,俯瞰整个故事的进程,其任务是人物的引出、背景介绍,和环境描写等等。另外作者叙述还经常深入人物的内心,表现人物情感的细微之处;在人物叙述上,作者通常借助文中人物之口,从文中人物的视角观照其对中心主人公的看法。由此最终做到了对其传主,既不溢美,也不隐恶,完成了为俄罗斯民众作传的书写任务。传记文学在西欧的发达进一步为传记影片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西欧的影视作品中,传记影片占很大比重。1997年伯纳德·罗斯执导的《安娜卡列尼娜》就属此类型。
二、传记影片
1997年英国导演伯纳德·罗斯执导的《安娜卡列尼娜》又名《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据说罗斯极度热爱托尔斯泰的作品,因此他以个人阅读经验,认为列文就是托尔斯泰的化身。著名的传记作家罗曼·罗兰就曾指出“列文和吉提的恋爱,他俩婚后的头几年的生活,就是作家自己家庭生活回忆的搬演。列文哥哥之死也是托尔斯泰的哥哥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追忆。”2所以罗斯执导影片时亲自担任编剧职务对原著加以改编,特意以列文的第一人称叙事贯穿全篇,并在片名上突出叙事者与作者的一致性。由于受电影时长限制,对长篇巨著的改编不被看好的原因与此也有很大关联。罗斯深谙此道,他撷取原著中几个精彩的片断,以梦境串联起所有的主要人物,敷衍成剧。致使安娜和列文演绎各自故事时巧妙地融为一体,比原著中的两条情节线交界之处的设计显得更加天衣无缝。影片以列文的一个梦境开头,梦境中列文被一群恶狼追逐而陷入困境,这时他的画外音响起:“我经常梦见自己抱着树枝,眼睁睁的等待死神降临,死时还未懂得爱情真谛,那就比死亡本身更可怕了,在这种黑暗深渊的何止是我,安娜·卡列尼娜也有过同样的恐惧。”由此将他与安娜·卡列尼娜这深陷痛苦中的两个人联系了起来。这很好地贯彻了导演的改编风格,也体现出他对原著的理解与感受。另一方面如此安排也是为了扭转以往的电影改编对列文部分的忽视,毕竟将原著中另外一条平行线索完全去掉,很难说能够完整再现托尔斯泰的作品与思想。噩梦为整部影片奠定了一个悲凉、阴冷的基调。紧接着影片正式开始,画外音再次响起:“在人生的残酷现实中,有位佳人总能令我眼前一亮,她就是施芭斯姬公主。”镜头切换到滑雪场,由此吉提与列文登场亮相。这条线索略作展现后,镜头转向火车站(开启另外一条主题线索),安娜·卡列尼娜与渥伦斯基相遇。列文真实的噩梦到温馨的会面再到安娜噩梦般的真实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该剧在上映时的另一个剧名《爱比恋更冷》也传递出导演对原著的解读中对作品基调的定位。不仅如此,在罗斯看来,安娜与列文还是托尔斯泰的两个自我——“安娜停留于躯体,而列文则停留于哲学。”如此以来,这部作品其实是托尔斯泰的传记。而导演的工作就是完成一次对话,既是与已经成为历史的原作的对话,也是与原作者的对话。
三、从文本到荧幕
文学与影视采用不同的语言符号和叙述方式,如何成功地完成二者间的转换,是决定改编成功的关键所在。托尔斯泰是洞悉人类心灵的艺术家,在小说中有大量的心理独白、意识流程,文学在这一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安娜·卡列尼娜》在描写列文在农庄思考农民和贵族的出路,人生的意义以及大自然的宏伟景象时,用了大量篇幅。改编成电影后,编导充分运用电影的视觉表现力,采用远景、中景、近景外加特写镜头的组合,让列文如老农般在漫无边际的田地里挥动镰刀,之后是长镜头下的列文驻足远望,镜头中人物的状态集中在画面的左下角,画面中大部分还是对一望无际农庄麦浪的描写,加上适时响起的俄罗斯民族音乐式的背景音乐,列文心中的那份恬淡就在这日升日落之间,在原始的自然与天地上很好地表现了出来。此外作品借用画外音,列文在田地里的那段心境独白也自然地刻画出了这个人物瞬间顿悟生死的复杂思想性格。至此原著中的文字符号就很娴熟地转化为了影片中的镜头语言,把这个贵族青年探索人生真谛的痛苦思考过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同原著注重内心世界的探索一样,改编者在人物塑造上,把注意力的中心也放在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上,重在揭示家庭冲突中人物的情绪与体验。摄影师精心拍摄人物的面部表情和眼睛的神态。罗斯认为,人物的眼睛可以表现出隐蔽的激情。因此,《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影片中的眼神拍摄,堪称一绝。安娜与渥伦斯基火车站初次相遇,从渥伦斯基眼中看到的由苏菲玛索饰演的安娜既不失俄国贵妇的典雅高贵与神秘忧郁,也带有法国女人特有的开放与活泼;在火车站,尚未经历人生坎坷的安娜目睹一起工人卧轨死亡惨剧,死者惨死画面深深触动了安娜,致使她在马车上神情呆板,未留意周边事物,近乎惊恐地喃喃自语“不好的兆头”;在公爵家的舞会上,渥伦斯基与安娜共舞,他看着她的眼,她的眼透露给弗龙斯基的是一种“过剩的青春”般的眼神,闪闪的睫毛下映射出按捺不住的火。影片尽管对结构和人物均有所变动,但保持了原著的基本思想和总体风貌。另外,罗斯深知服装造型对于人物情感、心理变化的影响。作为卡列宁夫人的安娜在社交场合以端庄典雅的贵妇形象示人;与渥伦斯基私奔后的安娜一头短发,服装也显得俏皮可爱,这种改变是安娜觉醒之后的心境符号。
四、结语
英国导演伯纳德·罗斯执导的《安娜卡列尼娜》即是在当下语境下对经典的重读,从一个接受者的角度对经典做出的阐释。《安娜·卡列尼娜》从文学文本到电影文本的转换,使其从文学语境的传播深入到文化场域的传播,受众不断增长。电影叙事中镜头之间存在的叙事空白、意义空缺也给观众带来了填补空白的乐趣。“电影提示观众在情节叙述组织以及风格式样化的基础上,去建构不断形成中的故事的过程”3由此,经典改编片的繁荣反之推动了受众群体对文学文本的再次关注。
注释:
1.法朗士.文学渴了·法朗士评论精选集.吴岳添译[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245.
2.罗曼·罗兰.名人传.刘超译[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8:86.3.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诗学.张锦译[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