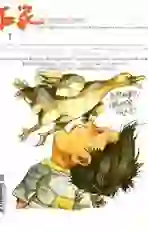洋眼看神州
2019-07-08卢岚
卢岚
一
因为清理书橱,在书堆中看到一部《中国来信》(Lettres de Chine),耶稣会传教士撰写的书信集。封面的洋人清官装扮。当初从书店携回后,又觉得这类“古董”不会给你生息,遂塞到高层架子的死角上,十多年来不曾碰它一下。今回重见于“江湖”,随手翻翻。打开第一封信。现在你在哪里?在中国;什么时候?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但一个中国人去听洋人向你叙述中国,该怎么说呢?康熙时代也远了,都三百多年了,眼下生活何悠哉?部头也大,足有500页之多,小型字体密密麻麻,即便为手头上的小篇章找点什么来填塞,也犯不着去折腾眼球。正要将它“回炉”,忽然看到关于广州的描写。你到底是广东人,就来了一种心情,继续看下去:
当你进入到广州河(珠江——笔者注),就可以看到中国的面貌是怎样的。河流两岸是种植水稻的广阔田野,像美丽的牧场般绿油油,一望无际地铺陈着,其中交错着无数的小水渠,以致你不时远远看到的来去的船只,不像是在水面上航行,而像是在绿草地上行走。远远陆地的山坡,上边种满了树,沿着河谷皆是以人手操作成的景观,像杜热丽皇宫花园的花圃。多少村庄,就错落在多姿多彩的田园环境中,你百看不厌,只可惜船只走得太快。
这样油绿如泼水的故乡,真抵得游子一辈子思恋。这是耶稣教会的神父普雷马尔(Prémare),于1699年2月17日,从广州写给德拉雪芝(de la Chaise)神父的信。由于知识界开始对科学感兴趣,康熙委托传教士白晋(Bouvet)回欧洲招聘专攻数学的传教士到中国,普雷马尔是应聘到中国的教士之一。信中所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印象。珠江两岸的田园景观,在他眼里跟伊甸相去不远。那个年代说远也远,说近也近,但环境变化之大,直教你做梦也回不去了。现在你就借用普雷马尔的眼睛,回过头去看看被高楼大厦,大小洋楼,交错的公路,来往不绝的大小汽车侵占了的地方。广阔的田野失踪了,小水渠没有了,村庄逃跑了……你就从这部沉甸甸的册子去寻旧,去敲敲消逝了的过去的大门。
二
北京的城墙、牌楼付拆之前,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力主北京的新建设以不破坏紫禁城,北京城墙,城楼,以及所有古建筑为原则。并提出一套都市规划方案,在城西建立一个新城。千年旧都,即使在城内起新楼,尽量在高矮方面配合,使其不失原有面貌,做到新旧两相宜。但最终方案条款绝大部分被否决,只接受保留紫禁城。一个美奂美轮的古城建筑,就这样消逝如灰烬。
偶然看到北京城的老照片,会忘情地进入画中世界。原来我们曾经拥有这样的楼阁玲珑,红墙琉璃瓦的故国家园。现在无影无踪了。好东西注定难逃毁灭?教士笔下的文字,给你内心一阵滞重:
那些城门,有些东西比起我们的还要宏大,还要华丽。它们起得极高,将一个方形城区围起来,周围起了高墙,城墙上筑有一座座美丽的沙龙,无论向村野,还是向城市的方向都一样。北京的城墙是用砖块砌成的,高度四十古法尺左右(一古法尺相当于325毫米——笔者注),以20图瓦兹(1图瓦兹相当于1.949米——笔者注)的同等距离,筑有小方塔楼,维修得非常好。好几处地方开了很大的上坡道,以方便骑兵部队登上城墙。
这是法国传教士洪约翰(Fontaney)信中一段文字。城墙状况与外貌,是1688年3月21日他眼知眼见。墙高四十古法尺,相当于四十三英尺,没有提及宽度,只说上头有一座座美丽的沙龙,即房屋,是各种活动的场所。其宽度给你无穷想象。且辟有上坡道,骑兵部队可以登上城墙。一队骑兵有多少?二十骑?三十骑?并排能走过多少骑?十骑?十二骑?当年林徽因的设想是因地制宜,将城墙改为环城公园,一定距离的路段筑梯级,逢交通要道开凿通道,方便车辆通行。城墙上栽花种草,放置长椅,给市民提供休憩娱乐场所。从保护文物,审美角度,或实用上的灵活变通,不能有更好的设想了。但上下缺乏共同思维。夫妇俩到处游说,写信求助,细说利害关系和变通办法,直至声嘶力歇。拆毁工程始于1953年,从拆牌楼开始。积淀了近千年的华夏文明的建筑物,象征民族灵魂的古物古风,如果毁在外人手里,我们骂上三百年不觉得累。
三
康熙治下的六十一年,被认为是政治清明,生产力稳定,文化事业有相当成就的年代。《康熙字典》的编纂,历时近百年的《明史》修撰,为后人乐道。鉴于历代修史者总是讥笑贬斥前朝,歪曲史实,既失公平,也失信于后人。康熙態度客观,要求编者立足于事实,着重良心,采纳公论,明辨是非,务使人心信服。并亲自过问明史的编纂。他平定江山后,好学而自律,思想灵活,见识过人,狄德罗把他比作古罗马和法国的两位贤帝:“从智慧而言,他是中国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从专制政治和统治时间而言,他是路易十四。”他充满信心,信心使他胸襟开放,对外来的传教士不乏宽容。17世纪末在京的传教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德国的汤若望(Schall),荷兰的南怀仁(Verbiest),都隶属于以国王名义主持的葡萄牙教会。到康熙时代,法国才有一个传教士组织在北京成立,起了教堂;他治下中国有115000教徒,159座教堂。1688年南怀仁逝世,康熙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
1688年3月11日,晨早七时,被恩准参加葬礼的高官抵达现场,洪约翰则以教士身份应邀出席。他看到一副巨大的厚达四英寸,外面上了釉彩,漆上金色的棺木,连担杠一起,放在大街上一个装饰极其庄严华丽的白色圆顶帐下。六十至八十人分别站立两边,出殡时用肩膀抬起棺木。教士当街下跪,行叩头礼,教徒高声痛哭。身穿白色丧服的官员端坐马背上,队伍起行时,皇帝的岳父走在最前面,跟着乐队和送葬队伍。一个高25英尺,宽4英尺的木牌,上头画着南怀仁的遗像,和漆金的中文名字。手持圣母像,耶稣像,洋烛,长条幡旗和燕尾旗的低级官员,和教徒队伍,浩浩荡荡,由五十个骑兵组成的队伍从两边框起来,向坟场走去,那里已经安葬着利玛窦和汤若望。人头攒动的市民,站在街道两旁,鸦雀无声,看着队伍走过。
洪约翰以两页纸来描写葬礼的中西合璧。其隆重奢侈,繁复细致,皆出乎想象。南怀仁虽然职拜大清钦天监监副,二品官,以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身份为朝廷服务,但毕竟是外国传教士,为他举行一个基督教色彩浓厚,震动京城的葬礼,必须具有足够的开放精神,坦荡的胸襟和高度自信。
其实早在1692年,洪约翰和刘应(Visdelou)两位教士,以金鸡纳霜为康熙治好了疟疾。康熙投桃报李,在皇城范围内皇宫附近的北堂,为传教士们起了面积宽敞舒适的花园寓所,同年颁布一道容忍传教活动的法令,这是传教士活动的黄金时代。能操满语和汉语的巴多明(Parennin)神父,颇得康熙和高层官员的信任,容忍他为苏努皇子及其家属施洗为基督徒。1722年康熙弥留时,希望会见传教士。离世前表示这种不寻常的愿望,耐人寻味。有意临终前受洗?但他身边的人拒绝让教士进入皇宫。巴多明在通信中表示十分遗憾。
四
到雍正登基,对传教士的态度与前朝大相径庭,敌意代替了尊重宽容。原因何在?反正事情闹出来了,受洗的苏努家族首当其冲。因受洗被迫害?不完全是,主要是苏努家族中的皇子有资格跟他争皇位,对他的权位有威胁。他虽然已登基,为巩固权力,对皇兄弟大肆残杀,迫害。其手段的残酷,冷血,使中国人发怵,也使欧洲人震撼。在京生活了40年,逝世于北京的巴多明,有12年时间,以每年或每两年一封的书信,将满洲皇族受迫害的事件详加叙述。
康熙子嗣众多。晚年见诸子争位,预感到会骨肉相残,深感不安。雍正即位后,果然为保权而操刀忙。雍正登基,疑点太多。“谋父”是嫌疑,而弒兄,屠弟,是大家眼见的。十多个兄弟中,或被投入监狱,或幽禁于府邸,未满15岁者,驱散到外地,贬为庶民。在位13年间,幽禁于咸安宫的二哥礽,死于雍正二年;禁于永安亭的三哥祉死于十年;五弟祺死于十年,七弟佑死于八年;廉亲王八弟祀死于四年,九弟唐死于四年,十弟被囚,直至乾隆二年才获释。之前大哥幽于府第,死于十二年。亲子弘时,因不满其父对兄弟的残杀,也被革去黄带,除名《玉牒》,革去宗籍,交给他视之为敌的八弟祀进行“约束”,雍正四年,在生死无人过问中去世,时年二十二。没有文献足以证实雍正亲手杀子,但父子关系恶劣有文为证,雍正曾有谕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廷。是以令为允祀之子……”从他对兄弟、亲子,和异议者的杀害,可以反证他的皇位来路不正。权力一旦失去合法性,就以屠杀、暴虐、压制作为统治手段。王权掌握了人的生死大权。但手握大权者下场又如何?雍正死因不明,成为历史谜团。历史上这种谜团俯拾即是。
八弟允祀,表面封为廉亲王,四大总理事务大臣之一,但很快被找岔子,指其“怀挟私心”“无功有罪”“存心阴险”“不忠不敬”,而被锁拿。九弟禟为人大气,善经商,积聚了大量钱财,经济实力雄厚,却是个明白人,声言不恋帝位,宁可出家:“我行将出家离世。”他才德兼备,受群臣爱戴,反而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罪名是,康熙去世那天,允禟突然来到他跟前,傲慢无礼地坐到对面,“其意大不可测”。遂革其黄带,削宗籍,加28条罪状,三条铁链锁拿,以木头车发配青海,在老苏努死后被抓回监禁保定。直隶总督李绂接到犯人,深谙皇意,以小人嘴脸说:“等塞思黑(即狗,不要脸)一到,我即便宜行事。”所谓“便宜行事”,就是把允禟囚在四面高墙,手脚难以伸直的囚室内,再三条铁链加身,在暑热如焚中死去。却称:“腹疾卒于幽所”。传被毒杀。
同时获罪的八弟允祀,也在狱中受尽折磨,允禟死后不过十天,也去世了。雍正还斥责两兄弟“罪恶多端”“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雍正帝”。如有人到灵前哭泣或叹息者,拿问。密奏。
1725年7月20日,雍正三年,巴多明给欧洲一位教士的信:
我去年寄给你的详细讯息,相信你已经整理好,那是关于在有血缘关系的皇族众多家庭成员中,所取得的宗教信仰的进展,以及关于皇子们带着天主的慈悲,他们还是新近受洗的呢,去面对失去尊严,被判处严峻的流放。但你可能焦虑不安,想知道他们是否以最初被贬谪时候的同样热忱互相支持,如果继续受苦受难,会否动摇他们的勇气。不,尊敬的神父,这些出色的新皈依的教徒的德行完全没有动摇。
由巴多明为他施洗的苏努,当时已77岁,作为皇室的族老,每天到皇宫早朝,参加公众仪式,平日在家料理家务,却别有怀抱,追求精神生活。从和尚道士的作品中寻找精神粮食,希望过有异于世俗的生活,但徒劳无功。偶然在书摊上找到一本《论人的灵魂》,巴多明著。回家細读,内心被激活了。遣仆人到天主堂,携回一大堆免费的书籍和小册子,于是,在情在理地受洗为基督徒。巴多明与皇室关系密切,了解情况较多。雍正残杀兄弟,为的是保皇位、保权力,他应该很清楚。但他从宗教角度来反映这件事,写道:“皇帝对他所憎恶的教徒皇兄弟进行迫害”,着意指出教徒身份是受迫害的原因,一再颂扬他们坚持对天主的信仰。欧洲信徒得到讯息后,大为感动,庆幸传教士活动的成功。在他笔下,经他施洗的老苏努、允祀、允禟及其家人在流放途中扶老携幼,妇孺蜷缩在简陋的木头车上,承受着流离颠沛风雨交加,极度艰苦的非人生活。但天主与他们同在,坚强信念使他们无怨无悔。流放途中的详细叙述,恐怕不会在中文文献里找到。讯息来源呢?巴多明在信中说明,都是朋友或仆人的所见所闻,并以直接口吻叙述。主要来源是交往密切的教徒,他们从皇子们的流亡地回来,其次是皇兄弟们给他写的信件,以及苏努家中受洗为教徒的仆人。有感于主人的恩惠,当皇子们落难,秘密地给他们帮助,带信,提供金钱和生活必需品。雍正到处布下密探,有人一进入北京即被捕下狱,审讯过程中,甚至牵连其他人。下面是流放地Fourdane一位居民的叙述:
看到皇子们悲惨遭遇的场面,真叫人心酸。没完没了的雨天将整个流放队伍打得七零八落。有的被迫付出一年的租金去租房子,流放者被趁火打劫;有的自己出资起屋,即将起好时,又被迫放弃一切,突然要他们撤离,有的走路,有的骑马,妇女和孩子们乘着破烂的木头车,向沙漠走去,那里没有牧场饲养家畜,没有木柴烧火,寸草不生,泥沙滚滚,想找地方起两间茅舍,业主要他们付出天价。
为对付政敌和仇人,雍正实行特务统治。流放队伍落脚的小城的所有城门,都贴出告示,严禁所有满洲人,蒙古人,满洲化的汉人到苏努家的茅舍,违反者抓捕送京,作谋反治罪。在极度艰辛、匮乏情况下,皇子们没有抱怨,作平常日子过,因为有天主作为信念。年近八十的老苏努,为引导家人受洗,被判一起流放,到底经不起折磨,流放中去世。随即,允祀,教名Louis,允禟,教名Joseph,在一道皇令底下,被押解回京城入狱,每人身加九条铁链,很快在狱中折磨致死,可能被杀。残酷、冷血的雍正,谋父,杀兄弟数人,欲盖弥彰,自称不辩亦不受。清史专家评曰:“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储棋局可能将具有永久的魅力,它薈萃了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精华。”
巴多明对皇室冤案的反映,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但在同一事件上,同时研究中国问题的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两人态度截然相反。孟德斯鸠第一个认为,这是中国的无可辩驳的暴政的表现:“巴多明神父的关于皇帝对他所仇恨的皇族教徒的迫害的信件,使我们看到一个连续不断实行的暴政计划,并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即以冷血,来向人类进行侮辱。”但伏尔泰却说:“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招致了几个中国人的死亡,尤其是招致了支持过他们的两位血亲皇子的死亡。从世界的另一端,跑到一个皇族家庭去制造混乱,导致了两位皇子受尽折磨死去,不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吗?”
法国的哲学家当中,最欣赏中国的,无可置疑是伏尔泰。在他的作品中,中国是无所不在了。在戏剧方面,他把《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剧院上演时,采用了中国服装和道具,大获成功。小说《巴比伦公主》也别出心栽,让公主去到康巴闾(北京),既看到人口众多,也见到彬彬有礼的清廷官员,看到什么叫艺术品位,什么叫奢侈。在那里,有一位躬耕的皇帝,为子民日夜操劳,为人公道,充满智慧。在《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中,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经济,政治,文明,科学,艺术,宗教,都是在中国发展起来,取得辉煌成就的。1774年发表的抨击百科全书的文章中写道:“将中国人置于地球上所有民族之上的东西是,无论法律,风俗,文人所使用的语言,在将近四千年间,都没有改变。”四千年不变,可能吗?还有进步可言吗?又说:“在我们学会了其中某些东西以前”,中国“创造了几乎所有艺术。”他在中国找到一个理想政府,就像西方当代的君主立宪,皇帝与国家的整体代表势力,联起手来进行统治。用现代语言就是,皇帝跟民选的议会共同治国。
伏尔泰对中国的大肆恭维,所倚重的都是传教士的通讯资料,尤其是出自于殷弘绪(Entrecolles),巴多明,博须埃(Bossuet)。他们首先发现了中国的古老,古老得使西方的历史变得可笑。从编年学的观点来看,《圣经》也变得可笑了。伏尔泰骨子里是反宗教,反《圣经》的。中国的历史比《圣经》的历史更古老,他的“反”就有立足之地。那个时代,西方人认为《圣经》追溯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故事。但是,当传教士们接触到中国文献,发现古代中国可以回溯到更古老的年代,可以从书写文献和天文观察文献中得到证明,如月食。如果说中国人是诺亚方舟人的后代,中国的编年史就可以回溯到公元前2952年,比起西方公认的洪水期早了600年。这个发现在欧洲引起的后果是,《圣经》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的记载是正确的。尤其是天文计算日期的准确,那么《圣经》所记载的古老世界,就必须往后推,以便跟中国的编年史相吻合。这也必然引起一连串问题,古代中国人从何而来?埃及人的后代?诺亚方舟人的后代?
再没有比启蒙时代的欧洲人更关心中国的了,不管对中国的了解是否正确。东西方路远迢迢,一趟水路动辄半年。狂风,暴雨,浪大如山,疾病,此中艰辛唯亲历其境者自知。当时没有技术条件获得中国讯息,没有字典,没有翻译书,没有翻译人材,没有直接传媒,传教士书信成为主要的讯息渠道。而教士各人的学识、思考、观点,也影响着对客观事物的理解。隔阂,曲解,变形都可能。他们眼里的中国不可能都一样。有大肆颂扬的,有态度保留的,或贬斥的,有为投合欧洲人的好奇心而着意落笔的。教士所提供的讯息参差错落,但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只能依赖他们了,选用资料,就看你偏向哪一位。所以18世纪的欧洲,对教士的书信满怀热忱,也采取批判态度。对他们反映的同一事件,经常作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传教士的书信,首先成就了伏尔泰的《风俗论》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
孟德斯鸠资料的来源,最初也是传教士,尤其杜赫德(Halde)。这位教士汉学家对中国基本肯定。开始时候,孟德斯鸠也相信,清廷这种家长制的社会制度,是被法律、风俗、传统限制着的,权力被削减了,尤其欣赏其农业政策。后来遇上大名富凯(Fouquet)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后,离开中国,也离开了耶稣教会。他向孟德斯鸠表示,对传教士的所谓“书信”,必须有所保留,中国并不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此外,孟德斯鸠也参阅了《从兰格到中国之间的来往》,这部著作由海军司令安森(Anson)口述,瓦尔特(Walther)执笔,安森是彼得大帝手下的一位瑞典工程师,他对中国商人提出严厉批评。从此,孟德斯鸠改变了态度,站到相反立场上。后来在《论法的精神》的第一部分,论述了三权分立后,以整整一章来谈论中国。他十分遗憾地发现,在传教士所反映的中国政治模式中,找不到他毕生探索的理想政治。他发现传教士陷入了颂扬家长制的陷阱,跟他所提倡的理想政治毫无一致之处。在《论法的精神》的第八卷第二十一章中说,他没有发现皇家的值得尊敬的荣誉,也没有发现民主或道德。谈到王权治下的中国人,他说:“我不知道大家所谈及的所谓荣誉,除非给他们棍棒齐下,不会有别的。”结论是,雍正统治下,“中国是一个以恐怖手段统治的专制国家”。专制体制的原则就是恐怖。“一个极度渴望权力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己之私,绝非国家利益。”《论法的精神》第八章如是说。
五
江西景德镇瓷器制作的揭秘,在传教士书信中,是苏努受迫害事件以外的另一件大事。1557年葡萄牙租借澳门,作为商船的中途落脚点和仓库。当他们把丝绸、漆器、玛瑙、水晶、珊瑚运到欧洲的时候,顺便带去一些瓷器作为试销品,想不到有马到成功之效。欧洲皇室视如珍品,贵族争相购取,瓷器之路一下子打开了。十七世纪末,当“安菲特里特”号帆船将巴多明神父送来中国,回程时携回瓷器共181箱。目前欧洲保存的最古老的一件中国瓷器,是1541的产品。当瓷器大行其道,欧洲人自然希望知道制作的秘密。那个时代没有专利权,没有技术保密,但两国之间路途遥远,民众没有来往,只有传教士能获得制作秘密。殷弘绪是里摩日人,1698年到中国,有十年时间在景德镇传教。经过长期的观察、了解,向教徒工人了解情况,并参阅中国书籍,1712年,以第一手资料,写了两封长信给奥尔利神父,详细而准确地描写了瓷器的制作过程。两年后在法国公开发表,瓷器制作秘密终于揭开。原来关键在于从景德镇山头上开采的黏土,称为“高岭土”,掺水变成胶状,焙烧后坚硬洁白。它跟另一种具可溶性的“白丘”长石,经过捣碎混合使用。两封信成为欧洲人了解瓷器的重要文献,被各方面不断引用,收录到《百科全书》里。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利用信中所提供的数字推算人口,认为当时景德镇人口超过一百万。
那个时代,法国没有大型工业,没有工业中心,殷弘绪介绍了一个百万人的工业城,一万八千户人家,操持着家庭式的工场制作,三千个瓷窑终年不熄地燃烧,连锁性的手工业活动,组织严谨的,比西方超前了数百年的流水作业,使欧洲人震撼。景德镇面临昌河,河流上排列着大小船只,活动频繁,有的将烧好的瓷器运走,有的将高岭土与“白丘”混合打成的砖块运来。景德镇不生产瓷器原料。白丘是石块,必须预先捣碎,上头布满发光的微粒;高岭土则不用敲打,加水即溶解成胶状,细腻,呈白色。经过一连串加工,才打成瓷坯,涂上各种颜色的釉彩,或手绘花鸟、人物、风景,送入瓷窑。火路调节是大学问,瓷窑以木柴作燃料,不同瓷器要求不同的焙烧温度和时间,没有测量仪器,时间掣,温度计,一切就靠实践经验。一连串的操作,紧凑,准确,不能有任何延误。日间到处升起烟与火的旋涡,将景德镇的范围标志出来。入夜,像一个巨大的燃烧着的火炉,远远望去,整个城像闹火灾。房屋密集,街道狭窄,柴火不易控制,火灾经常发生。不久前烧毁了八百间房子,泥水匠和木匠很快着手重建,再投入生产。殷弘绪对手工业者承受的煎熬感到不忍,认为景德镇是工业地狱。到19世纪,类似的地狱也在西方出现了。
六
莱布尼茨(Leibniz)说:“我认为今回的传教活动(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是我们的时代最大的一件事,无论是荣耀天主……和对人类的总体利益和科学艺术的发展,于我们和中国人都一样;因为这是一种启蒙的交流,数千年积累起来的经验,反手间给了我们,而我们的也给了他们,这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大事。”
文艺复兴时期的传教士知识渊博,是教会的精英,也是社会的精英。当时贵族阶层奉行长子出家的习俗,许多教士出身贵族之家。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信念,宁可放弃舒适的生活,扬帆东渡,先去承受海上每分钟都是死里逃生的历程。使命感使他们大无畏。每一种职业的人都有使命感。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沙勿略(Xavier),就希望天主的福音能抵达亚洲。他出身贵族,与国王结下深厚的友谊,34岁即以“教皇特使”身份,独自一人启程到东印度,在印度,锡兰等地传教,再转到马六甲、日本,然后企图进入中国,未竟,1552年逝世于广东沿海的上川岛。到葡萄牙租借了澳门,传教士到中国的门户随即打开,最初只限于在澳门传教,后来逐渐北上。
传教士到东方传教,中国文化史上是大事,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大事。唐僧将佛经从印度携回,是采购,基督教是外卖,由传教士亲自送上门,来自大西洋彼岸,很远。开始时候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难以避免;成见,误解,敌意,非我族类之间的抗拒,甚至被指为侵略行为。传教士只能以个人的方式方法活动。深知要达到传教目的,必须进入到最高的权力机关:宫廷。一旦进入,就以天文、数学、物理、机械、自然科学、绘画的知识,使中国官员,直至皇帝产生好奇心。利用科技为信念服务。于是带来天文望远镜,天文圆规座,日晷,自鸣钟,教他们使用。欧洲的科学知识就这样进入中国。路易十四的城市规划图也给带了去,向清朝官员展示。千辛万苦扎下了根。“泛海八万里,而观光上国”的利玛窦,深知要达到传教目的,不但要走上层路线,跟知识界建立友谊,跟皇帝打交道,还要适应中国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无视他人的文明,则无法推行传教事业,他说。他用中文写下了《交友论》。还要心灵手巧,懂得制作钟表,用威尼斯玻璃制成三棱镜,用一块黑色石头制成日晷,为皇帝和皇室人员画像。都还算不了什么,还要懂得编写历书,择吉日,计算闰月、春分、秋分,预告日食、月食,稍有差错,失信于朝廷,后果严重。有的教士是建筑师,广州最华丽的教堂,是传教士图尔科蒂(Turcotti)所建。战争时期,还要懂得铸造火炮,汤若望就在崇祯促使下参与了火炮的铸造。他们进入上层社会,直至朝廷,并不是因为传教士身份,而是科学家的身份。利玛窦被写入《明史》,是作为天文学家,历法学家,侍奉于明﹑清两个朝代。日后传教士所选择的,都是利玛窦的路线。
但从利马窦到1949年四百多年历史来看,教士们的传教业绩并不辉煌,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传教是初衷,活动过程中,不知不觉成了文化使者,从欧洲到中原帝国之间,起了一道文化桥梁,让东西方文明接触,互相惊叹于对方的文明。中国人惊叹于西方的天文望远镜、日晷、自鸣钟,西方人则惊叹于中国的考试制度,园林艺术,物产丰富。但欧洲人大抵认为,由于失去了这批科学精英,影响了欧洲的科技发展。现实喜欢作弄人,你等的人儿没有来,不等的人却来了。
七
《教士书信》供你寻旧,满足你对过去的好奇心。广州街道狭窄,铺着凸凹不平的大石,几乎不能使用马车,付出小小费用即可租用轿椅。房屋低矮,都用作铺子。独立的房子没有窗,以竹编的栏栅作门。很少女人出现。蚂蚁般走在路上的男人,头、脚光溜溜,大部分肩上负着重荷,没有工具可将出售或购入的物品搬运。
官员的府邸就不一样。不知要通过多少个院子,才能抵达召见同僚或朋友的厅堂。官员出门阵容可观,总督(两省总督)不会少于一百人护驾,整队人马井井有条。身穿制服的人手持各种徽号走在最前面,跟着大群徒步行走的士兵,官老爷坐在一张很大的,金光耀眼的椅子上,让六至八人扛上肩头,高高抬起走在队伍中间。出巡占去了整一条街,民众站在两边观看,尊敬地停下脚步,直至队伍走过。
安徒生的童话《夜莺》,说中国的御花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奇花异草,珍禽鸟兽,面积无尽地伸延到海边。安徒生的灵感来自于乾隆宫廷画师王致诚(Attiret)笔下的圆明园?现在御花园已成废墟,王致诚笔下曾是人间天堂,他说:“当你看过意大利和法国的宏伟建筑和大楼,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一切你会漠不关心,或瞧不上眼,但北京的皇宫和离宫是个例外。”王是乾隆从法国聘请到北京的画师,属耶稣会。1739年,从澳门乘船到北京,作为宫廷画师入住圆明园,在乾隆身边生活了30年,跟着乾隆跑遍帝国,画下百多幅皇帝肖像及战争场景。但拒绝接受封官,逝世于中国。1743年,他从北京寄出一封信,详尽地描写了圆明园的环境和园内生活。1749年第一次发表,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中国园艺给欧洲,尤其给英国带来新观念,英式花园从此产生。原来中国园艺是反对称的,不规则的,是看不出其艺术的艺术:“这里展示的是一个乡野的自然世界,一种孤寂,而非对称和比例规则上井井有序的宫殿。”御花园的建筑物散落在无数小山丘的山谷之间,山丘以人工堆成,其中大小运河,湖泊,池塘,海,纵横交错。大小宫殿200座,每座由一个太监看守,在屋旁筑小室居住。王致诚认为圆明园不会小于他的出生地多尔城。但偌大园子只属皇帝一人,只有皇后,各级嫔妃,太监和宫女在里面生活。皇子和大臣,只在听政厅见面,极少引进到别处。天子在园里只是个囚徒,住所周围绕着又深又阔的运河,形成一个孤岛。一旦出门,数小时前清理环境,肃静回避。为阻挡视线,周围严密地拉上幕布。偶或到鄉村,两列骑兵像两堵墙,远远走在前面。所有欧洲人,画师,钟表匠,都集中在园里,方便工作,但不能在里面过夜,晚上返回附近教堂。乾隆每天视察工作,以致他们没法缺席或偷懒,却有机会走遍花园和宫殿。参观时由一群太监带领,走路得轻手轻脚,像小偷。有一回,乾隆请他们在园子里吃晚饭。每天见到皇帝,是中国人不敢祈求的。他们工作繁忙,只能在星期天和节日向上帝祈祷。乾隆每年在园里生活十个月,御花园离北京不远,大概是凡尔赛宫和巴黎之间的距离。
八
一个三四百年前的中国朝廷,里面混着深眼钩鼻的洋人,非我族类,却身穿官服,为朝廷服务。名字不叫Jean、Francois,而叫刘应,王致诚,白晋,跟中国人一样中国。可见世道的安稳。且不管他,你只满足于在书信里回到三数百年前的故乡,登上北京城墙,游圆明园,到景德镇,当你掩卷闭目养神,却被一些问号留在了那里。洋清官头顶是否盘着辫子?普雷马尔说广东年产三造米,在哪个山旮旯?法国教士龚当信(Contancin)详细地描写了雍正扶犁,为表示重视农业,祈求风调雨顺农作物丰收,从初春二月中选择吉日,亲自下田开犁。仪式前三日,斋戒,节欲;在皇室中选德高望重的长者,到祖庙向祖先牌位禀告;开耕礼由三位皇子九位族长陪伴,选四十或五十位出色的老农出席典礼,又选四十位年轻农夫来装置犁耙,将牛套上。皇帝开犁之后,皇室人员跟着扶犁,并在田间扎帐让皇帝午餐。最后由皇帝撒下五谷种子,稻谷,蜀黍,稷,高粱,蚕豆。皇后则到民间中去织布。这些描述使欧洲人醉倒。被誉为“欧洲孔夫子”的魁奈(Quesnay),甚至奉劝路易十五以雍正为榜样,开春时也来一场开耕仪式。
皇后到民间去织布,史书似未见记载。雍正二年首次举行“籍田”礼,四年指示各级官员置“籍田”。天子籍田千亩,诸侯百亩,都是征用民力无偿耕种,“籍田”越多,农夫负担越重。所谓“籍田”开犁,只是天子或诸侯,手执耙子在籍田上三推或一拨,象征性地表示对农业重视。孔唐山笔下的多姿多彩,资料从哪来?法国博物学家索内拉特(Sonnerat),18世纪下半叶到访过印度和中国,他很不客气,给这个形象泼冷水:
当皇上走下皇座去扶犁,之前,所有一切都白纸黑字先写了出来。他们大肆宣扬这个徒劳无益的仪式,就像希腊人对塞雷斯(农业女神——笔者注)的肤浅崇拜。由于治国不力,导致千万中国人成为饿殍,卖儿鬻女。实际上是有可能保障他们的生活的。
教士探究中国的史实,有时也陷入思想的因循。尤其涉及判断或结论,经过观点或情绪的过滤,或文学润饰,以致跟事实产生距离。所以,瑞典工程师安森,博物学家索内拉特都指出,教士们生活在深宫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对中国的认识有限而表面,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中文的钻研,和科学知识的使用上。利玛窦和汤若望都能用地道的古文著书立说。雍正迫害事件,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作出相反结论,资料的选用是原因之一。伏尔泰也翻阅中国书籍,但他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他所找到的,恐怕是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和皇帝。将一个远古的,可能是传说中的理想国度,放到一般的历史范围里,这可不是历史,而是文学。
横渡大洋,经历险象环生的海上之旅到中国的商人,为的是图利。传教士呢?为的是传教。冒险精神来自于信念。更严峻的考验是,单枪匹马去到一个不理解“以善报恶”的“异教徒”国度,必然会遇上的灾难和危险,这个他们知道。孤独无奈也会浮上心头。在韶州遇袭受轻伤的石方西神父逝世后,利玛窦哀叹发愁:“我在这片沙漠中失去了我唯一的朋友,他曾经是我沙漠中的绿洲。在这周围都是异教徒的人群中,我再一次感到寂寞。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何以解愁?唯有科学知识,以它来引人注目,借此在知识界和宫廷中逐步扎根。后来《明史》记载:“万历中西洋人利玛窦制浑仪、天球、地球等器”。这与原来的本心错了位,也只能这样了。那时候,宗教与科学并不对立,两者的发展并驾齐驱,只要你懂数学,懂天地万物存在的理由,就会理解宗教。汤若望在中国的著述中,关于宗教方面的书籍很少,只得几种,自然科学则比例较多。在《主制群征》中,如是解释自然规律:“环宇中物,无一无为者,亦无一乱为者。虽体势性情,种种殊异,或相克相伐,然即此相异相克,而公美正赖以成,匪直无损于大成而已!”他通过自然现象和事物为例,证明一切皆是造物主之手所安排。莱布尼斯就坚持以科学来证明信仰。
都说传教活动在中国进展过慢,汤若望自述:“若望谈道之名,反为其历学天文所掩”,其他教士何尝不如此。既然自然现象是天主向人显示的宗教真理,教士们就不曾迷路。当年利玛窦与三淮和尚辩论,最后一句话是:“我今天不是依据权威经典来跟你辩论,而是依据道理来与你辩论。”选择“道理”作为立足点,将宗教撇过一边,所谓持守公理,莫过于此矣。
唯是自利玛窦开始,到后来两个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对儒教的妥协让步使人费解。利玛窦是有意识地被同化的:“我已经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儒教着重现世的道德,重点在此岸而非彼岸,这点他们深知,但,既然儒教的天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权宜一下,大家的观点就基本一致了。利玛窦说,看过中国的圣贤书后,发现没有什么是跟启蒙思想相矛盾的。他的弟子特里戈(Trigault)还说,孔夫子的门徒所倡导的都很恰当,跟我们心中的光明是一致的,与基督教的真理是一致的。果然是这样吗?陷害汤若望几乎致死的小人杨光先有两句话,暴露了他的无知,但可以拿来作为话题:“耶稣既钉死十字架上,则其教必为彼国所禁,以彼国所禁之教而欲行之于中夏,是行其所犯之恶矣……”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分裂出来的,因教义分歧,耶稣被祭司长彼拉多判死罪,钉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罪名是“叛国”,“妄称上帝之子”。加略山目睹了人类的大恶。耶稣一身背负了全人类的痛苦。但经过百年与犹太教的逐步远离,基督教酝酿出自己的信仰中心,产生了《福音书》,宣扬救世。从《马可福音》发展为《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最后到《约翰福音》,基督教的道德训诫基本形成。提倡“爱”,“律法是一切道理的总纲”。“爱你的敌人”,你就没有敌人了。“抛你地上的财,积你天上的财”,重点放在彼岸而非此岸。耶稣之死,演变成救赎性之死,“上帝之子”为人类的罪恶进行救赎,让十字架上的痛苦不再重现。以善报恶,慈悲容忍,成为基督救世的本心。骷髅地上的大恶走出了死胡同。
韩非子有谓:“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西方的现代文明就这样“受事”,发展起来了。你在欧洲行走,到处可见塔尖高耸的巍峨教堂。人为神比为自己创造更起劲。精雕细琢,比皇宫造价要高。墙壁满布历代名家的壁画,以形象来抵达信念。教堂成为西洋画蓬勃发展的地方,不少伟大画家从教堂的宗教画起步,如米开朗基罗。雕塑、文学、艺术、哲学也被带动起来了。精神变物质,19世纪的欧洲静静地织造着财富和现代思想。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的西方文明。而两千多年来,星移物位,沧海桑田,自然和社会都在不断变化,唯有儒学没有演进,没有发展,始终读圣贤书,立修齐之志,君臣父子,忠君孝道,君臣伦理大义,从古到今一贯制,依旧是官场哲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利玛窦会看不到这点?但他却说,基督教与儒教是相一致的。
设想孔子生活于现代,会说“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类蠢话嗎?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在女权时代,想找死不成?聪明如孔子,一定会懂得与时俱进,许多话都不会这样说。是我们过于执迷。子曰诗云,使用起来太现成,太方便,免去了我们的思考。世代因循,永远保鲜,永不过期。金科玉律变成“十面埋伏”。我们裹足不前。博学而聪敏的利玛窦和教士们,也许过于热爱中国文化,自觉地被中国人同化了,就按中国人的思维来思考,来说话吧?
2018年10月
责任编校 谭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