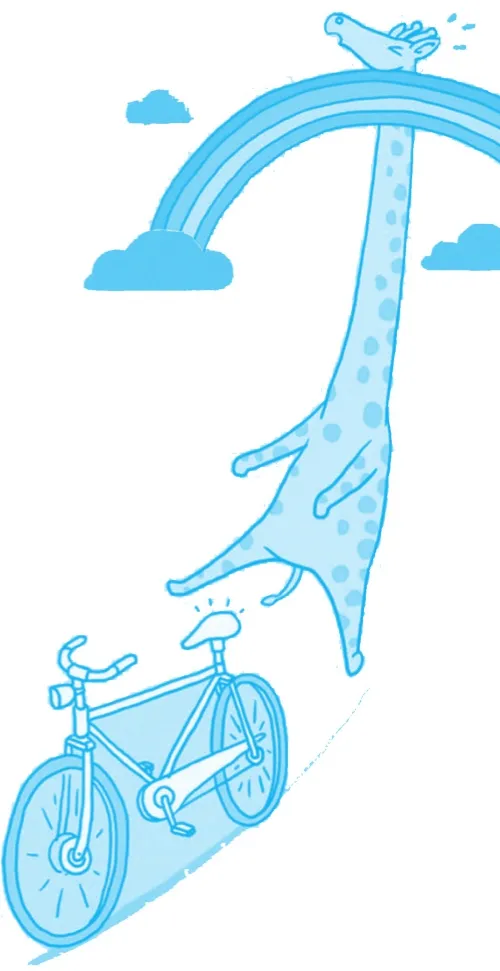少女何吖卣之曾女
2019-07-04徐社东
◎徐社东

艺体节文艺汇演那天,我们早上7:50就要赶到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邵逸夫多功能厅。七十多个班级,几千名学生,浩浩荡荡地排出了长龙阵,全部步行,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们把教工路、文一路、文二路、学院路、黄龙路、西溪河下,所有的交通都堵塞了。
那天,我们班的梅子是主持人。她早上6:00就到校,化妆、准备好后,我们班的合唱演员才到达演出现场。
曾女拉着我走到了梅子身边。梅子对曾女说:“说实话,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紧张。不过还好,不影响我主持。”我们看着梅子化妆以后的样子,很羡慕她。她落落大方,楚楚动人。
时间掐得很准,8:30时,舞台灯光一下亮了。我们也赶紧退回到自己班级的座位那里。曾女拿起望远镜,看着舞台上的梅子。从几个漏出天光的地方,很多浙大的学生也涌进来,看我们的演出。我们的演出说不出有多精彩,但每个班的文艺尖子还是出了风头,并被我们大家所熟知。我们像记住流行歌手的名字一样,记住了他们的名字。那天学校请来的浙江京昆剧团的表演真的很精彩。舞台上,有一个贼在一个夜晚,进入到一个人的家里,和人摸黑打斗。两个人极其搞笑,钻桌子,钻板凳,打错方向,东摸西找,乱打一气。最后,临到我们班的合唱队上场时,我有点紧张。但曾女说,我一看到前面亓亓的头花,顿时就感觉气氛亲切。我的紧张也荡然无存。
整整一上午,演出圆满地结束了。我们排队步行回校,偏偏那时下起了雨。我们学校一共有三个校区,现在分成了三路,向三个方向像游龙一样地走去。为确保安全,也保持班级管理的稳定,老师不准我们坐公交车。其实,我们许多人都有公交IC卡。我们步行从黄龙体育中心那里绕,学校在各个路口都安排了老师值勤。
雨把我们淋湿了。
“我现在是清楚两万五千里长征有多难了。”吕品说。
我手里撑着伞,但是那伞真的不管用,我的身上都湿了。我们不是把伞打在头上,而是举在天空中。这么多人一起排队冒雨走路,本身就是一件很让人兴奋的事。
肖雅皮故意让他的雨伞一个拐角的水流流到了我的身上来。我说:“好,就这样,这样爽!”他放过我,去浇灌别人去了。
到了文二路,又到了教工路,我发现曾女也掉队了。
不过,我很奇怪,曾女的身上居然一点也没湿。
我惊叹,对大家说:“喂,你们看曾女,她太了不起了,她的身上一点也没湿耶!”
张老师在陪曾女走路。
我们都奇怪死了,是张老师为曾女打伞,不让曾女淋一滴雨水,而时老师走在张老师的旁边,帮张老师拿着一只包。我们班上许多人都奇怪,为什么曾女享受了王母娘娘的待遇,连玉皇大帝都给她打伞?
曾女写了一篇名叫《我感冒啦!》的作文,完全文不对题。
每次作文都是这样,总有人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但这并不影响我的阅读。并且,我发现,凡是敢于走题的,都比较有趣。
真的是伤心太平洋。已经有二百年都想生病的我,竟然在不是流感的季节里感冒了,不像话,都快过年了耶!
扫兴!感冒!好讨厌的事。鼻子整天不停地吸,累!而且不一会儿就来一个“冷战”。哎……感冒的事可不能让老妈知道,要不然麻烦可就多了,一要吃药,二要早睡,三要讲究饮食,四还有什么的,五不能上学,所以,一定要保密,不能被察觉。
原本春光明……什么的,这个字我不会写了,就算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吧……(来了一个“冷战”,打断了)……可怜,刚才我在想什么,也被一个“冷战”打断了。……以前总以为感冒不是坏事,根本不知道它的恶劣程度,现在知道了,不是时机呀!这一段时期,《流星花园》漫天飞呀!F4更是火得发紫又发亮,市场上更是多了一些东西,都是有关F4的,这样的情况也就像是流感一样,从港台传到了内地,使少男少女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娘大妈们都感冒了。道明寺、花泽类、西门、美作、杉菜,他们的笑,他们的悲,他们的爱,他们爱得疯狂。阿寺的幼稚、暴躁、傻,杉菜的可爱、杉菜的个性、杉菜的作为,当然还有她的执着和她的格言,她总爱说“别人的事我没兴趣”。阿寺也有一句话是“道歉若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吗”,都流行了!
这一切的一切,来得突然、火爆,F4的红,好快,似乎比我的感冒快,说来就来,而且不容易走掉。
虽然很多人早已看过盗版了,但电视上正式放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再回味一遍的,加上一些没看过的人进来,更是人气大升了!……所以,就期待《流星花园》吧,希望到时候我的感冒能好,希望我对感冒的埋伏能成功,也希望F4的流感潮有新的进展!
也不怪,曾女因为身体不好,经常请假,她未必能搞得清作业是什么。她能写,并且上交,就已经是不错了。不过,她真是一个有趣味的人,和我有着共同的兴趣。她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张老师从来不批评她。
不知不觉之中,我已经看完了很多随笔。我把我认为好的随笔放在一边,一般的放在另一边。天已经暗下来了,外面打球的同学都散场了,办公室里也空了。当我回头一看时,我吓了一跳,原先以为傍晚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但分明还看到了一个人,张如果仍然坐在他的座位上。
他坐在那里不要紧,问题是他不能那么没有声音地坐在那里。他什么事也不做,就那样一个人坐着。一个男人,一个深沉的男人,那样枯燥地坐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啊?老师您……”我吃惊地叫起来。
“怎么了?我吓着你了?”他看着我,说。
“老师,您怎么不说话?……您……好像……有心思。”我笑着问他,但也不是真的问他。
“谢谢你,何吖卣。你……这是关心我吗?”
“老师,您这一段时间,都到哪里去了?”我并不希望他回答,我只是想和他说几句话。我只是觉得奇怪,他有半个月没来学校上班了。我指着一摞本子对他说:“老师,我看好了,这些,写得比较有趣。”
“……我……这一次回老家,是因为……我以前的一个学生,拿起了一把刀,要捅死一个人……我很痛苦,因为我当初没教好他。人家当然不会来找我的,但我自己会来找我的。我是他的老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