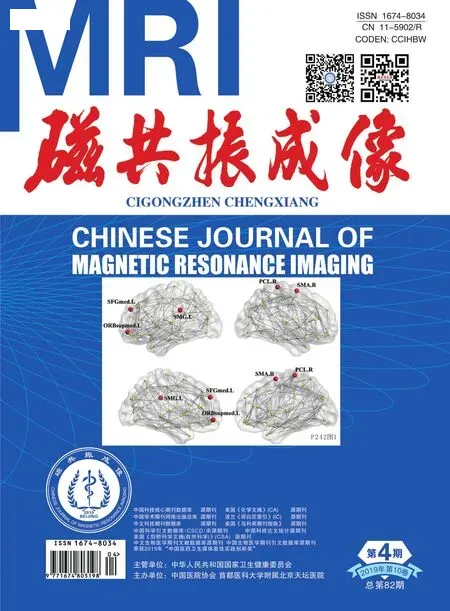迟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易感基因及其对脑结构和功能影响的研究进展
2019-07-01王军霞吴思楚张鑫张冰
王军霞,吴思楚,张鑫,张冰*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导致中老年人痴呆的主要原因,其在65岁以上老年人中发病率达5%,而在85岁以上老年人中占到30%~50%[1]。A D 是由基因、代谢及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疾病。其主要病理机制是细胞外由淀粉样蛋白(β-amyloid,Aβ)形成的老年斑沉积,以及细胞内含有超磷酸化微管相关蛋白tau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tau,MAPT)的神经纤维缠结。按照不同的发病年龄,AD主要包括早发型AD (early-onset Alzheimer's disease,EOAD)(发病年龄<65岁)和迟发型AD (lateonset Alzheimer's disease,LOAD)(发病年龄≥65岁)。临床上最为常见的是LOAD,约占94%,其中遗传易感性占LOAD发病原因的80%[2]。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的发展为AD遗传致病因素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迄今为止,研究报道了多种与AD相关的风险基因,其中前10位热点基因包括载脂蛋白E (Apolipoprotein E,APOE)、桥连接蛋白(Bridging integrator 1,BIN1)、凝聚素(Clusterin,CLU)等(表1)。这些基因的作用通路主要涉及到胆固醇代谢、Aβ代谢、tau蛋白等(表2)。
近年来, MRI在AD风险基因与脑形态学及脑功能的关系研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其中主要包括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voxel based morphometry,VBM)、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及基于血氧水平依赖的功能MRI (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 functional MRI,BOLD-fMRI)等。正是在上述影像技术及GWAS技术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AD风险基因及其相关作用机制被报道出来。因此,本文就AD主要风险基因的作用通路及其对脑结构、脑功能的影响展开综述。
1 胆固醇代谢通路
细胞内β-淀粉样蛋白生成和老年斑沉积是AD的主要病理机制。胆固醇是β-淀粉样蛋白生成过程中最关键的物质之一。胆固醇体内平衡失调主要表现为高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 lipoprotein,HDL)、低密度脂蛋白(low-density lipoprotein,LDL)和HDL/LDL比率的水平异常。其中HDL是与细胞中胆固醇清除有关的重要物质,其能产生潜在的抗动脉粥样硬化效应,包括从外周细胞到肝脏的反向胆固醇转运。胆固醇代谢过程同时受到多种基因调控,包括APOE、胆固醇酯转录蛋白(cholesterol ester transcriptin,CETP)等。
1.1 APOE基因
APOE基因共有3种多态位点,分别是ε2、ε3、ε4。其中,APOE-ε4是目前唯一确定的与散发型LOAD相关的致病基因。APOE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将胆固醇转运至神经元中从而调节脑内β-淀粉样蛋白的生成。该基因不仅能够促进脑内Aβ的沉积,其也是轴突生长及突触形成、重塑的关键物质。因此,APOE基因能够影响人类学习、记忆及神经元修复等功能。
Cacciaglia等[3]对533名健康成人进行基因-脑形态学关联分析发现,APOE-ε4携带者右侧海马、尾状核、中央前回及小脑脚区的脑灰质体积减小,同时在这些区域APOE基因与年龄具有交互作用。同样,Saeed等[4]提出APOE-ε4基因位点量越大,AD患者海马体积越小,学习记忆尤其是长时回忆表现越差,而且海马体积与学习记忆表现的相关性只在APOE-ε4携带者中观察到。上述结果表明,APOE-ε4基因与海马萎缩及学习记忆能力减弱有关,这与先前多项研究结果一致。APOE基因不仅影响脑结构及认知行为表现,与脑功能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De等[5]证明APOE-ε4携带者左侧海马种子区与左侧前额叶、右侧顶叶及岛叶皮层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增强。同时,APOE-ε4携带者海马脑区与左侧顶叶皮层的功能连接强度与记忆表现呈正相关。作者认为APOE-ε4携带者海马脑区与上述脑区的功能连接增强可能是对其认知行为能力减弱的一种补偿机制。
1.2 CETP基因
CETP基因位点位于16q21。其编码的胆固醇酯转录蛋白是调节体内脂蛋白水平的关键蛋白,其主要将胆固醇酯从HDL转移到LDL,以交换甘油三酯,从而调节胆固醇的体内平衡。同时,CETP能够通过与APOE受体相互作用来促进脑内神经元摄取HDL颗粒[6]。CETP基因变异可导致CETP血清浓度和活性的改变,从而影响HDL水平以及脂蛋白颗粒的大小。
有学者就CTEP基因多态性与脑结构及功能的关系做了相关研究。Murphy等[7]通过VBM方法分析发现,APOE-ε4携带者中,CETP I405V-V与C-629A-A基因携带者内侧颞叶脑皮层厚度更大,所患AD风险更低;而在APOE-ε4非携带者中,I405V-I基因携带者同样具有上述表现。这表明CETP基因多态性对脑结构可能受到APOE的调节,即两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Salminen等[8]对健康老年人进行DTI扫描发现,与CETP I405V IV/VV相比,II/II组双侧颞叶、顶叶及枕叶灰质的平均扩散率(mean diffusivity,MD)更大。且同时携带APOE-ε4基因者,其左侧颞叶的部分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和轴向扩散系数(axial diffusivity,AD)增大。这表明I405V II基因可能是健康老年人灰质体积减小的独立风险因素,且部分脑区灰质老化可能与CETP风险基因导致胆固醇运输障碍有关。该研究还初步证明了I405V基因与APOE-ε4基因在脑灰质损伤的协同神经保护作用,这与上述Murphy等[7]的研究共同验证了CETP与APOE-ε4基因具有交互作用。Warstadt等[9]提出年轻人中CETP rs5882 G基因量增加与VBM分析中FA值升高、径向扩散系数(radial diffusivity,RD)及MD降低有关。而上述关系在老年人中结果却相反。这表明胆固醇水平可对脑白质完整性产生影响,且CETP基因对脑白质完整性的影响具有年龄依赖性,这对更进一步明确AD病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1.3 CLU基因
CLU基因又称为载脂蛋白J (apolipoprotein J,APOJ)。顾名思义,其与APOE的生物学作用相似,都与体内脂质运输有关。CLU还参与细胞凋亡及调节补体系统,并产生与Aβ蛋白清除有关的凝聚素,在蛋白降解中承担着分子伴侣的作用。有研究表明CLU rs11136000 T基因对人脑功能具有神经保护作用[10],且CLU-C与CLU-T基因相比,其发展为LOAD的概率是后者的1.16倍[11]。
Lancaster等[12]对85名健康成人进行fMRI扫描,提出CLU rs11136000风险基因C携带者在做工作记忆任务时前额叶和边缘系统的脑激活增加,且CLU-C基因携带者的右侧海马皮层脑灰质密度轻度减小。作者认为上述脑区的激活增加可能是由于CLU-C风险基因导致早期大脑结构及功能连接改变而产生的一种补偿神经活动。一旦上述补偿机制失调后,就会进展为临床型AD。Ye等[13]通过静息态fMRI扫描提出,在默认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的核心皮层中线结构中,遗传性轻度认知障碍(amnestic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aMCI)者CLU基因、疾病、时间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他们表示对照组中CLU-CT/TT者前额叶的功能连接增强和aMCI中CLU-CT/TT者边缘系统功能连接减低都是对情景记忆能力下降的一种补偿机制。也就是在正常衰老过程中增强的FC是对认知能力下降的一种补偿表现,同样aMCI CLU-CT/TT者FC减低也是对认知功能损害的一种补偿表现,因为研究者认为在认知障碍发生后过度增强的FC反而不利于认知功能。由此可见,存在于CLU基因多态性与脑功能之间的这种补偿机制对维持人脑活动具有重要作用。

表1 LOAD相关的前10位热点基因多态性Tab. 1 Top 10 hot spots related to LOAD

表2 LOAD不同发病机制通路中的风险基因Tab. 2 The risk genes in the LOA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echanism pathways
2 Aβ通路
A β 蛋白主要是在淀粉样前体蛋白(a m y l o i d precursor protein,APP)水解过程中借助β和γ分泌酶衍生出来的,其中β分泌酶被认为是此过程的限速酶。Aβ蛋白是AD病理机制的核心物质。其在神经末端异常聚集形成老年斑块,从而导致神经突触的损伤和最终神经退行性变[14]。因此,Aβ蛋白与AD患者突触损伤和记忆力缺陷息息相关。
2.1 TOMM40基因
线粒体外膜转位酶40(translocase of outer mitochond-rial membrane 40,TOMM40)与APOE都位于19号染色体上,且两者处于连锁不平衡关系(linkage disequilibrium,LD)。目前研究较多的是TOMM40rs10524523(“523”)脱氧胸苷聚合物(T)的长度可变性。现今统一将该聚合物的长度分为以下3种:短(S:14~20重复序列)、长(L:21~29 重复序列)和很长(VL:超过29个重复序列)。TOMM40基因编码的线粒体外膜移位酶对体内蛋白质的运输至关重要,包括将β-淀粉样蛋白和其他蛋白物质转运至线粒体内从而使其发挥生物学作用。TOMM40表达异常会导致线粒体无法进行正常的供氧活动,最终使得大脑神经元及其他组织器官的功能障碍。这也是TOMM40成为AD风险基因的关键机制之一。
Burggren等[15]提出TOMM40 poly-T长度越长,大脑内嗅皮层厚度越薄,且该关系只在APOE-ε4非携带者中存在。Johnson等[16]同样表示TOMM40 VL/VL组与S/S相比,前者在语言学习任务中表现更差,而且随着VL基因量的增加(从无VL基因到S/VL,再到VL/VL)腹侧扣带回和内腹侧楔前叶的灰质体积越来越小。Laczó等[17]在aMCI者中也发现TOMM40 523 VL/VL基因与S/S基因相比,其两侧内嗅皮层及左后侧扣带回皮层厚度显著减低,且TOMM40 523 VL基因与非中心空间导航功能障碍有关。大脑内嗅皮层是决定人类记忆、学习功能的关键脑区,上述研究结果皆验证了TOMM40 VL/VL与特定脑区如内嗅皮层厚度减小及学习记忆等功能下降有关。这也强调了对认知正常的老年人进行临床前的形态学评估及基因变异检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2 BACE1基因
天冬氨酸蛋白酶1(B-site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cleaving enzyme1,BACE1)是Aβ蛋白生成中最主要的限速酶,其也是目前β分泌酶中研究最为广泛且成果最为显著的一种。研究证明,AD患者脑中BACE1的表达明显增多,且BACE1的水平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多[18]。Timmers等[19]提出,脑脊液中BACE1的水平与AD下游标记物即Aβ1~42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证明了BACE1基因在AD病理机制中充当着关键的作用。
目前,关于BACE1基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抑制剂的临床应用上,而针对其与脑结构及功能方面的关联性研究尚且不多。Tsai等[20]提出BACE1 rs638405基因多态性与正常人脑灰质体积变化有关。他们提出与rs638405 C等位基因携带者相比,GG组左侧小脑和右侧小脑舌侧区的灰质体积显著增大,但两组在认知功能测试上无显著差异。Ewers等[21]通过分析脑脊液中BACE1的表达水平和人脑海马体积发现,脑脊液中BACE1活性增高与AD患者两侧海马体积减小呈正相关。因此,BACE1基因多态性能够影响部分脑区灰质体积,但其具体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 tau通路
脑内神经纤维缠结是AD的另一重要机制。神经纤维缠结主要由成对的螺旋细丝(paired helical filaments,PHFs)形成,PHFs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异常磷酸化的MAPT。MATP在人体内参与多种细胞生物活动,包括神经轴突的生长、微管运输及少突胶质细胞的成熟等。tau的异常磷酸化是AD发病机制的关键点,因此,与tau磷酸化相关的基因及蛋白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包括BIN1、糖原合酶激酶3B (glycogen synthase kinase 3B,GSK3B)等。
3.1 BIN1基因
BIN1基因是继APOE之后发现的第二大AD风险基因[22]。BIN1基因编码一种与细胞内吞作用、细胞凋亡等有关的蛋白质。BIN1能够直接与tau蛋白结合,从而调节tau蛋白的活动。另外,BIN1基因还能通过调节BACE1的活动从而影响Aβ蛋白的分泌。Ubelmann[23]等证明,BIN1能够抑制早期轴突核内体中BACE1的再循环,将其限制于早期内体小管中,从而影响Aβ蛋白的生成。因此,BIN1与BACE1基因在AD病理机制上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Wang等[24]认为BIN1基因多态性与AD患者海马脑区(rs7561528)及海马旁回(rs72838284)萎缩具有显著相关性。Li等[25]提出BIN1 rs6733839与左侧海马及右下顶叶体积减小有关。Chauhan等[26]同样提出BIN1与海马萎缩有关。因此,上述多项研究证明BIN1基因多态性与海马体积减小存在相关性,这也为AD BACEI基因携带者记忆力减退提供了证据。Zhang等[27]对正常年轻人进行结构MRI及fMRI扫描发现,BIN1 rs744373 GG组在高强度的记忆任务中表现较差,两侧海马(hippocampal formation,HF)与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弱,但GG组的海马脑区体积却较大。作者认为BIN1 rs744373 GG组海马脑区体积增大可能是对HF-DLPFC功能连接减弱表现出的一种补偿机制,从而得以维持正常人脑的认知行为。
3.2 GSK3B基因
GSK3B基因是糖原合成过程中重要的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其能够磷酸化和灭活糖原合成酶。GSK3B主要参与神经元中细胞骨架形成与重塑,因此,其与突触可塑性及神经损伤有关。最重要的是,GSK3B能够使得tau蛋白过度磷酸化,从而促进神经纤维缠结。
目前,GSK3B基因在脑结构与脑功能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Bai等[28]提出aMCI组GSK3B rs334558 T基因携带者右侧额上回存在激活缺陷,但是该区域的功能连接却显著增强。同时,右侧额上回脑功能连接增强与aMCI T基因携带者非记忆表现存在正相关。该研究表明aMCI患者静息态脑功能异常可能由GSK3B rs334558基因遗传变异来解释,但受到样本量的限制,上述实验结果仍需进一步验证与研究。
4 多巴胺通路
多巴胺(dopamine,DA)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其参与人类认知行为及情感处理等多种过程。多巴胺在脑内的信号强弱主要取决于多巴胺的分泌水平和多巴胺受体的功能。因此,对多巴胺分泌和多巴胺受体具有调控作用的基因都能对多巴胺的生物学作用产生影响。
4.1 COMT基因
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COMT)是人脑突触内多巴胺的主要降解酶。COMT有多个基因多态性位点,包括rs4608、rs4633等,其中Val (158) Met (rs4608)位点是目前研究最为广泛的。COMT Val (158) Met多态性对儿茶酚胺神经递质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COMT Met基因编码的COMT酶活性较低,使得人脑内多巴胺的水平升高,从而使Met基因被认为是人类认知行为的有益基因。相反,COMT Val基因编码的酶活性较高,使得人脑中尤其是前额叶多巴胺水平明显降低。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对COMT与脑结构、脑功能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有研究表明COMT rs4608 Met基因与额颞叶及后扣带回[29]皮层厚度增加有关,也有人认为Val基因与额叶体积增大、Met基因与海马体积增大[30]有关。Watanabe等[31]提出与Val/Met相比,Val/Val者两侧尾状核和扣带回后侧的体积明显减小。由上可知,目前关于COMT基因与大脑形态学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上述实验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影像学分析方法和实验设计的不同造成的,后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Jaspar等[32]对15名年轻成人进行任务态fMRI扫描发现,Val/Val与Met携带者相比,其在做斯特鲁任务(stroop task)时右前额叶与左侧颞中回的脑区激活更加明显。同时,Val/Val组这两个脑区之间表现出更强的正向功能连接,而在右前额叶与左侧舌回之间表现出较强的负向功能连接。这表明COMT基因对额叶功能具有重要作用,且前后脑区之间功能连接增强可能是为了保证Val/Val组多巴胺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仍能高效完成Stroop任务而表现出的一种补偿机制。Zhang等[33]运用静息态fMRI和特征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 centrality,EC)研究方法提出与Met携带者相比,Val/Val组在记忆测试中正确率更高,且Val/Val组左侧海马旁回的EC更高。同时,Val/Val组左侧海马旁回的平均EC值与记忆测试的正确率呈正相关。由此可以说明COMT Val (158) Met多态性能够影响左侧海马旁回与其他脑区的内在功能连接。但上述结果与先前部分研究[34]认为Met基因携带者认知行为更佳相矛盾,因此,就COMT基因多态性对认知行为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Xu等[35]认为与COMT rs4633 C基因携带者相比,TT者的言语智商(verbal intelligence quotient,VIQ)更低,其左侧额上回及左侧顶叶的远程功能连接密度(long-range FCD,lrFCD)更高。同时,左侧顶叶的lrFCD对COMT rs4633与VIQ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这暗示COMT基因-脑-认知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一条调控通路,并可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4.2 DRD2基因
人脑内多巴胺受体主要包括DR1样受体、DR2样受体,其中DR2样受体又包括DRD2、DRD3和DRD4。目前研究较为广泛的则是多巴胺D2受体(dopamine D2 receptor,DRD2)。DRD2定位于11q22-q23,其大多表达于大脑纹状体中。DRD2与COMT都是多巴胺神经递质表达的关键物质。COMT主要影响突触内多巴胺的分泌水平,DRD2主要与多巴胺神经递质结合从而促进其发挥生物学作用。
Persson等[36]提出DRD2 TaqIA rs1800497 A1基因携带者与非携带者相比,其记忆能力尤其是长期记忆表现明显下降。同时,A1携带者左侧尾状核的激活减少,且该效应只在老年人中有所体现。再者,在A1基因非携带者中,尾状核的脑区激活与记忆表现存在正向关联。这提示DRD2 TaqIA基因与脑功能、认知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一条调控通路,且DRD2基因多态性对大脑功能的影响会随着年龄被放大。Stelzel等[37]提出DRD2 rs6277 C基因与做记忆任务期间基底节区与前额叶皮层的功能连接增强有关。同时,Markett等[38]利用扩散加权成像技术发现,DRD2 rs6277 CC者基底神经节至额叶皮层连接的白质纤维束FA值要比T基因携带者高。FA值是反映轴突髓鞘形成的敏感指标,因此可以预测DRD2 rs6277基因多态性不仅与基底节区与前额叶皮层的功能连接有关,还能对两者之间的结构连接产生影响,这对更进一步研究DRD2基因与脑结构及功能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5 神经营养因子通路
5.1 BDNF基因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是一种对酪氨酸激酶B受体(TrkB)具有高度亲和力的神经营养因子。BDNF与APOE相似,在脑内都主要由星形胶质细胞产生,都与突触修复及神经可塑性有关。BDNF主要在海马脑区高表达,因此其对人类学习和记忆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B D N F 基因多态性中,目前研究较多的是Val66Met多态性与脑结构及脑功能的关系,且大多在成人中进行。研究证明,Met携带者与Val/Val相比,其额上回及额中回(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39]、前扣带回皮层[40]、舌回[39]的灰质体积明显减小。然而,Liu等[41]运用VBM分析方法提出Met/Met与Val/Val相比,其左侧额中回、两侧颞中回及左侧小脑灰质体积较大,且其左侧颞中回、左侧颞下回及右侧额上回较Val/Met增大。由此可知,关于BDNF Val66Met多态性与脑结构的关系尚不明确。在脑功能方面,Chen等[42]提出BDNF Met携带者与非携带者相比,其在执行工作记忆任务时右侧额上回及中间枕回的脑激活显著减低。Sambataro等[43]同样提出与Val/Val者相比,Met携带者在做记忆存储及记忆检索相关的任务时,其海马脑区的激活减低。因此,BDNF Met基因可能与做记忆任务时特定脑区激活减低、认知功能减弱有关。
鉴于迄今关于该基因与儿童脑结构及功能的关系研究甚少,因此部分研究者在健康儿童中做了相关实验。Jasińska等[44]提出BDNF Val/Val组与陈述性记忆有关的脑区如前颞叶和内嗅皮层的皮层厚度更大,但Met携带者右侧海马体积更大,这一研究结果与Marusak等[45]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这与成人的研究结果相悖。Hashimoto等[46]提出BDNF Met/Met组右侧楔叶的灰质体积比Val/Val组显著增大,而这一结果迄今尚未在成人中发现。因此,从上述BDNF基因对青少年及成人脑结构的影响中可以发现,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脑区BDNF的表达水平及其作用是各异的。在一定程度上,BDNF Val66Met多态性对大脑发育过程中脑结构的影响能够反映特定脑区皮质发育成熟的轨迹变化。
6 小结
AD是最常见的老年性痴呆类型,但由于其风险基因众多,致病因素多样,至今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GWAS及MRI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探究认知相关基因对脑结构及功能的影响。本文从不同基因各自的作用通路方面介绍了其对脑结构和脑功能的作用,这对AD病理机制的研究及临床AD的早期诊断与预防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后续探究基因-脑-行为学通路及不同基因间交互作用对脑结构及脑功能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