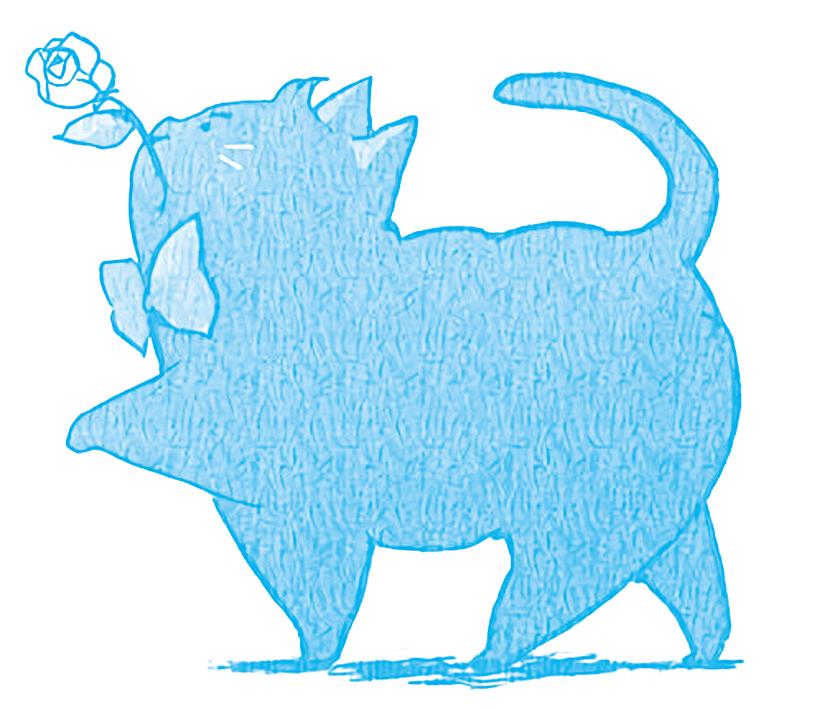我在北京的第一次恋爱
2019-05-31洪烛
洪烛

我与北京老市民阶层的最初交往始于第一次恋爱。也直到我爱上了一位北京姑娘,才仿佛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生活。一开始我也没关心她的家世,只觉得她穿衣服不华丽但干净,说话的语调很顺溜,儿化音重,喜欢使用一些生动的本地俗语(譬如半开玩笑地说我“蔫好”,即暗坏之意,半贬半褒),跟我日常听到的普通话存在明显差异,简直是银铃般的嗓音。我很快就在这种音乐中醉倒了。我很快就鼓足勇气追她了。
记得第一次在楼梯拐角处强吻她,她挣脱了,骂我一声“坏蛋”,但是很快就原谅我了。她也就把我当成爱情的候选人,不时让我帮点小忙。有一年圣诞节看完夜场电影,她不敢一个人走夜路,让我送她回家。我们转乘的公共汽车一直向南开,最终停靠在一个叫做白纸坊的站台。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城南的“老区”,进入胡同與四合院构筑的古代迷宫,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来自建筑学意义上的冲击与感动,而且是在一位满口清脆京腔的北京姑娘陪伴之下。年轻的爱情与古老的建筑无意间被命运排列在一起也并不逊色,因为它们同样是在尘世间追求不朽的事物。女友让我用打火机照着她拿钥匙开门,我借着火光留意了一下门牌:“白纸坊东街樱桃胡同28号”,这简直是悬在我头顶的一行诗啊。
我们顺利进入众多造型雷同的四合院其中一座的内部,站在栽种有石榴树的昏暗庭院里,迎面的正房亮着灯,女友的一家人都坐在客厅里等待她的归来。女友落落大方地把我以朋友的身份介绍给她的家人,她母亲首先感激地说早知道有我护送就不用担心了,随即招呼我在藤椅里坐下,又在低矮的茶几上摆开一圈小酒盅般的茶杯,端起沏好的茶壶倒茶。我抿了一口,是茉莉花茶,老北京人爱喝的。在我品茶的过程中,她母亲一直打量着我。而她父亲点头之后只是眯眯笑着,盘着腿坐在长沙发上听手中半导体里的京戏。以后常去她家,发现她父亲话不多,与人交往大多是憨厚地笑着,却是个痴迷的票友。我当时就觉得她父亲身上有旗人的遗风。
那天喝完茶已是后半夜,公共汽车不通了。女友的母亲执意挽留我天亮后再走,并说空着的西厢房专用来接待来访的亲友过夜的:“你没在四合院住过吧?那就住一晚呗。”她的慈祥与热情一下子拉近了跟我的距离。西厢房的摆设极简单,也就一架旧式雕花木床和几件老家具,但有土暖气管道,暖洋洋的。那天夜里我居然失眠了,因为从天而降的爱情?因为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这确实是我在老北京的传统民居里住过的第一夜,第一个古色古香的梦。这就是我发生在北京的一篇奇特的西厢记。我像张生一样辗转反侧,想念着一墙之隔的莺莺,尤其在如今看来,已是一生之隔。那毕竟是一次曾经辉煌但最终失败的爱情,像一枚燃料耗尽而中途坠落的火箭,燃烧的弹片如同流星雨纷飞于我内心的海洋。
第二天上午,女友领我逐一参观各个房间,了解四合院的结构。屋檐上都长草了,砌在墙脚的金鱼池也青苔斑驳,她说她爷爷就出生在四合院里,由此可见这里扎着她家族的根。总之这座院落虽稍显颓败,但一砖一瓦仍流露出昔日的庄严与华贵。她指着天井里的那棵石榴树,说那是她降生之日父亲种下的,如今迎风飒爽如体态婀娜的少女。
那是一次漫长的恋爱。我无数次地跟女友约会又无数次地送她回家,无数次地穿行于那条曲曲弯弯的胡同,仿佛无数次地往返于北京城的历史与现实。我仿佛既是现实的主人又是历史的客人,去北京的往事中做客,听不完的城南旧事。女友的一家日常生活很俭朴,但每逢我去,总要邀请我吃涮羊肉火锅,热气腾腾的火锅使世界都缩小了。女友的母亲在餐桌前最爱回忆她的家谱,她终于遇到一位来自远方的听众了,况且这位听众对她描述的一切充满好奇。
接触多了,我逐渐体察到北京老市民阶层生活的轮廓,他们呼吸在一种陈旧的氛围里。他们住在烧蜂窝煤的平房里,喜欢吃牛羊肉,喝茉莉花茶与二锅头,听京戏,养鸟或金鱼,谈论国家大事,尤其爱回忆往昔,比照当代,他们属于有心理坐标的老市民,下意识地以主人自居,一口一个“咱北京”……
那次恋爱等于给我补上了一门北京民俗课。但在下课铃快响的时候,我和女友由于种种原因还是分手了。真正的爱情或许能开出最绚丽的花朵,却很难结出圆满的果实,造物主可能刻意如此安排的。时间一长,彼此也就中断音信。多年后,我因办公事偶然再路过白纸坊,惊讶地发现那一片四合院居然被推平了,附近崛起一座蝴蝶状立体交叉桥。女友的一家早已拆迁了。难道这一带的古旧建筑也紧随着我的爱情变成一片废墟?徘徊在面目全非的爱情遗址,我究竟在寻找着往事的影子,还是自己的影子?白纸坊重新变成了一张白纸。纸上的风景全部被岁月收藏了。我一直以为一切都在远处、在城市的这一隅完好无损地保存着,但世界的变化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我曾经爱上过白纸坊的女儿,看来我这辈子注定与纸有缘。有缘而又无缘,包括今天,在纸上给昔日的爱情勾勒出模糊的轮廓。一纸之隔的爱情,却比一墙之隔、一生之隔还要遥远。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