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李尔王》的多重解读
2019-05-26曾艳兵
曾艳兵
一种理论或者方法能够适用于任何研究客体或者分析对象,包括对它自身的分析和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是具有普遍效率的理论;一部作品能够被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并且均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发现,那么这部作品便绝非平庸之作,必定是一部深刻、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多见,这样的理论则几乎难以寻觅,若有这般理论,那就已经不是理论,而是真理了。理论可以成为真理,但真理不能成为理论,因为一旦变成理论,便不再有真理了。这里有关理论的问题我们姑且不论,还是谈谈作品吧。我以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李尔王》就是这样一部能够适用于各种批评理论和方法的作品。
该剧根据古老的不列颠传说改写而成。李尔王年事已高,决定根据三个女儿对自己的爱将国土分给她们。大女儿高纳里尔(Goneril)和二女儿里根(Regan)花言巧语哄骗父亲:
高纳里尔:父亲,我对您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我爱您胜过自己的眼睛、整个的空间和广大的自由;超越一切可以估价的贵重稀有的事物;不亚于赋有淑德、健康、美貌和荣誉的生命;不曾有一个儿女这样爱过他的父亲,也不曾有一个父亲这样被他的儿女所爱……
里根:姐姐的话正是我爱您(李尔)的实际情形,可是还不能充分说明我的心理:我厌恶一切凡是敏锐的知觉所能感受到的快乐,只有爱您才是我无上的幸福。
于是,大女儿和二女儿平分了李尔王的国土和权力。小女儿考狄利娅(Cordelia)实话实说:“我爱您(父亲)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李尔王听后颇为不悦,便剥夺了原本准备给考狄利娅的那一份国土。好在法兰西王对考狄利娅一见倾心,喜欢她的诚实:“最美丽的考狄利娅!你因为贫穷,所以是最富有的;你因为被遗弃,所以是最可宝贵的;你因为遭人轻视,所以最蒙我的怜爱。”于是考狄利娅被远嫁法国。李尔王在失去国土和权势后,受到大女儿和二女儿的虐待,并被赶出家门,流落野外,在暴风雨中倍受折磨。考狄利娅闻讯后率军回国讨伐姐姐,不幸失败而被害死。李尔王悲愤不已,最后发狂而死。考狄利娅的两个姐姐争夺权力,争夺情人,最后互相残杀,先后死去。

当然,许多人,包括托尔斯泰都认为李尔王分国土的情节不可信,“李尔没有任何必要和原因而必须退位。同样的,他跟女儿们活过一辈子,也没有理由听信两个女儿的言辞而不听信幼女的真情实话;然而他的境遇的全部悲剧性却是由此造成的。”(托尔斯泰《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见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02页)李尔王对女儿厚薄不一,以这样的条件放弃权力,如果放在一个几内亚或者马达加斯加的小亲王身上,也许会更加可信。不过,托尔斯泰责备《李尔王》,“但这却成了一个可悲的讽刺,因为托尔斯泰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李尔王。”当然,“托尔斯泰很准确地看出作为戏剧家的莎士比亚既非基督徒也不是道德家。”弗洛伊德则这样解释《李尔王》,“两个姐姐已克服了对父亲与生俱来的爱恋,并萌发出敌意。具体地说,她们憎恶因早年的这种爱恋而招致的沮丧。考狄利娅对父亲仍然一往情深;这是她心中圣洁的秘密。一旦被要求示之众人,她只能缄口不语,公然抵抗。在很多病例中我都见到过类似的行为。”(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03页)这种说法虽然别具一格,但恐怕很难让人们心悦诚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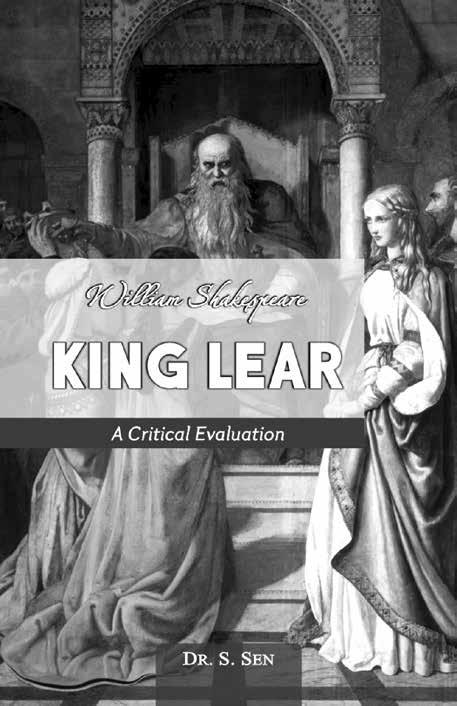
李尔王在荒原中的一段呼喊,被认为是人文主义者的经典发声:
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会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
荒野的暴风雨象征着李尔的内心风暴,促使他清醒地认识了外部世界。通过自己苦难的遭遇,李尔也清楚地认识了自我,并开始回归人性,回归自我。自身的苦难使他开始体悟到全体人民的苦难,开始想到那些“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时的李尔似乎与杜甫的情怀有些接近。这段台词洋溢着浓郁的仁爱思想,這也是人文主义者的主导思想之一。凡此种种,便可以看作是人文主义式的解读了。
美国当代批评家迈克尔·莱恩(Michael Ryan)在认真研读过《李尔王》后,决定对该作品进行多重解读:一方面检验各式各样的理论,另一方面则拓展并深化对《李尔王》的理解和认识。莱恩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酷儿理论、男/女同性恋研究)、历史主义、族裔批评(后殖民主义和国际主义研究)。
迈克尔·莱恩首先对《李尔王》进行了形式主义的解读。他认为,形式主义者可以从注意该剧对它的世界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假定的陌生化开始。自然的等级制度受到了质疑,有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该剧第一场:李尔王宫大厅。肯特伯爵与葛罗斯特伯爵的对话:
肯特:大人,这位是您的令郎吗?
葛罗斯特:他是在我手里长大的;我常常不好意思承认他,可是现在惯了,也就不以为意啦。
肯特:我不懂您的意思。
葛罗斯特:伯爵,这个小子的母亲可心里明白,因此,不瞒您说,她还没嫁人就大了肚子生下儿子来。您想这应该不应该?
肯特:能够生下这样一个好儿子来,即使一时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
葛罗斯特:我还有一个合法的儿子,年纪比他大一岁,然而我还是喜欢他。这畜生虽然不等我的召唤,就自己莽莽撞撞来到这个世上,可是他的母亲是个迷人的东西,我们在制造他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场销魂的游戏,这孽种我不能不承认他。
这孽种就是葛罗斯特的庶子艾德蒙(Edmund),葛罗斯特还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儿子,名叫艾德加(Edgar)。最后庶子受到父亲的青睐,嫡子却被父亲驱逐。由他们的关系混乱、僭越引出当时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混乱、颠倒这一主题。“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为仇敌;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最后,俄国形式主义也许会注意到,开场的对话这一动作偏离了处于剧本中心的主要事件。与后面紧跟着的李尔的宣言相比,偏离的性质就更明显。而且,它的话题是一种发生在合法的社会行为场景背后的事件(通奸、非法的生養),和一种要避开公众目光的隐蔽的意图(‘看不出两位公爵他更喜欢哪一个)。也许可以这样说,开场对话的这种隐蔽的场景背后的性质使隐蔽的意图(隐藏在阿谀奉承的场景之后)的问题戏剧化了,而这将导致李尔的垮台……戏剧从离开中心情节的地方开始暗示在这些争论中所持的立场:真实不是一种外在表演的东西,也不是由舞台上的言词构成的,而是不在他人视线之中的自然产生的真实情感——‘说我们感受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应该说的东西。真正的高贵或美德也将被证明是一种内在的高贵品质,而不是那种外在的公开的展示。戏剧本身在开场的背景对话中,说明了前台是一个欺骗的场所。”(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赵炎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1-12页)
该剧一开始并没有直接描写李尔,而是通过肯特和葛罗斯特之间的对话间接地讲述了李尔的故事。从这一对话中我们得知,李尔是难以理解的,并且李尔也并不了解自己。葛罗斯特有两个儿子,合法的艾德加和非法的艾德蒙,这正如词语具有两重意义一样:既能表达意义,又能隐藏意义。“《李尔王》是一部多种话语模式并存的异质性文本。”李尔的语言具有命令话语的性质,他把这称为父亲的语言。它的意思是单一的、独语的,没有混杂其他的话语。李尔的突然发疯预示着语言的崩溃。
在第一场,通过对考狄利娅姐姐们的侧面评论,考狄利娅对姐姐们的阿谀奉承的做法进行了对答:“考狄利娅该说什么呢?默默地爱着吧。/……我确信我的爱比我的语言更富有。”在考狄利娅看来,真实在于感情而不是言词。在这里,考狄利娅的言词就是她的语言,并胜于语言。在浮夸的语言面前,沉默是一种更加有力的语言。
一个新批评主义者将会在剧本中寻找反讽和悖论,它们体现了矛盾的成功和解,普遍和特殊的融合。其中典型的例证是法兰西王对考狄利娅说的那番话:“最美丽的考狄利娅!你因为贫穷,所以是最富有的;你因为被遗弃,所以是最可宝贵的; 你因为遭人轻视,所以最蒙我的怜爱。”李尔曾呼唤考狄利娅“my poor fool”,但这不是“我可怜的傻瓜”的意思,应译为“我可怜的好闺女”(这里“fool”不是指傻瓜,而是表示爱怜的称呼。该词朱生豪译为“傻瓜”,方平译为“丫头”,孙大雨译为“小宝贝”)。这些修辞表达也是新批评主义者会特别关注和分析的。
一个结构主义批评家将会对《李尔王》具有双重情节,而且这两个情节既平行又同构这一事实产生兴趣。第一个情节就是李尔王从掌权到失权;第二个情节是艾德加从无权到有权。艾德加推翻了那个非法的王位继承者,也就是他的非法出生的弟弟艾德蒙。“通过结构的对应,戏剧的意义系统也被用来证明从血缘转到高贵的合理。”
从精神分析角度看,李尔与他的女儿们的关系,使人想起男孩与他的母亲的关系。批评家们注意到真正的母亲在剧中是缺席的,她的缺席意味着什么?母亲的缺席是否凸显了俄狄浦斯情结呢?
依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李尔王》正处在老的封建形式与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间的交界处。李尔是土地贵族的代表。“他的垮台是当时 ‘贵族的危机的一个寓言。他的失去土地是一个土地正在失去其经济上的力量并正在被贸易所取代的一个典型。”在这个时代,高贵与气质或出身没有什么关系,而与金钱有关。

下面我们看看后现代又是如何解读的。莱恩说:“福柯也许会把剧本看成是描写了从传统的社会控制形式向更为现代的惩戒性的社会类型的转变,这种转变要求对那使得新的方法成为必然的危机进行描写。德勒兹与加塔利也许会在其中发现它描写了一个领土的平衡如何被一系列的溃败和领土分割的运动所打破,而这种分割最终又自己重新整合起来,产生出一种新的秩序。德里达也许会对剧中由真理与表现、存在与模仿、言说与书写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有序与无序的方式感兴趣。克里斯蒂娃会注意发疯一场怎样展现了意涵在颠覆假定语言维持的真理秩序的理想方面的力量。利奥塔将会注意剧本怎样为了真理的观念或语义的内容而消除自己的形式,它更重视的是这些而不是物质性的意涵的运作。而鲍德里亚则会注意剧本是怎样驱逐模仿肯定真实的,而那真实本身也仅仅是模仿。”
一个女性主义者也许会把李尔王看作一个滥用权力的家长,而不是一个有着悲剧性缺点的英雄。从性别理论或酷儿理论来看,“《李尔王》写于一个同性恋——或者鸡奸——被禁止的时代,然而它也是新登基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使他的臣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是一个同性恋的实行者的时代。”“人们甚至可以说,通过在开场的对话中将它引出来,莎士比亚暗示了同性恋亚文化生活的隐秘性质,而作为剧院中的一员,他可能也是属于这种亚文化的……莎士比亚通过描写一出充满了同性恋暗示的戏中戏,映射了当时伦敦剧场本身存在的同性恋亚文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莎士比亚是个可能的同性恋者,然而却结了婚,我们知道艾德加爱的是男人,然而与詹姆斯一世一样,在悲剧结束时他不得不站在公众场合,假装服从强制性的异性恋的原则。然而这种服从命令的标志的明显缺乏(艾德加一直没有与任何一个女人有联系),说明了这种接受是多么的犹豫与勉强。”总之,《李尔王》“也是同性恋男人的悲剧,因为他必须在强制性的异性恋形式下生活,同时却体验着那种必须保持沉默的感情”。
从历史主义或新历史主义的视角看,《李尔王》又具有另一种意义。《李尔王》1606年宫中上演,詹姆斯一世1603年登上王位。人们早已注意到了虚构的国王与真实的国王之间性格的相似性。但是,莎士比亚写作此剧究竟是批判和谴责国王,还是警告与维护国王的权威?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主义者与新历史主义者的态度也许有着根本的不同。历史主义者也许会写作《李尔与詹姆斯》這类文章,主要持前一种观点;而新历史主义者则会写作《莎士比亚与法官》这类论文,主要持后一种观点。“詹姆斯以厌恶国事而著名,而李尔在剧中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把自己从‘国家事务中解脱出来,以便能够去打猎,而这是詹姆斯最喜欢的一项消遣。”“剧中对于司法与审判的看上去是颠覆的批判是话语方面的一种策略。它通过警告王权的滥用以更好地为它的神圣天定的必然性辩护,从而试图确立绝对君权的合法性。”
该剧还表现了酷刑,即挖出葛罗斯特的眼睛,这在公开行刑的制度化的暴力社会司空见惯,而在今日文明社会里就显得难以为人们所接受了。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福柯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规训与惩罚》。“在几十年间,对肉体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征性烙印、示众和暴尸等现象消失了,将肉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的现象消失了。”(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页)有人认为从宗教角度看,该剧可以改名为“李尔王的救赎”,李尔王代表的是受苦受难的普通人;考狄利娅则代表救赎人类的圣徒和殉难者;艾德加则是一位基督教绅士。也有人将该剧理解为一部当代的荒诞戏剧。已经疯狂的李尔与已经失明的葛罗斯特在多佛悬崖上的一段对话可以理解为贝克特荒诞剧的先驱。
总之,该剧通过描写一个绝对权威的封建君主变成普通人的过程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这部戏的概括意义最强,富有哲学意味。该剧探讨了权威与社会正义、权力与智慧、真诚的爱与虚伪的爱、人性与大自然的善恶等问题。以权威强求爱反而会失去爱,助长了虚伪与邪恶;而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但真诚的爱又会损害权威的尊严。因此,权威与爱不可兼得。由此可以推及家长与子女、国王与臣民、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没有权威便不可能统治平稳,但权威又会遏制爱与理解,失去民心,这样统治仍不会平稳。光有权威或者爱都是不够的,而二者只能择一时,莎士比亚选择了后者。另外,权利并不等于智慧,权力助长的往往是愚蠢。权力如果再加上愚蠢,悲剧就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