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者花总:挣脱那个名为“英雄”的壳
2019-05-24高伊琛
高伊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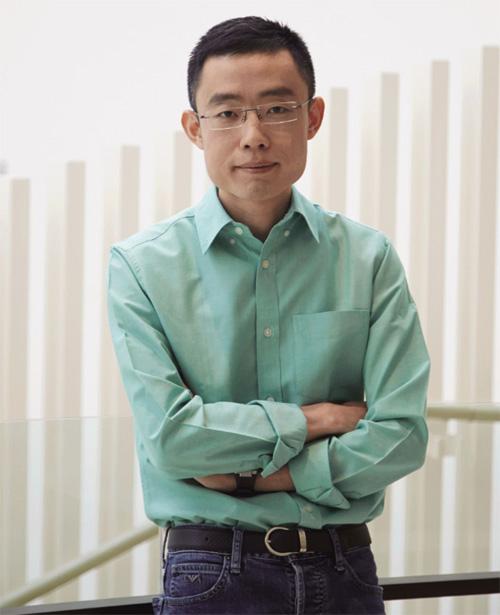
四十岁这年,花总没能不惑,反而遭遇了一次更严重的“人设”桎梏,让自己陷入迷茫。时无英雄,于是人们将他困在一个名为“英雄”的壳里,而他想挣脱。
2018年11月14日发布的偷拍五星级酒店客房卫生的视频《杯子的秘密》,让花总的微信好友人数破了千。一些朋友开始写文章回忆他的过往,“就感觉这人已经挂掉了一样”。越来越多自媒体以他为主人公,加工他的事迹,转换为十万加的点击。
“我都快被那篇洗稿文搞得抓狂了。”本以为,2018年那场五星级酒店杯子风波将随时间平静下来,结果有一天,知名网友花总惊恐地发现,朋友圈里有七八十人转发了同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
在文中,他成了英雄。他募捐,支教,卧底,鉴表,写《装腔指南》,扒皮“世奢会”,揭露酒店卫生乱象,做着“有益于社会却讨不到半点好处的人”。
“我说那不是我,那谁是我?”网络和现实的边界再一次被打穿,大众眼中的花总,亲友眼中的吴东(“花总”真名)和真实的他相互碰撞,人物性格更多的是全然不同。
被打穿的保护壳
花总被“特殊对待”了。
2019年新年过后,他和朋友在北京一家酒店餐厅吃饭,后厨拿着酱油瓶绕出来,服务员抹着隔壁的桌子。两人用餐,五六个工作人员站在不同角落忙碌。他意识到,他们是“看热闹来了”。
入住的客房放着一罐饼干,他吃了几块,第二天罐子马上被补满。床上摆着软枕头——他的睡眠喜好被专门记录下来。如今到任何酒店,他都会被认出来。
一个超过2000天以酒店为家的人,理应被当作“消费者”,却被定义成了“暗访者”。
跟绝大部分中国网民一样,吴东小心翼翼地躲在自己的ID“花总丢了金箍棒”背后,以此作为保护壳。但在几次“英雄事迹”后,花总躲不过去了。
如今他成天躲在自己的微博小号背后卖萌,试图消解大号的苦大仇深。事实上,两个号的人设都无法体现真实的他。
他常用小号搜索自己的ID,又对细节耿耿于怀。100条评论里,哪怕有98条好评,他也会更在意余下两条恶评。他介意被说“自我炒作”,也介意被当作“虚伪冷漠的上等人维权先锋”。
网络和现实的边界第一次被打穿,是在7年前的新周刊新锐榜颁奖典礼。
台下嘉宾里坐着一名戴着口罩的怪客,主持人华少念出获奖者的名字——吴东。真名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被暴露在大众面前,他不知所措。登台的刹那,他想,既然名字都被公布了,样子也没必要藏了,于是摘掉了口罩。
拿奖一幕被镜头捕捉下来,他右手握着奖杯,扭头回望,看上去意气风发。那张照片后来成为世奢会风波中他被警方传唤的新闻配图。现实中开始有人知道他就是花总。
《杯子的秘密》之后是第三次被打穿。
视频发出当天,新京报视频团队来做采访,询问是否需要打马赛克。他判断,可能会有酒店不承认视频内容或者提出“摆拍说”,决定露脸出镜来为自己的作品背书。
这加速了他的个人信息暴露。2018年11月16日起,花总的资料开始在多个酒店群流传。“吴东即花总”的消息迅速扩散,卧底时认识的工友、偏远地区的乡村干部、久不联络的中学同学,甚至相亲对象都来追问。
底线被触及,他决定死磕——上一次是世奢会风波中,有人找上他的父母。
花总用了四十多天寻找信息泄露的源头。
他在城市间奔波,挨个说服二十余名参与者回溯传播源。在他看来,大部分信息传播者没有法律意识,提醒即可,行政拘留就“过了”。这些人他都原谅了。
最终,他找到的信息最上游是深圳龙华某酒店总经理彭某,数度沟通无果。
2019年1月9日,深圳龙华公安局通报,彭某在微信群发布涉及花总的个人信息,根據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给予其行政拘留7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迅速掌握游戏规则的人
“这个社会是不是特别缺一个英雄人设的人?”2019年1月7日,吴东靠在北京某五星级酒店的沙发上,他抛出这个问题,却不像需要答案,“但我不是。”
陈龙耀第一次见到吴东时,吴东的父母正帮他挂床铺上的蚊帐。
大学宿舍八人,只有吴东是由家长送来的。那是1990年代后期,福建师范大学学生大多来自周边农村,吴东父母的穿着打扮和待人接物,让陈龙耀迅速得出一个结论,这位舍友应该出身于家境良好的知识分子家庭。日渐加深的了解也证实了他的判断。
在陈龙耀的记忆里,吴东的知识面之广远甚于同龄人,他每周必买《南方周末》《电脑报》《新周刊》等刊物,属于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一拨人。大一时,舍友们跟着吴东去东街口电信大楼上过网,那是1997年周围唯一能上网的地方,上网要带身份证,一小时10元。
时隔多年,陈龙耀对吴东的故事细节还记忆深刻。
在QQ还叫QICQ的年代,吴东曾让同学们多申请几个QQ号,说“这个东西将来可以卖钱”。他还曾在电商平台8848买过指甲剪,称“网购可能是未来的趋势”,电商平台的创始人、同为知名网友的老榕后来成了他的好友。陈龙耀还记得,吴东被舍友们笑了很多次,彼时网购需要先去邮局汇款,而指甲剪,在宿舍楼附近的小卖部就能买到。“东西寄到宿舍时,大家觉得很离谱,这种东西怎么会去网上买?”
陈龙耀后来成了中学历史老师,在给学生讲解“第三次科技革命”时,他常拿这位舍友做例子,佐证科技发展之快速。
掌握互联网传播规律对吴东来说轻而易举。
大二那年,班上一名女生得了重病。吴东跑去找中文系教授写求助信,通过互联网为她募集到了30萬元。
福州媒体上门报道了这起前所未有的网上救助行动,吴东在师大出了名。在随后的学生会改选投票中,他被选为97级学生会主席。现在的花总不愿多提此事,担心对女生的家人有后续影响。
仿佛是一种天赋,他总能迅速学会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
2007年,还没成为花总的吴东刚到四川泸州支教两周,就在网上为学校募集到3万多元资金,用于资助家贫学生。
他所在的叙永县白蜡苗族乡荞田完小有五百多名学生,分布在学前班到九年级。对于“吃饱肚子就不错”的大部分家庭来说,初中每学年约700元、小学300元的学杂费,负担过重。
山村学校不通网络。周一到周五,收集贫困生家庭情况,周末,吴东跟随校长佘成银回到城里,在个人博客发布信息。学校到县城只有一条火车铁轨式的凹槽小道,路上最少要花费一个半小时。他在博客上描述了这里的状况,并公开佘校长个人账户。
在荞田小学的半年里,吴东的宿舍从17平方米教室改造的四人间宿舍,挪到小青瓦房办公室,再搬至当地农户家中——这段时间里,荞田小学在修建新的教学楼。
钱是吴东找来的。他说服广东一个基金会向学校资助20万元,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增加支持二十余万元,学校修建起一千多平方米的教学楼。
他还联系上海滨特尔公司派技术人员上门检测学校水质。当时山水水源泥沙杂质很多,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义务为学校生产了净水设备,至今还帮学校定期更换滤水芯。
“他做事前从来不跟我们说,没做成更不会说。”佘成银说。
“以为能改变好多,但其实没有”
在花总自己的讲述中,十多年前的支教故事有另一个版本。
“我是个外来物种,自以为能改变好多东西,但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他觉得自己只是制造了一种充满希望的幻觉。
支教归来,他在一家上市公司当高管。他为荞田小学的教师设立过一个奖教基金,两三年后又单方面终止,他觉得自己被当成救世主般的存在,压力过大。
他想割断一切情感联系,一起去荞田支教的老师经常会在QQ或微博上给他留言,而他“始终没回过一句话”。
但在当地老师鲁晓眼中,吴东是个“有心人”,每年都回学校看看,在地震、高温或有人生病时都会第一时间发短信。
彼时,一群二十多岁的人都口无遮拦,“东哥”叫着叫着成了“冬瓜”。他也不恼,给鲁晓起外号“芦花”,管一位稍胖的老师叫“沙发”。当地五十多度的白酒,他喝一杯就脸红,半斤不到必醉,但他每次都喝倒,“不愿伤感情”。
2018年,原来的老师们因城区考调、考公务员等原因相继离开,荞田小学急缺老师。佘成银不愿再求助吴东,“觉得他付出的太多了”。但他还是得知了此事,自费请了三名老师去支援。
“你洋洋自得地说,我解决了一个问题,但那是用钱砸出来的,对当地教育没有改变。”他只感到自己的无力。
另一大学舍友余飞觉得,他骨子里是个悲观主义者。
吴东家境不错,虽然生活在小城市,但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还曾两次获得文化部表彰。他从小就能接触到几百种杂志报纸、大量书籍。上学前就自己拿着字典读《西游记》,小时候就用收音机听BBC,在相对封闭的年代,他早早打开了知识面。
“这是个小概率事件。”他常想,假如自己投胎稍微偏个两公里,可能就要放牛种地长大了。
“他对现实有饥饿感”
花总说自己其实愿意当一个沉睡的人,但“问题是你已经醒了,醒了你就很难忍受”。
支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乡间,他曾向学生狠狠灌过励志鸡汤,说着“努力一定能改变命运”,后来却是连自己也困惑了。
他频繁跑去“沉浸式体验”人生,试图解答困惑。
到东莞工厂里卧底,假装自己是证件被盗的小学老师,在印刷厂干活,“手被锋利的纸边拉出十来道小口子”。还设定自己是无所事事的小混混,在边境和艾滋病人聊天。
“阶层下降很容易,最关键的是你的衣着和神态。”卧底时,谈吐和气质他都可以“戒掉”,换一副二三十块钱的眼镜,镜片不要擦干净,胡子别及时刮,头发别天天洗,“要是能够坚持两天不洗澡身上有点味儿,或者在太阳底下多晒晒显得黑一点,你就成了另一个人”。这些经历中,花总从没被怀疑过。
环境对人的心理暗示作用巨大。在东莞工作仅一周后,花总路过肯德基,会觉得“那是很贵的地方”。
卧底时跟工友喝一块钱的奶茶,睡15块钱的床位,回到自己身份后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如此几次过后,他就不再需要转换心态了。卧底结束后,他会去剪个头发,“人家说你怎么黑了,我说我去海南打球了”。
由于早期投资成功,他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务自由,有条件时愿意追求并享受物质生活,注重干净和体面。但在“沉浸式体验”中,洁癖又仿佛消失不见。
在朋友们眼中,不断“搞事”是一种天赋,“他内心肯定有一个很大的洞,对现实有饥饿感”。
花总的手机屏幕最近是一张侗族青年的照片,前段时间在黔东南拍的。旅行指南《LonelyPlanet:贵州》作者袁銮在公众号“青蛙在贵州”回忆:“花总的粉丝可能不知道,他曾经花了好几年时间,在贵州采集各式各样的侗族琵琶歌,是侗歌田野录音做得最全的一个人。”
他喜欢侗歌“干净”。20年间,他斜挎着装有录音器、iPad和烟的帆布袋,去过近一百次贵州,还交往过一位当地女歌手。
他还曾在深圳龙华的劳务市场寻找一个死去的“三和大神”。离开龙华之前,他在死者“吴斌”去世的居所睡了一夜,那是个被后期隔成的小房间,空气不流通,墙上用锐器刻着一个“苦”字。他没有将这个细节当作《寻找三和死者》一文的结尾,希望减少一些负能量。
他像台球桌上被撞来撞去的白球,享受行进轨迹的未知,球杆却其实握在自己手里。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人设里,“沉浸式体验”是想主動出壳。“当你能走到别人的世界,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实际上所有事情都是可理解的,不会那么剑拔弩张。”
他甚至很多次想,演员毛坤为什么会变成世奢会风波里的欧阳坤,没有人一开始就这样,“所以你说我怎么强硬得起来”。
试图规避风险,又总是失败
花总最后一次尝试回归“正常生活”,正是在2012年的世奢会风波前。
他回到福州,找了一个负责品牌的中层职位,按部就班地工作,领工资,还在同事的安排下相亲。如果没有后来因为世奢会风波被北京警方带走,他原计划按照这样的节奏生活下去,这种生活让他感到平静。
“我一路退着走到现在。帖子删了,也不追究了。”世奢会风波前期,他不断表达意图求和,而对方报了警。
他永远记得第一次自国贸大酒店64层被警方带走的2013年9月17日,他“心如死灰”,以至于警察觉得他在故作镇定。在命运未知的二十多个小时里,他想到很多细小的事情,通知表弟过来拿自己的信用卡结掉房费,申请给女友打电话,取消中秋节之约。
每次“触碰边界”前,花总其实都会自我审查,试图规避“较大的风险”。
《杯子的秘密》便是一例。很多粉丝在他的公众号“新装腔指南”后台催更,他当时想得简单,这条视频曝光的问题不大,酒店不难改正,只要改了就能很体面地解决问题,热度最多持续两三天。但事情走向每每不如他所料,将他卷入一次次风波。
视频发出后,花总回福州避风头,住宿的过程“像做贼一样”,陈龙耀帮他预订办手续,他进门后直奔房间,避免接触酒店工作人员。
余飞则拜访了他的父母,临走时,叔叔阿姨将他送到楼下,叫他有空劝劝吴东,不要再去做这些事,安安稳稳地生活。余飞有点心酸,“他总希望自己能改变一些东西,边边角角,敲敲打打,让它更好”。
鉴表之后,官员不戴表了,但没有公开财产。发表装腔指南,本意是要拆穿装腔与恶俗,结果大家拿着指南当教材用。而曝光酒店卫生情况等来的结果是,14家涉事酒店中的12家,仅被罚款2000元或以下。
“热点总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直到大家都陷入审丑疲劳,或者抵达忍耐的极限。”2012年8月,鉴表之后,花总写道。
上了20次微博热搜后,他也曾有过错觉,以为自己一个人可以和一个行业PK,真的是“国民英雄”了。
“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我跟他同时出现在你们面前,你会觉得我们差了10岁。他家住在贵州,我是他小孩的干爹。”这是花总的镜子。
镜子的存在提醒他,他所有的沾沾自喜都依托在一种小概率上。他有过太多次经验,深知自己做不了英雄。
“打破规则是有风险的。”他说,现在的自己更注重安稳,不会再冲出去。
以前不是也说过类似的话吗?
“是,都是真心的。”他陷入沉默。
2019年1月20日,花总发布了自己的新作预告片。那是一个纪录片,他带着两个摄像兼导演,跟着一名大卡车司机从石家庄一路跟拍到成都。这是他找到的第一个愿意被跟拍的对象,他希望,大卡车司机能让人们赶紧忘记“杯子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