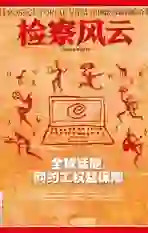对症下药:解决新型用工关系的法律路径
2019-05-22王桦宇
王桦宇
和传统劳动者相比较,目前网约工在身份认定、风险防范和权益保障上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网约车与平台之间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多数网约工甚至只能以自由职业者方式缴纳社会保险。现行司法政策对网约工是否与互联网平台建立劳动关系仍持保守态度,这更使得网约工的劳动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网约工权益保障问题也因此受到了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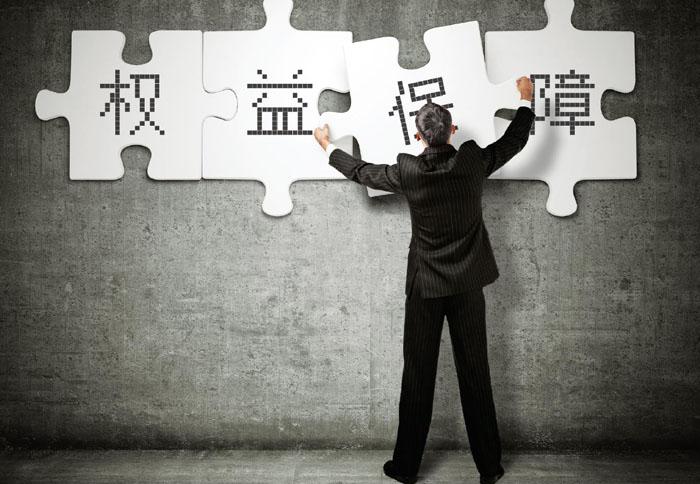
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之争议焦点
目前我国共享经济的服务提供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数量庞大。但是,一个前置性的基础问题出现了,网约行业及网约用工是否具有合法性?对于蓬勃兴起的互联网经济及相关就业新形态,现有的法律法规并不能完全地进行规制和调整。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法律法规的发展并不能完全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或者换个角度说,针对特定事物的立法本身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较为成熟,对特定事物本身和现象的评价趋于稳定后,法律法规才可以进行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基于互联网平台分派产生的网约工種属于新型的就业形态,不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对其合法性都还未产生定论,是否可以按照或者参照已有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调整和规制也有待商榷,故而法律法规在网约工层面的空白和不足也难以避免。
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网约用工形态所产生的就业关系性质认定。“网约工”是一个社会名词,不属于劳动法上正式的法律概念。现在最大的争议就是,网约工和平台之间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抑或是其他的服务合同关系?如果是劳动关系,那么网络平台或用工单位就必须严格遵照《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承担就业单位的法定责任;但是,如果仅只成立雇佣性质的劳务关系,则双方是平等的民事关系,由《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来进行调整,双方可以书面约定基于雇佣而产生的各自权利、义务和责任。
还有观点认为,网约工和平台之间既不是传统用工产生的劳动关系,也不是基于雇佣产生的劳务关系,而是基于特殊约定面向第三方产生的就业服务中介关系,但平台应当就第三方承担合理且必要的连带关系。整体而言,网约工基于劳动法上的权益保障是不明确的,一旦出现工伤意外或其他严格责任难以自己抵御风险。
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之现有规定
目前,我国国内立法并未对网约工此种就业形态专门进行规范,但是在已经出台的对部分网约行业的相关规定中有所涉及。2016年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等六部委联合出台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第18条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有合法从业资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维护和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
这一规定明确了网约平台与网约工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助于网约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网约工定位模糊的情形下,若根据《电子商务法》第9条关于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相关规定简单加以套用,则网约工需要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这也会影响对于网约工权益的有效保障。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网约工在全球各国都有所普及。优步公司(Uber)就已经进军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网约经营的态度立场也不统一,一些国家例如法国、日本、比利时等就事实上禁止此种网约车的服务进入该国市场,也未有专门的立法进行规定。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则采取观望态度并在立法上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认了网约车服务的合法地位,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印度比我国更早出台了网约车的全国性指导规定,印度道路交通部在2015年10月曾发布《网约车监管指导意见》,就驾驶员的行业培训、定位管理和驾驶员工时安全等做出明确规定。此外,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遵循判例法的传统,从而依据判例来解决相关的争议问题。
网约工权益保障之相关建议
网约工作为一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对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和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保护理念造成较大冲击和影响。传统的用工模式体现为对人身和财产的双重隶属属性,劳动法上的传统劳动关系认定则主要在于从属性、人身性和有偿性的内在特征把握和对单一性、标准性和恒定性的外在属性识别。网约工的就业形态则在内在特征和外部属性上发生了变化:一是网约工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工作及有权选择具体的工时和地点,从属性和人身性并不明显,在分配上也可通过系统自行结算;二是网约工可以同时选择多个平台获取工作并可以随时采取自愿方式灵活退出,其非标准特点也非常明显。
因此,网络平台是信息提供商、平台提供商还是雇主,在认识论上都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无论如何,网约工作为一种新型就业形态,有利于扩大就业,适应共享经济发展需求,在法律政策上应加以规范和引导,并对作为相对弱势的网约工进行适当的偏重保护,以符合非典型就业背景下劳动法的现代品格。
首先,在立法规范上,要兼顾新业态发展的规律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在保障“网约工”权益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根据实际需要,探索适合新型就业模式的行为规则。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对网约工比较集中、社会比较关注的重点领域比如网约车驾驶员、快递员等进行专门立法,单独或联合制定相关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就具体的新型就业模式的性质进行梳理,对权利义务责任进行合理的分配,并可以制定专门的行业规范和协议指导范本。
其次,在行政执法上,无论网约工与网约平台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是否有定论,网约工作为弱势群体和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都应当得到有效保障。市场监督、劳动监察、社保经办等有关部门对网约工进入劳动关系范畴和社会保险体系应秉承“宽容”态度,对于网约工自主或者网约平台申报缴纳社保持开放态度,并对网约平台公司进行适当政策指导。可考虑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平台公司更加注重对网约工的权益保护并制定合理的风险分摊机制。
再次,在司法裁判上,要根据具体的案情来对具体的网约用工形态做法律上的识别,并贯彻弱势群体保护的司法理念。一方面,要充分认识互联网经济在繁荣和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劳动就业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促进企业推动业态创新的积极性,不能不合理增加网约平台的负担;另一方面,要认识到网约工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准从属性特征的非典型就业形态,即便不能纳入传统劳动关系调整,也需要在司法政策上予以照顾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