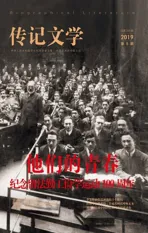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中国回忆录理论探索述论
2019-05-17徐洪军
徐洪军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新时期以来,我国出版、发表了大量回忆录作品,形成了一种“回忆录热”的文化现象。对此,学术界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部分学者对回忆录的理论问题、具体文本进行了有益的分析和探讨,积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回忆录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试图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回忆录的理论探讨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回忆录的概念
要对回忆录展开研究,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是,什么是回忆录?国内学者主要给出了这样几个概念:1997年版《现代汉语词典》条目记载“回忆录”是“一种文体,记叙个人所经历的生活或所熟悉的历史事件”。1999年版的《辞海》记载,“回忆录”是“一种叙事性文体。用叙述、描写、资料编排等方法,追记本人或所熟悉的人物过去的生活和社会活动,篇幅有长有短,带有文献性质”。刘耿生定义:“回忆录是当事者将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历史,以大脑为载体,形成记忆,再转录成文字等材料的一种文献形式。”李良玉认为:“回忆录就是记录当事人回顾自身经历所形成的文字或音像资料。”陈墨提出,“回忆录”的内容是“回忆并叙述某一段历史故事、某些社会事件以及某些公众人物或一般人物”。
这些概念共同指出了回忆录的核心内容——当事人对历史的记忆与叙述,但也各有侧重。在词典中,回忆录是一种带有文献性质的文体,而历史学者则主要强调其文献的性质。在记述的内容上,有学者只强调了对自身经历的回忆;有学者则相反,认为回忆录是对别人或历史事件的回忆;比较全面的概念则强调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本人的生命经历、别人的生活片断或叙事人见证了的历史事件。在保存的形式上,大多数学者都没有特别强调,李良玉则特别指出它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音像资料。
这里面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第一个问题是回忆录的叙事人是否必须为回忆内容的当事人?李良玉把“局外人对某种事件或事件中的人的回忆”也视为回忆录,并且指出:“这种回忆有两种情况,一是同时代的、与有关历史事件人物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根据有关见闻、印象、传说所作的回忆;二是有关历史人物的亲属的回忆。”这样的理解有些过于宽泛。有些人可能并没有参与到他所回忆的历史内容之中,但是如果他作为一个见证人,见证了他所叙述的内容并留下了印象,那么,他的回忆可以视为回忆录。但是,如果他只是从别人口中听说了这些内容甚至是道听途说,那么他的回忆内容就很难视为回忆录。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有关历史人物的亲友见证了他的生活片段,则其亲友的叙述可以视为回忆录。但是,如果亲友只是听他讲述自己的生活,则无论是以访谈的形式还是以转述的形式记录下来,其记录的内容都只能算作该历史人物的回忆录。
第二个问题是回忆录的内容,它关系到回忆录的边界问题。如果只把回忆录的内容局限于叙事人自己的生命经历,则回忆录与自传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就很难区分。相反,如果把内容界定为叙事人对其他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回忆,那么,很大一部分以自己的生命经历为内容的回忆录就会被作为自传排除在外。所以,回忆录的内容应该包括自己的生命经历、别人的生活片段、叙事人参与或见证了的历史事件。这样,回忆录按其内容就可以分为自传性回忆录(以叙事人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中心)、他传性回忆录(以被回忆人的经历为中心)和事件性回忆录(以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为中心)。当然,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回忆录还可以有其他分类方法。例如,在《现代传记学》这部具有开创性贡献的著作中,杨正润先生就将回忆录分为事件回忆录、时代回忆录、亲近回忆录、自我回忆录和复合性回忆录五类”。无论怎么分类,分类的标准需要统一,而且应该一以贯之。
第三个问题是回忆的姿态。这一点在上述所有概念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如果只是一般性地说叙事人撰写回忆录的方式是“记忆”“追记”“记叙”“回顾”等,那么,回忆录与日记有何区别?难道仅仅在于篇幅的长短、人生经历的完整与否?大量的单篇回忆录篇幅都不太长,内容也并非严谨完整。这些回忆录与日记的区别何在?其实,细细想来,日记与回忆录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撰写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的距离。回忆录的撰写时间一般要比故事内容发生的时间晚很多,而日记的撰写时间与故事时间则几乎是同步的。正是因为有了回忆录撰写时间与故事时间的时间差,叙事人在叙述回忆内容时才会产生一种回顾性的叙述姿态。这种叙述姿态可以给回忆录带来日记所没有的浓厚的历史感、叙事人个性人格的自我认知与省察以及由怀旧而产生的审美体验。
第四个问题是回忆录的产生方式。关于这一点,李良玉给出的概念有所显示:回忆录不仅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音像资料。也就是说,回忆录有可能是叙事人自己撰写的,也可能是自己口述别人记录整理的。那么口述性回忆录与口述史有何区别呢?在这一点上,陈墨的分析值得重视。他认为,口述史与口述回忆录的区别在于:一、口述史是由采访人与受访人合作完成的,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口述回忆录的录音文本整理人则主要是采访人的助手;二、口述史的内容是采访人与受访人合作建构的产物,而口述回忆录却主要是受访人的个人回忆及自语独白;三、口述史是采访人根据提纲对受访人的一种主导性访谈。在此过程中,他不仅控制着话题的走向,而且提出质疑和考证、分析与评说。这一观点基本上对口述性回忆录和口述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辨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如果要给回忆录下一个定义的话,那就应该是:回忆录是当事人以一种回顾性的姿态对自己参与的历史进行真实记录的文字或音像资料。“当事人”是主体要求,“回顾性姿态”是本质特征,“参与的历史”是叙述的边界,“真实记录”与其说是对文本的客观确证,不如说是对叙述态度的真诚要求,“文字或音像资料”是保存的形式。
回忆录的价值
学者们对回忆录的价值有着较为充分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回忆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回忆录本身的史料价值。无论是专门研究史料学的学者还是一般的历史学者,大家对回忆录的史料价值都颇为重视。王海光认为:“复原历史的工作难度很大,仅仅留有大量文献档案材料和影像资料是很不够的。一则是这些材料往往是经过选择处理的,有些历史细节可能就被过滤掉了。二则是这些材料对当时历史场景往往忽略不记,后人体会当时那种生动具体的历史现场感比较困难。三则是这些材料是对当事人已经表现出来的言行记录,在这些当事人言行中的情态、感受和复杂的思想动机,是不容易把握住的。这就需要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作一补充,才能窥其历史全貌。”后来在《回忆录:当代人负有存史责任》这篇文章中,王海光又补充了一条:“档案文献对历史的记载是有限的,文字记录缺失,文字记录不存,文字记录有误,这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都是屡见不鲜的。”总体来讲,回忆录具有文献档案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在保存历史方面能够成为文献档案的有益补充。
虽然回忆录具有存史功能,但它们的价值是不能等而视之的,不同的回忆录往往具有不同的史料价值。在李良玉看来,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这件事的史学价值。事件越重要,回忆录的价值就越大:二是当事人的参与程度。回忆者越是处在这件事的核心地位,发挥的作用越大;他的回忆的价值就越大;三是当事人回忆的准确性。准确性越高价值越大。
因为回忆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所以,一些学者将其视为第一手资料。陈恭禄认为,回忆录是“当事人回忆,是第一手资料”。但李良玉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史料学上确定是否第一手资料的标准,不是该史料所叙述的是否确实,也不是该史料所记载的是否亲身经历,而在于该史料是否事发时留下来的原始文字资料或者物件资料。”两位学者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对“第一手资料”概念的理解不同。在李良玉这里,第一手资料必须是原始资料,不能是事后的追忆。如果按照李良玉的界定,第一手资料要少很多,因为很多事情并没有留下原始资料。陈恭禄理解的第一手资料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比较相似,它大概是指资料持有人最先搜集整理的或者是他本人经验所得的。按照这样的理解,很多回忆录是可以视为第一手资料的。
回忆录第二方面的价值是就史学研究而言的。李良玉将回忆录在这一领域的价值总结为八个方面:不可取代性、真实性(大部分回忆录是可以信赖的)、有较高的可信度、可以解决没有文字记载的问题、可以纠正文献资料的错误、能够揭示当事人不承认的事实、能够揭示极有价值的真实细节、是作出历史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这种归纳对于认识回忆录的价值的确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仔细审视,它们似乎还可以被进一步概括为四个方面:大部分回忆录真实可信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解决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问题、可以纠正一些档案文献的错误、可以参与历史的评价。
回忆录第三方面的价值是其对于叙事人的价值。耿化敏认为:“回忆录的根本价值在于:为私人提供了一个独立的个人化的叙事空间。”在这样一个叙事空间里面,“‘原本’的自我与文本自我之间”“流连顾盼”,“作者对往日生平”进行“不自觉的感情烛照”,在此过程中,叙事人对自己的个性人格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认识”。这一价值主要是针对自传性回忆录而言的。叙事人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往往会以一种回顾性的叙述姿态,穿过历史的隧道,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整体观照,借以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或者是成败得失。在此意义上,我们虽然不能认为回忆录就与法国著名学者菲利普·勒热讷界定的自传一样,能够建构自己的个性人格、探索自己的内心成长,但是一般意义上讲,它们应该具有相似的功能。
回忆录第四方面的价值在于能够建构起一个流动变化着的传主形象。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身后往往会有很多回忆录对其进行悼念缅怀。但是,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回忆录往往会留下一个不一样的传主形象。这些有着共同特征却又形象各异的传主形象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传主本人的多个侧面,也让读者看到了同一时代不同立场的人,以及不同时代同一立场的人对他产生的不同评价。比如鲁迅去世以后,有三个时间段出现了大量的回忆录:一个是鲁迅去世的1936年,一个是鲁迅诞辰80周年的1961年,再一个就是鲁迅诞辰100周年的1981年。这三个年份其实就是三个时代,在不同时代的回忆录中鲁迅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位回忆者在实现返照历史镜像的映射中,都在以自己的语言呈现了一个存在过的鲁迅”。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价值以外,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回忆录的创作也可以成为观察历史的一个视角,这指的是回忆录创作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本身的价值。这里面可能包括这样几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创作回忆录?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而不是别的时间创作回忆录?他都回忆了什么?有无遗漏或错误?这种遗漏或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回忆录的创作现象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有何关联?等等。例如,20世纪的80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大批作家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回忆与随想文丛”、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骆驼丛书”,茅盾、巴金、胡风、丁玲、冰心、夏衍、臧克家、阳翰笙、徐懋庸、陈白尘、赵家璧、曹靖华、许杰、王西彦、姚雪垠、梁斌、陈学昭等作家的回忆录著作和回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胡风、丁玲、沈从文、冯雪峰、瞿秋白、郁达夫、田汉等作家的文章、著作大量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如此集中地、大规模地发表、出版作家回忆录,可以说前所未有。这样一种十分突出的文学史现象值得认真研究。它不仅对于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理解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生态甚至时代氛围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回忆录的真实性
作为一种史料,人们自然会对回忆录的真实性提出要求。“回忆录的基本特点是真实性,这可以说是它的本质。”一部分学者对这种真实性的要求十分严格,认为“回忆录不属于文艺作品,不能虚构夸张,必须实事求是,若有不实回忆,则回忆录就失去了任何价值,只能算作稗官野史,甚至连阅读的价值也没有。”有人甚至干脆将那些不真实的回忆录排除在回忆录的范畴之外。
对于以上观点我们有必要做一些分析。
首先,“真实性”是不是回忆录的本质?对于回忆录研究而言,将“真实性”界定为回忆录本质的观点是不合适的。如果将“真实性”界定为回忆录的本质特征,那么,“不真实”的回忆录自然就会被排除在回忆录的范畴之外。这时就会出现一些从理论上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真假的问题如何判断?如果一部回忆录有的地方是真的,有的地方是假的,又该如何处理?有学者认为,可以写出真实的回忆录对其进行驳斥或者确证。但是,谁又能确保写出来的回忆录就一定比别人的真实呢?有学者或许会说,可以利用文献档案对其进行考证核实。或许很多回忆录的真实性问题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获得解决,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问题都能够找到可靠的文献档案。据说,1936年红军走完长征时,鲁迅曾经发电报表示祝贺。电报是只有鲁迅一个人还是鲁迅与茅盾共同署名?说法不一。根据回忆录,就这一问题,臧克家和茅盾的侄女沈楚都曾经问过茅盾,但是他们记载下来的答案却互相矛盾。臧克家的回忆录《往事忆来多》说落款的只有鲁迅,而沈楚的《患难见真情》却说茅盾也署了名。因为鲁迅的电报原文至今没有发现,而茅盾本人也已经去世,以至于孰是孰非连胡绳先生也无法判定。根据以上分析,将真实性界定为回忆录的本质特征并因此将“不真实”的回忆录排除在外,对于回忆录的研究而言似乎不太合宜。
在谈到回忆录的本质特征时,李良玉认为回忆录的本质是“记忆资料”而非真实性。就学术实践而言,这一观点显然更具合理性。但是,如果说“记忆资料”是回忆录的本质,那么日记呢?“记忆资料”是不是它的本质特征?如果日记也具有这样的特征,那又怎么能说“记忆资料”是回忆录的本质特征呢?在我们看来,回忆录的本质特征既不是“真实性”也不是“记忆资料”,而是由回忆录的撰写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的时间差带来的一种回顾性的叙述姿态。因为这样一种回顾性的叙述姿态,回忆录的真实性就需要谨慎对待;也是因为这种叙述姿态,回忆录与日记得以区别;还是因为这种叙述姿态,很多回忆录不仅具有一种浓厚的历史感,还往往带有一种怀旧的审美体验。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回忆录就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资料,它还可以成为一种文体,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被广泛阅读,比如鲁迅的《朝花夕拾》。
其次,回忆录能不能虚构?刘耿生的观点是绝对不允许的,大多数学者都持反对态度。大家反对回忆录进行虚构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回忆录的史料应用,没有人会愿意采纳存在虚构的史料作为论证的依据。但是,如果从回忆录的创作本身来看,事情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如果不允许回忆录使用虚构和想象,那么,作者如何“还原”他几十年前的生活场景?在进行回忆录的创作时,作者“在时间轴上来回跳跃、再现可信的对话、在场景描写和概述中不停穿梭、控制故事的节奏和张力——通过这些,回忆录作者成了娴熟的故事作者,让读者全神贯注”。在此意义上,美国学者朱迪思·巴林顿认为:“回忆录是一种混合的形式,兼具小说和散文的要素。”因此,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批评回忆录对几十年前的历史场景作小说式的精描细画是一种不真诚,那并不能说明作家的道德存在问题,而只能说明我们对回忆录的理解还存在偏狭。当然,允许在回忆录创作中进行虚构和想象,并不意味着容忍对历史进行故意的歪曲。虚构和想象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塑造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真实的自我,而并非允许通过歪曲事实来掩盖历史的真实。在回忆录中,虚构和想象在发挥其作用时要受到历史真实的限制。
由于回忆录存在不真实的可能性,所以,在运用回忆录作依据时需要进行鉴别。在这一方面,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撰写了多篇论文进行阐释,甚至提出“尽信回忆录不如无回忆录”的说法。陈先生的这一观点还有这些论文引起了周海婴、罗飞两位先生的积极回应,罗飞先生曾经撰写了多篇论文与之商榷。但是仔细阅读下来,感觉整个争论的过程一直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常常纠结于一些具体的回忆录文本上面。陈漱渝先生提出的回忆录需要鉴别的观点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辨析。从个人的理解来看,回忆录自然是需要进行鉴别的,根本无法确保哪一本回忆录是完全真实无误的。
那么回忆录失真的原因何在呢?将学者们的观点总结起来大概有这样四点:一是人的记忆能力的有限性。人不可能记住所有经历过的事情;二是人的记忆的选择性。由于生理机制与思想立场的原因,人们会对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进行选择性记忆;三是自我合理化的倾向。“平心而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里面。这种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四是故意掩盖事实,甚至扭曲事实。有些人可能会为了推脱责任或打击别人而故意如此。这样的例子在“文革”期间应该比较常见。这四个原因是按照主观性逐渐加强的顺序进行排列的。记忆的有限性是无法克服的,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回忆录的真实性就会永远成为一个问题。记忆的选择性既可能是因为无意识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有意识的。在创作回忆录的时候,不仅要尽量克制有意识的选择性回忆,还要尽可能地提醒自己进行客观叙述。自我合理化既然是人性使然,所以,只要作者不违背原则,不故意掩盖、扭曲事实,读者一般还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在研究回忆录时还是要保持谨慎,因为这有可能会关系到读者对被回忆人历史形象的想象与建构。
回忆录与周边文体的关系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文本可以算作回忆录的问题,也就是说,展开研究之前,往往需要弄清楚回忆录的范畴是什么。否则,如果连自己研究的文本是不是回忆录都无法确定,下一步的工作也就难以开展。
在《回忆录及其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中,李良玉认为,回忆录包括以下九种材料:自订年谱,自传,据新闻采访整理、写作而成的传记类著作,专家学者协助记录整理的回忆性文稿,特定环境中留下的自述材料,当事人所写的单篇回忆文章,以诗词歌赋等文学题材的题解、注释等形式出现的回忆文字,以机构、组织或与当事人没有关系的个人的名义发表的、带有例行公事性质的纪念或回忆文章,传记著作中包含的回忆录成分,或者是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传记。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对回忆录范畴最为详细的界定了。但是,用列举的办法来界定一个概念的范畴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列举得再多也有可能有所遗漏。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符合回忆录定义的历史材料都能算作回忆录。
在李良玉上面的概括中,他是把自传归入回忆录进行研究的。但是在自传与回忆录的关系方面,学者们却有不同的意见。杨正润先生认为:“回忆录的内容通常比较分散,不像自传那样集中。”同时,“自传写作中难以避免的收集、查阅、核对和研究资料等种种繁难,在自我回忆录的形式里大都被避免或简化”。所以,他认为:“自我回忆录以自我为中心,属于自传的范畴。”对于杨正润的这些观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李亚男指出:“杨先生在他的专著中讨论回忆录与自传的关系时犹豫乃至矛盾,主要原因是他谈及的回忆录过于宽泛而又庞杂。”
在辨析了杨正润的观点之后,李亚男对自传与回忆录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自传应该是作者自觉地对个性人格历史的反省追索,而回忆录则是不自觉地对个性人格构成的流露展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传是历时展开传主个性人格的成长变化,而回忆录是共时展开传主个性人格的结构特点。”这种观点应该借鉴了勒热讷《自传契约》中的相关理论,阐释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一观点似乎有将回忆录等同于自传性回忆录的倾向,这样就把他传性回忆录和事件性回忆录排除在外了。
与李亚男正好相反的是,在区分回忆录与自传的关系时,陈墨则是把自传性回忆录从回忆录的范畴中排除在外。他认为:“回忆录与自传的区别是,回忆录叙述的主要对象通常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与作者相关的其他人物或事件。自传中当然也会涉及时代背景、社会关系网络、与他人的交往并接受他人的影响等等内容,但传主即自传作者本人是这一作品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结点。”从对中国回忆录文本的考察还有对回忆录概念的界定来看,这种观点显然也是不够全面的。
学者们之所以对自传、回忆录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意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在中国,虽然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很多时候却很难区分。“回忆录同自传有时很难区分……自传的许多特点,回忆录基本上也是具备的。”
由于受到西欧基督教传统的强大影响,菲利普·勒热讷认为:“自传不仅仅是一种内心回忆占绝对优势的叙事,它还意味着一种把这些回忆加以组织,使之成为一部作者个性历史的努力。”它是作者自我救赎的一种手段,是一种“神圣的写作”,是“对上帝的发现和皈依”。热心提倡回忆录写作的美国学者朱迪思·巴林顿认为:“自传是关于一生的故事:‘自传’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作者会设法捕捉一生中所有的重要因素。”与之相比,回忆录“并不复述生活的全部。回忆录写作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选择能将整部作品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个或多个主题”,它带有“明显的主题限定”。“大多数人一辈子只写一部自传,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你可能会写很多回忆录。”所以,从西方学者的理论来看,回忆录与自传的主要区别有两点:自传是面向作者内心的写作,是对作者个性历史的建构;回忆录是对个人所属的社会历史的个人见证。自传是关于一生的故事;回忆录是一种阶段性的主题写作。其实相似的观点郁达夫早在1935年就提出过,他认为:“自传是己身的经验尤其是本人内心的起伏变革的记录,回忆记却只是一时一事或一特殊方面的片断回忆而已。”郁达夫同样看到了两位西方学者总结出来的两点区别。
与前面的观点相比,从理论上来讲,郁达夫与两位西方学者的观点似乎更为合理。但是这也仅仅是理论层面的东西。如果具体到中国回忆录创作的实际来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一般说来,自传和回忆录在中国的分别并不太大,通常用‘自传’这个名称的较少,而用‘回忆录’的较多。”所以,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自传与回忆录并没有严格的文体区分,而且,由于回忆录不仅包括自传性回忆录,还包括他传性回忆录和事件性回忆录,因而具有更大的外延,所以,自传也就很自然地应该被包含在回忆录之内。
除了自传以外,有些学者还探讨了回忆录与口述历史的关系,从上面我们分析的四个方面来看,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学者对回忆录的一些主要内容大体上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是,这种探讨显然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首先是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并不太多,目前只有杨正润、李良玉、陈漱渝、王海光、陈墨、李亚男等有限的几位。其次,由于对回忆录的理论探讨在中国大陆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筚路蓝缕,开拓实属不易,很多问题还没有能够深入进去,一些问题一直停留在细枝末节的纠缠上。最后,理论探讨与中国回忆录的创作实际结合得还不够紧密。不少观点还基本停留在理论推演的层面上,而不是从中国回忆录的创作实际总结归纳而来。
注 释
1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 《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3 刘耿生:《试论回忆录和口述档案》,《档案学研究》 2001年第2期。
4 李良玉:《回忆录及其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社会 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6 李良玉:《回忆录及其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社会 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7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424页。
8 陈墨:《自传、回忆录与口述历史》,《粤海风》2014 年第3期。
9 张月:《 回忆录与“公器意识”——“回忆录热”三 人谈》,《北京日报》2008年2月18日。
10 王海光:《回忆录:当代人负有存史责任》,《社会 科学报》2007年3月22日。
11 李良玉:《回忆录及其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社会 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2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232页。
13 李良玉:《回忆录及其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社会 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基于聚居动态进化理论的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以湘西地区山背村为例 张志强 谭益民 许 程 等2018/03 71
14 李良玉:《回忆录及其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社会 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5 张月:《回忆录与“公器意识”——“回忆录热”三 人谈》,《北京日报》2008年2月18日。
16 李亚男:《自传与生平回忆录关系初论——与〈现 代传记学〉作者杨正润教授商榷》,《山西师范大学 学报》2012第5期。
17 张大海:《鲁迅的镜像——通过回忆鲁迅的文章谈鲁 迅形象的变迁》,《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
18 何东:《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1985年,第203页。
19 刘耿生:《试论回忆录和口述档案》,《档案学研究》 2001年第2期。

21 李良玉:《回忆录及其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社会 科学研究》2004年第1期。
22 朱迪思·巴林顿:《回忆录写作》,杨书泳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23 朱迪思·巴林顿:《回忆录写作》,杨书泳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24 张月:《 回忆录与“公器意识”——“回忆录热” 三人谈》,《北京日报》2008年2月18日。
25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第422页。
26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第426页。
27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第 428页。
28 李亚男:《 自传与生平回忆录关系初论——与〈现 代传记学〉作者杨正润教授商榷》,《山西师范大学 学报》2012年第5期。
29 李亚男:《 自传与生平回忆录关系初论——与〈现 代传记学〉作者杨正润教授商榷》,《山西师范大学 学报》2012第5期。
30 陈墨:《自传、回忆录与口述历史》,《粤海风》2014 年第3期。
31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第417页。
32 菲利普·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页。
33 朱迪思·巴林顿:《回忆录写作》,第5-6页。
34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第6卷, 广州: 花城出版社,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3年版,第284页。
35 张瑞德:《自传与历史:代序》,《中国现代自传丛书: 资平自传》,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版;韩彬:《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