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新闻搭车”现象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2019-05-15邵超琦
邵超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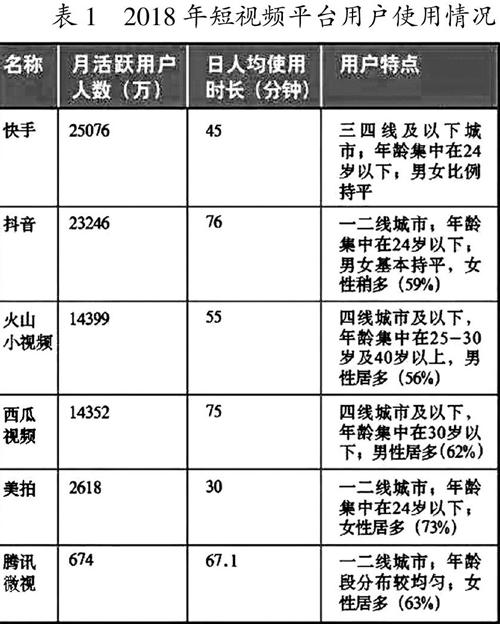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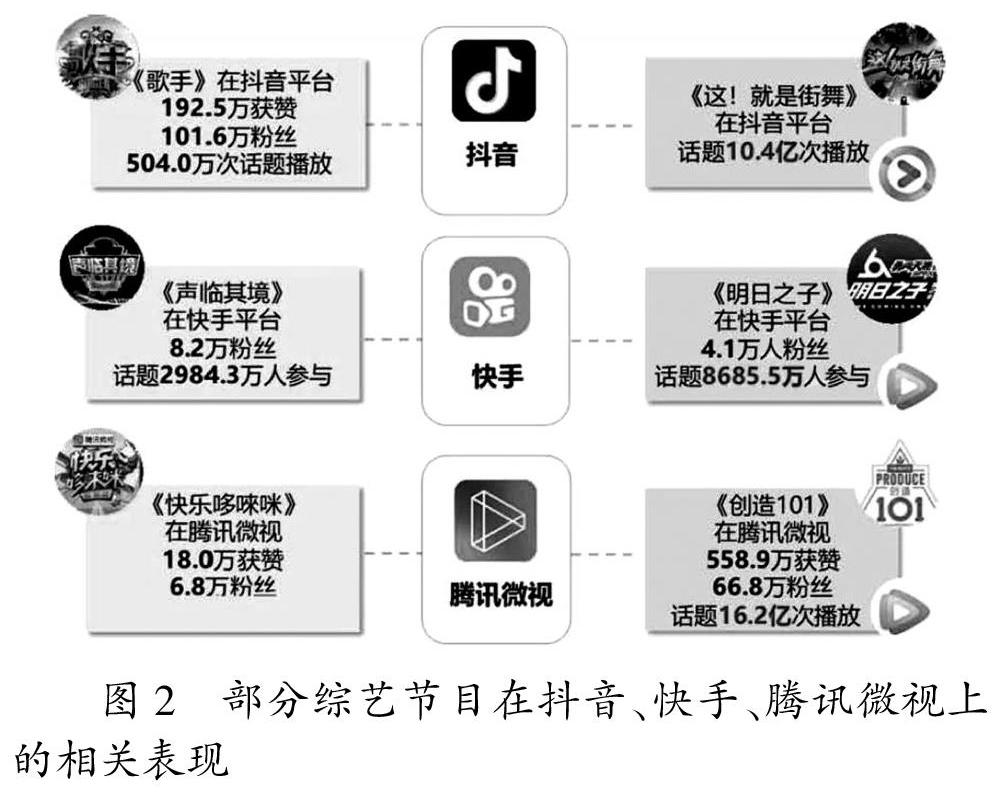
[摘要]重共鸣、轻真相,长情绪、短记忆的后真相时代,一件突发性事件可以在互联网瞬间引爆舆论,在官方还未有所回应之前,一系列主体相似、内容相关的事件接连爆出,甚至引发二次舆论,新闻出现“搭车”现象。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媒体议程设置失焦和网络受众的不理性,造成后真相时代的“新闻搭车”现象频发。而主体公信力下降、网络民粹主义盛行舆论引导不力、议程失焦、网络受众缺乏理性,是“新闻搭车”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要减少“新闻搭车”现象,必须从政府、媒体和公众三个方面提出解决之道。
[关键词]后真相;新闻搭车;原因分析;对策分析
一、后真相时代的“新闻搭车”:情绪感染大于客观事实
“后真相”这个词最早可追溯到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中批判了海湾战争政府操纵媒体,从而使美国大众“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世界”。2004年,美国作家凯伊斯提出了“后真相时代”(Post-TruthEra)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社会不存在真实与谎言的清晰界限。介于真实与谎言之间,存在着一种情绪化的第三种现实。2016年11月,英国《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定为2016年年度词汇,意为“陈述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力弱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的情况”。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传播已经演变为一种情绪传播,情感正取代理智逐渐成为信息内容本身。与此同时,真相在不断地被掩盖、消解、忽视,但它依旧存在,只是不再那么重要,因为人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可以为情感所接受的“真相”。
后真相时代形成的一个主要背景便是新媒体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传受平权”。当一个社会事件发生,真相往往尚未浮出水面,官方还未给出明确回应,而公众已经在社交平台通过发文讨论、点赞回复进行情绪化表达,将舆论推向高潮。这时主题相类似、与主体相关联的新旧大小事件便如同磁铁急速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新闻搭车”现象。喻国明教授较早指出此类现象为“新闻搭车”,即“当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到主体新闻事件时,与此地域相关的、以往难以受关注的问题集中爆发出现在公众视野,举报人会趁社会注意力和各方面力量聚集的时刻,寻求解决自身问题”吧。
二、“新闻搭车”现象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公信力下降,网络民粹主义盛行
如果新闻当事人身居要位或身份敏感(如政府官员、演艺人员、网红、教育从业者等),那么,他们的被关注度就要高于其他人。当媒体新闻内容具有较强的新闻价值和刺激性,特别是新闻涉及官员受贿、医疗事故、学校教育等与价值观念社会管理、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时,一些网络上不起眼的细节也能立即打开无法预知的后果的大门,从而引发大量的关注和高热度的话题讨论,掀起一波又一波舆情浪潮。在新闻主体事件发生后,新闻真相的水落石出往往需要时间,政府为了控制舆论发展,通常会采取删帖、屏蔽和撤热搜等强制性手段来打造舆论的“沉寂化”。根据回旋镖效应,政府越是抑制,大众挖掘真相的心情就越迫切。舆情长期的累积,容易使舆论从事件本身转移到对政府发言的不信任与质疑,从而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影响,使得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民粹主义话语强占,正是看到舆论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利用信息传播中所谓的破窗效应,通过爆料、过激言论、假消息假事件等引起網民关注,从而控制舆论走向”。当舆情不受控或受到故意引导时,“新闻搭车”的概率便会大大提升。
(二)媒体舆论引导不力,导致议程设置失焦
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大众媒体通过提供相关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引导人们去关注媒体想要呈现的事实。在以前,传统媒体作为权威的信息发布者、唯一的议程安排者和最终的决策发言者,不仅可以通过设置议程有效地把控舆情,还可以提供语境引导公众的思考模式。在新媒体语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的获取由简单的、单向性的线性模式转化为复杂的、双向性的网状模式。公众不只是被动地接收来自政府、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还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主动选择和搜寻自己感兴趣的各种信息,社交媒体也为公众提供了“发声”“讨论”的渠道和平台。议程的设置变为由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公众三方一起参与的过程,议程设置的效果出现了大大的弱化现象。
在后真相时代,“反转信息、洋葱新闻以及网络谣言等网络信息传播的问题症候已经成为互联网的日常呈现”。不可否认的是,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的主体事件提高了一些议论度低、尚未解决的同地域或同类型事件的曝光度,加速了“新闻搭车”事件的解决。但同时,部分夹带着自身价值取向的自媒体文章以及一些添油加醋、鼓动情绪的不实谣言乘虚而入,使得舆论导向背离客观事实,加大了舆论治理和事件处理的难度。微博大V和自媒体纷纷就自身立场表明观点,引发狂欢群众的站队和围观。议程不断扩张不断更改,导致“议程失焦”,牵扯的事件越来越多,于是开始“新闻扎堆”。这对主体事件问题的解决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因过多的信息干扰核心议题的深入,造成舆情声势浩大而调查停滞不前的现状。在后真相时代,一件又一件新闻事件的爆出不停地干扰公众的注意力,甲事件的后续还没有结果,立刻又有一个乙事件爆出转移公众的关注焦点,随后又会有丙、丁事件覆盖之前的事件。情感很多,真相太少,公众舆论找不到释放的通道,于是将突破口转移到同议题事件或新闻事件的其他相关事件,使得“新闻搭车”现象愈演愈烈。
(三)网络受众回归“本我”,缺乏理性
有关新闻之所以能够成功“搭车”,与受众的心理也密不可分。一方面,情感共鸣为相关新闻事件“搭车”提供了某种便利。近年来,虐童案件层出不穷,人们“唯恐自己成为这种行为的牺牲者”,出于心理上的恐慌,又苦于真相求而不得,于是将焦点转向相关热点事件,使舆论保持热度。因此,北京“红黄蓝”事件爆出后,一系列涉及军方、教育制度、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蜂拥而出。公众希望多方輿论合力造成浩大的声势,对政府及媒体施加压力,倒逼真相。
另一方面,认知偏见给予虚假消息滋生的空间。社交媒体平台、智能算法、精准推送等合力形成了一个认识过滤的机制。如同麦克卢汉所言,社交媒体让社会回到了一个重新部落化的状态。在社交平台中,个体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物都是依据喜好与兴趣过滤筛选而来的,久而久之,那些不以致或是不感兴趣的消息经由你的社交圈子被过滤掉,消失不见。那时人们就会陷入回音室式的信息闭环社会之中而不自知,认知偏见随之加深。通常“被搭车”的案件都是受众围观周期长、讨论激烈且真相没有及时公布的事件。公众显然对政府、企业等官方的回应存在明显的怀疑和抵抗,这就给部分新闻发布者爆料类似事件创造了条件。不实信息操纵着民众情绪和网络焦点,将虚拟的情绪传播转化为媒介审判与网络暴力。其实只需多方调查稍作比对便能辨别真伪。但在这样的特殊节骨眼上,由于之前事件所带来的认知,受众对此深信不疑,不实消息混入其中,也使得舆论更加情绪化焦灼化。
三、“新闻搭车”现象的对策分析
一定程度的“新闻搭车”能够引起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有助于问题的尽快解决。然而在很多的“新闻搭车”现象中,逐渐演变出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网络民粹主义,使新闻传播产生反功能的现实性意外后果,舆情陷入恶性循环,公众处于一种舆情焦虑之中,失去信任,怀疑一切,不利于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和社会稳定。彭凤仪教授认为:“要防范和应对媒体的意外后果,化解和消除传播危机,可以从建立事态预防机制传播规范机制、危机管控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入手。”呲外,要减少“新闻搭车”的出现频率,笔者认为还应当从政府媒体和公众三个方面来寻找应对之策。
(一)政府及时把握话语权,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
现在的信息发布形式似乎有这么一种套路,知情人或是当事人在网络平台发布,随后引发公众大量讨论与转载,然后传统媒体介入其中,经过调查取证,进行报道,最后政府部门介入其中,进行发声,回应相关事件或解决相关问题。政府似乎总是最后出面,普通公民既无法参与到决策中去,往往在长久的等待中等不到满意的结果。知情权作为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之一,是公民行使表达权利、监督权利的必要条件。如果知情权得不到满足,长此以往,受众会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对政府部门的言论和观点进行逆向思考和理解。政府应当联合传统媒体,及时把握话语权,运用新媒体技术,通过政务微博政府公众号等平台,第一时间公开信息,及时同公众进行沟通,了解公众的需求与疑惑。领导干部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六个及时”为准则,多上网了解民意,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同时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一些存在较大争议的事件中,发言人的缺位无疑是错过了与公众交流解释的最好时机,虽然官方以文字和图片信息第一时间做了公告,但是这种沟通是单向的,这种见事不见人的发言,在情感上的沟通几乎为零。危机关头,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不仅是官方信息的回应,更是一种官方态度、官方立场的回应。后真相时代,公众最关心的不是真相,而是一种对真相的态度和解读。政府应在新闻事件被“搭”注意力的顺风车之前,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降低“新闻搭车”的可能性。
(二)媒体要加强舆论引导,避免舆情积压
在舆论风暴面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各司其职,相辅相成。传统媒体因为其守门人制度,为确保消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消息的发布总是滞后于新媒体。新媒体时代,技术赋权,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化,传统媒体的地位一度下滑,甚至面临失语的现象。然而,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与专业性依然是新媒体无法媲美的。在舆论爆发期,传统媒体更应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坚持深度调查和持续报道,探索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因,引导社会舆论往正确的方向发展“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另外,新媒体依据其特有的便捷性、及时性,实时向公众公布最新结果,要避免虚假消息乘虚而入、混淆视听。媒体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中折射出的大众心理问题,及时进行有效排解,避免舆情积压,使“新闻搭车”有机可乘。
(三)公众需继续提高媒介素养,理性看待“新闻搭车”
如今,受众常常对传播媒介中不合理的解释提出质疑,主动探索追寻事件真相,这显然是媒介素养提升的结果。2011年出版的《真相》一书的封底写道:“现在是新闻最多的时代,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但追究真相更难。新闻素养已经不单单是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素养,在新媒体时代,公民在享有发言权的同时也应承担提高“新闻素养”的义务,做有判断力的信息公民。后真相时代,由于社交媒体的去中心性和匿名性,发声渠道多元,信息鱼龙混杂,造谣成本降低,信息的真实性有待考究。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信息,而是信息太多太滥,无法分辨。因此受众需要提升媒介的批判意识形成媒体信息的辨别能力,避免被操控,成为信息的囚徒。
理性观望、全面而客观地浏览信息和听取意见,避免“情感”站队,避免盲从盲信,对“新闻搭车”现象会有良好的导向作用。后真相时代,当主体事件引发舆论热议时,人们讨论的重点已经发生偏移,比起所谓的真相,似乎情感上的共鸣更加重要。“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众不是想看你怎么表达你自己,而是想看你怎么表达我。”在注意力经济社会,不少意见领袖为了吸引眼球,以诱导性的标题和言语引导受众,形成舆论共同体。参与舆情讨论的网民面对主体事件,往往缺乏一种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因此,在“新闻搭车”现象面前,我们必须保持弗洛尹德所说的代表理性与常识的“自我”,以防情绪和立场引导思维甚至行动,从而避免在网络环境中的“狂欢”行为增加“新闻搭车”的概率。
四、结语
“新聞搭车”现象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大量关注,有助于增强舆论声势,引起政府和媒体的关注,从而加速主体事件的解决。但后真相时代频繁的“新闻搭车”现象也加剧了新闻的同质化和碎片化,过度消费了受众的注意力与情感,不仅会引起受众的视听疲劳,还会加剧社会的心理恐慌,更会导致舆论生态的固化和恶化。在信息繁芜的后真相时代,突发舆情是不可避免的,“新闻搭车”现象也无法杜绝。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并非束手无策,而需各方齐心协力:政府及时准确把握话语权,完善网络发声制度,给予公众诉求释放的渠道;新旧媒体通过互动联合形成一个良好的舆论引导机制,避免舆情的积压;受众只有不断提高自身媒介素养,不被虚假非理性的信息所左右,理性看待“新闻搭车”,才能进一步构建起良好的新闻传播新秩序。
参考文献:
[1]江作苏,黄欣欣.第三种现实:“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伦理悖论[J].当代传播,2017(4):52—53+96.
[2]林斐然,程媛媛.庆安枪击案舆情“拔萝卜带泥”N].新京报,2015—05—14(A16).
[3]陈晓莹.网络传播中的“新闻搭车”现象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7.
[4]陈龙.话语强占: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实践[小国际新闻界,2011,33(10):16—21.
[5]解迎春后真相语境下网络信息传播的问题症候与应对策略[I].东南传播,2018(11):126—127.
[6]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7]彭凤仪.论新闻传播的意外后当代传播,2013(6):18—20.
[8]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