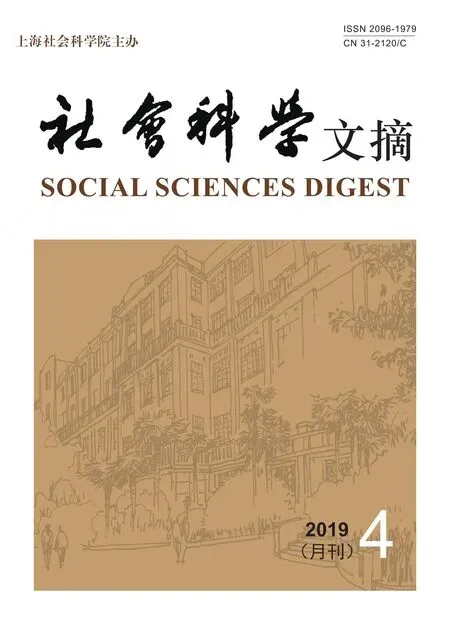阶层固化:基于历史与国际比较视角
2019-05-09
引言
学术界关于阶层流动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寒门难出贵子”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暂且不论“阶层固化”是“客观现实”“主观现实”或“话语现实”,媒体的大肆报道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本身反映着各界对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的不平等的不满以及实现向上流动的渴望。然而,这些报道和争论作为一种话语影响深远,甚至本身便可成为阻碍阶层流动的重要机制,其作用形式有两种:一是处于中下层的人们认为,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可能自暴自弃,甚至可能演变成有反社会的倾向;二是处于中上层的人们可能认为即便躺着睡觉也能享有权力与金钱,因而可以不努力。不管是消极怠工,还是坐享其成,都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本文对阶层固化讨论进行简要的回顾,并通过历史和国际比较视角对“阶层固化”进行重新审视,以期进一步讨论行动者和制度的为与不为及所带来的结果上的差异。
简单地说,阶层固化就是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趋于停滞。在具体研究中,代际流动通常受到更多关注。父母的阶层地位如何影响或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子女的阶层地位,便成为判断阶层是否固化的重要依据。当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越来越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便认为是阶层固化。
阶层固化:历史与国际的视角
1. 传统、转型与现代社会的情况:历史视角
在传统社会,“子承父业”某种程度上是作为褒义词而使用的。当时普通民众的社会等级以年龄为划分标准,即所谓长幼有序。人们地位与权力的获得是依靠世袭,而非后天的努力,是出生这一先赋因素决定的。世袭是阶层固化的静止状态,也是极端状态之一。中国自古是一个皇权社会,政治资源对民众来说可望而不可及,官民之间等级森严,即使上下级官员之间的等级也不可逾越。尽管有科举制度,但因这种制度性安排而实现的社会流动微乎其微。
从历史视角审视,几乎可以认为阶层固化是社会的常态,而阶层流动则主要发生在朝代更替或转型社会阶段。转型社会,阶层流动剧烈,但这仅仅出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转型一旦完成,进入现代社会后,阶层又会出现固化的倾向。在传统社会,阶层处在固化状态,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垂直流动非常少。在现代社会,阶层流动相较于转型社会大大减少,但国家与市场给社会各阶层所提供的机会比传统社会还是多得多,其阶层流动也比传统社会多得多。由此可见,以往研究所揭示的“阶层固化”结论是有前置条件的,主要出现在转型社会的后期与现代社会。但与传统社会相比,转型社会与现代社会禁止人们跨越阶层边界进行流动的正式制度与规则已经大大减少,尽管实际上依然存在着各种制度和非制度力量有形或无形地限制了人们的代际和代内流动。因此,相较于转型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但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则又是一个阶层流动的社会。

图1 非暴力革命形态下的社会阶层流动频率变化
2. 其他社会的情况:国际视角
盖茨比曲线绘制的是世界上一些国家不平等程度与代际社会流动状况的关系,其纵轴叫做代际收入弹性,用来指示父辈的收入差异如何影响子代的收入差异。代际收入弹性越大,代际流动性越弱,阶层固化程度越高。因此,纵轴也被称为代际流动性。盖茨比曲线的横轴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与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即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代际流动性越差。
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于2012年1月12日向国会提交的总统经济报告中曾引用了科拉克的这一研究成果。指出:美国的代际流动性不如其他发达国家,且不平等程度从1985年至2010年增加的同时代际流动性减弱。
与克鲁格报告相呼应的是,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中直指,“现在美国人从底层奋斗到上层的机会少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美国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上层群体的收入增长得最快,但底层群体的收入实际上在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底层和中层群体曾一度收入很好。但2000年左右,不平等加剧”。虽然美国一直视自己为一个机遇平等的国度,但这样的“美国梦”越来越蜕变成一种神话。“富不过三代”在当前的美国社会也变成了一种神话,因为上层人物的后代仍更有可能继续待在那个位置。
尽管表面上是那些以最优成绩毕业于最好学校的人有更好的机会,然而,富有的家长才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高昂的精英大学费用和拼爹的推荐入学制度使精英教育成为特定阶层所享有的资源。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指出,人们所依赖的保障社会流动的市场机制并没有充分保证机会公平,市场力量会受到国家法律法规、政府投入、税收政策等规则和条例的影响。
从盖茨比曲线看,日本的阶层流动情况似乎比美国好得多。但近年来对日本阶层固化的讨论也非常多。三浦展对日本所做出的“下流社会”的判断曾一度引爆讨论。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日本是一个由极少人数的上流阶层与人数众多的下流阶层所组成的等级化社会。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社会呈现出中流化的倾向。然而,三浦展观察到:“这部分中流阶层正在日益减少,逐步两极分化成上流阶层和下游阶层。虽说是向两极分化,但由‘中流’上升为‘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由‘中流’跌入‘下流’的却大有人在。日本的中流阶层正在经历着一个‘下流化’过程。”虽然不是直接讨论阶层固化,但“下流”似乎比阶层固化更加背离社会流动的初衷。三浦展在后记中所思考的现象,“过去阶层低的人比起阶层高的人,总是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现在情况变成了阶层越高的人工作越辛苦,而阶层越低的人工作越闲散,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工作”,也正是为阶层固化后果忧心忡忡的人们所担心的。
韩国虽不在科拉克的盖茨比曲线中,但在孙洛龟对韩国“房地产阶级社会”形成之前因后果的分析中可对其阶层流动情况进行管窥。他用翔实数据说明了韩国社会房地产财产的严重分化,并深入描绘了拥有不同价值房产的阶层过着如何不同的生活,以及住房资源的代际传递如何成为阶层再生产的新机制,最终导致阶层固化社会的出现。
国际比较似乎表明,阶层固化是全球性趋势,所不同的是世界各国之间的阶层固化程度上的差别。然而,作此分析并不是想说阶层固化是正常的,更不是为中国的阶层固化寻找合理化理由。借历史和国际比较,更想表达一种追问,既然子代继承父辈社会地位、财富等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西方与东亚社会都普遍存在,那么阶层继承率或社会流动可能性为多少算合理?我们所言的“阶层固化”,是基于怎样的历史时期或怎样的理想社会所作出的?暂且不论身份地位等指标的信度和效度,但依然应该思考,阶层不固化意味着子代的身份地位完全不受父辈影响的状态,还是子辈受父辈的影响小于父辈受祖父辈的影响便意味着社会流动性有所增强?进一步要追问的是:阶层固化固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但阶层流动就是我们应追求的理想社会?答案可能也不完全是。因为阶层急剧流动本身不仅意味着代际传承的断裂,也意味着中上阶层群体的地位恐慌,进而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增多与社会稳定性下降,整个社会也可能因此而陷入“焦虑型社会”的陷阱而难以自拔。由此可见,阶层固化或者阶层流动保持在某个“适度”范围内,可能恰恰是我们应追寻的理想目标。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适度”究竟是多少?
为与不为:结果大不同
1. 个体的为与不为
尽管不能说“阶层固化”完全是学者所建构出来的,但作为行动者,对这些概念也应保持警惕与思考。毕竟学者很多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判断和话语本身可能无形中正在阻碍社会流动,甚至达到“自我实现预言”的效果。而身处“阶层固化”判断中却没有反思的行动者可以陷入一种宿命论。在不甚努力的情况下,把自身的不利处境归咎于外在的结构性因素,把别人的成功归功于先赋性条件的作用,终日抱怨,其结果更是被负面情绪左右,更不利于自身处境的改善,从而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正如《下流社会》所指出的那样,“疲疲沓沓走路、松松垮垮生活的人不在少数,因为这样的生活态度毕竟来得轻松”。殊不知,以努力与奋斗的程度而言,多数人可能还没有感慨“阶层固化”的资格。
事实上,即使是阶层固化,也仅仅是指阶层流动的概率或可能性较小,绝不意味着社会流动的终止。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流动机会要多得多。例如,尽管精英大学招收的本科生中来自寒门的学子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但毕竟还有相当比例的寒门子弟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精英大学读书。本文绝非要歌颂社会有多公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醒行动者看到社会流动性的所在,不要被“阶层固化”的话语所困。
毕竟处境不会因为“不为”而变好,却可能因为积极地“为”而有所改善。“为”的人通常乐观开朗,生活态度积极,“为”的过程中个人能力得以提升,即便不能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也可能使自身在原有阶层结构中的位置悄然上升,至少可以使自身及家庭的处境有所改善。
2. 体制的为与不为
对“阶层固化”话语本身的反思及对行动者为与不为的讨论,并不意味着体制就可以因此而置身事外。媒体对阶层固化问题的热切关注,不仅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不平等现象日益强烈的感知和不满,也暗示着人们对等级固化的焦虑及对向上流动的渴望;学者们对阶层固化的各种讨论,尽管存在着“层化论”“碎片论”和“断裂论”等不同的判断且尚未达成一致,但绝大多数也都是为了反思当前的一些不合理制度以及可能的努力方向。
对于阶层固化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学者们已经有很多阐述。阶层流动性下降,会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达成相互了解与理解的困难,甚至会使政治上的对立越来越严重。社会分化历来对社会不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加剧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的体制不思优化或改革则可能使整个社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严格的政治身份分层随着市场经济改革逐步瓦解,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也使中国社会在过去30多年充满了活力。然而,事实表明,市场机制并非一劳永逸,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演变成一块政府不作为的遮羞布。市场力量在打破阶层固化上的作用之所以有限,不仅因为市场本身具有不稳定性,而且因为政府政策会塑造那些市场力量,他们参与资源的分配,并且设定和强化游戏规则,甚至诸多权力寻租方式会以无形之手作用其中,而产生新的更隐蔽的阶层固化方式。在这一点上,体制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对于当前的阶层固化,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作用机制之一。在托马斯·皮凯蒂看来,人口增长停滞或者减少会造成前代人累积的资本的影响力增强。“历史上那些由资本主宰、由继承财富决定人们阶层地位的社会,只有在低增长条件下才能出现和维系下去”。中国俗话中的“富不过三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在子女人数众多特别是儿子多、各个儿子相对平均继承财富的法则作用下,资源只能分散地或部分地传递给下一代的家庭,因此财富被稀释。而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家庭的人口结构迅速向“四二一”“四二二”转变。同时,越是较高阶层的人受到越严格的限制。在没有完善的遗产税等进行限制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的副产品便是祖辈和父辈所积累的资源几乎全部往极少数甚至仅有的下一代集中。“二代”们之间的差距因此而急剧扩大。
在另一些方面,体制也难辞其咎。尽管像等级社会一样显性的政治身份隔离不复存在,但中国目前依然是一个隔离性制度的社会,赤裸裸的制度性的社会歧视与社会排斥比比皆是。例如,户籍制度及其在此基础上的一整套制度性安排,人被分成三六九等,不同的人所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责任很不相同。很多制度安排对城市人有更多的保护,而农村人饱受歧视。即便是保障社会流动的高考制度,仅仅从高考录取名额分配来看,按照省级行政区划制定,明显向北京、上海等地区倾斜,不仅导致了全国高考同分不同权现象的出现,而且还十分严重。例如,山东的孩子考上精英大学的可能性比北京的孩子要难得多。
结果与讨论
通过历史和国际比较视角对“阶层固化”进行重新审视,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在传统中国社会还是现代西方与东亚社会,子代继承父辈的社会地位、财富等现象普遍存在,所不同的是世界各国和不同时期的阶层固化程度有所差别。然而,这并非意味着阶层固化是正常的,更不是为中国的阶层固化寻找合理化理由。虽然严格的政治身份分层随着市场经济改革逐步瓦解,但中国依然是一个隔离性制度的社会,对于目前的阶层固化趋势,体制本身难辞其咎。政府应该对阶层固化的社会后果保持清醒,对市场机制中的权力寻租等保持警惕,对制度性藩篱进行清理,从而创造良好的社会流动机制。
“阶层固化”的讨论之所以在近几年更受社会关注,并非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流动真的那么顺畅,而是因为在那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阶层不是固化,而是凝固,几乎不可能流动。实际上,改革开放初期也只有考大学、参军提干等极少途径才能实现凤毛麟角式的流动,但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凝固阶段着实顺畅,更为重要的是,有了制度性的开闸,才有了充满希望的自我实现和社会发展。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流动性其实只是相对于更为凝固的阶段而言;那段时期变得值得怀念,更可能是一种有目的的建构,流露出人们对制度进一步开放的期待。作为行动者,对当前的“阶层固化”的判断和话语应保有一份反思,避免陷入“自我实现预言”的怪圈。
今日之中国,社会似乎有一种被撕裂的趋势,中上阶层被污名化,权贵子弟似乎变成了纨绔子弟的同义词,同时,活在当下在普通民众中间流行。实际上,权贵子弟的努力与勤奋程度可能完全不亚于来自社会底层民众的子女。而阶层固化为那些不思努力的人们提供了足够的借口,同时也从心理上真正关闭了向上流动的大门。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流动的机会远远多于传统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和发达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当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也同时面临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复杂状况,中国社会未来往何处去,正取决于执政者在体制上的为与不为,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如何选择为与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