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菜的滋味
2019-04-16小米
黄 菜
黄菜生长在村后的荒坡上。不算很多,但偶有所见。我以前总认为黄菜是草,不是菜。
我小时候,放了学回家,给猪“寻”草(也就是打猪草),是我的主要的任务之一。因为那时候,我们所学的课程太少了,只有语文和算术,作业也就更少。老师从来都不给我们布置家庭作业。放学不回家不行,学校就在村里,父母都知道放学的时间。回了家,时间还早,必定要帮家里做点什么。但做家务,向来都是我所厌烦的事情。所以我总是自告奋勇地,放下书包,就跟别的读书郎一起,提一个竹编的笼子(篮子)或干脆背一个背篼,到坡上去,给猪寻草。尤其是在夏天,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工作。因为用不着在家里听大人的使唤,我可以一边玩,一边干。山坡上的风吹得也畅快,阳光也不像中午的时候那样强烈了。不时地,还可以一边听别人唱山歌,一边给猪寻草,是很惬意的事情。
在我们乡下,几乎人人都能唱山歌,而且多半都是自编自唱,现编现唱,很随意,很有个性,也很能抒发自己的感情。山歌不能在家里唱,不能在村里唱,只能在野外唱。给猪寻草,就是唱山歌的最好的时机。因为寻草的人一般都在玉米地里,也多是单个的,别人能听见,但看不见,唱了,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一旦到了暑假,我更是每天都要去给猪寻草。庄稼地里的草,一般都比较小,很麻煩,要一两个小时才能把篮子或背篼装满,费时又费事。给猪寻草,我就喜欢到坡上去找黄菜。运气好的话,能够一下子找到好几丛。黄菜的根是黄色的,一根一根的,很粗,也很稀疏。它的叶子绿油油的,能长到一尺左右长,指头那么宽,黄菜的叶面很厚,很嫩,叶子也很多。一丛黄菜能揪一大把叶子,五六棵黄菜就能装满一篮子。我们也只把叶子揪来,让根留着,继续给我长叶子。什么地方有黄菜,我是牢牢地记在心里的。给猪寻草,找黄菜,相对来说,轻松得多了。
暑假的时候,玉米长得比人还高,出“天花”了,玉米穗子也“挂红”了,可以“咂”玉米杆了。玉米杆是我们的“零食”,比甘蔗还甜,还爽,水分也比甘蔗还要足,尤其是靠近根部的比较粗壮的那四五节,也就是玉米穗子以下的那一部分。我们不希望地里的玉米长得都很好,我们希望每一块地里,都有几棵长得不好的玉米。长得不好的玉米,叶子不那么绿,是黄色的,玉米穗子很小,玉米杆也匀称。这样的玉米,结不出好的玉米棒子,结了,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颗玉米粒。见了这样的玉米,剥掉根部的干叶子,如果玉米杆不是绿色,是黄中带着红的,玉米杆“咂”起来,就肯定很甜。
长得好的玉米,玉米杆就不甜。能“咂”玉米杆玉米,一般没有收成,因此也就不能算是糟蹋庄稼,人人都可以这么做,也都在这么做,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我有时候甚至弄几根回家来,慢慢再“咂”。
给猪寻草,如果找到了黄菜,就可以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坐着或者躺着,咂着玉米杆,听着别的寻草的人唱出来的山歌,悠闲地享受一番。我当然要等到天黑了才回去。回家太早了,父母肯定还得安排你再做点儿什么事。
我小的时候,就没有吃过黄菜。但我听父母说起过,他们说,在大饥荒的年份,他们是吃过的。他们认为黄菜不好吃,所以,不到饿死人的程度,他们也就不吃黄菜。
把黄菜焯一焯,晾干,可以存到冬天,再吃。也可以用盐来腌。乡亲们觉得腌它太浪费盐了,一般都不这样做。
我是参加工作,调到县城以后,才吃过黄菜的,是在宴席上。它的味道寡淡寡淡的,难以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更不会有什么深刻的记忆。我跟我父母的观点差不多,觉得它实在不怎么样,很一般。但是,这时候的黄菜,已经成了山珍,别说拿它喂猪,连村里人自己,也是舍不得吃的了。它们被菜贩子收购了去,加工之后,绝大部分都卖到沿海城市或国外去了。据说,在村里就可以卖到四五十元一斤。谁还舍得吃它呢?
亥 韭
我认为亥韭就是韭菜,是野生的韭菜。
早春,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在那些土很薄的贫瘠的干旱的荒山野岭上,它不动声色地萌发了,出土了。它的根好像不死,很粗,而且肥大,应该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亥韭的根系比较发达,能够紧紧地把有限的那一点点土抓住,抓牢,即使牛羊吃了它,也只能吃掉叶子,它的根还在。只要根还在,叶子也就会很快地再一次长出来,在风中招展,摇摆。亥韭的叶子跟韭菜比起来,叶面较宽,较厚,颜色较深,要更“肉”一些,更嫩一些,也更加碧绿。韭菜让人们精心地“饲养”着,为什么还常常是那么一副穷酸相呢?亥韭自己养活着自己,反而比韭菜更加精神,更加饱满,实在值得令人深思。
亥韭经常成片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但它们是单株的,株与株之间,一般都有几寸到半尺的距离。甚至更远些。它们保持着必须要保持的距离,似乎为了不抢,不争,也是为了不互相影响,互相妨碍。它们是有距离的,却又是在一起的,它们能够看见,但不依靠对方,它们是一个并不拥挤的团体,也是一个不能分开的整体。这样的状态,是理想的,和谐的,因而也是好的。人也应该这样。这样的道理人当然是知道的,但人做不到,或者,人不容易做到。
亥韭有蒜的味道,但比大蒜淡得多了。
藏在亥韭骨子里的,更多的,还是韭菜的味道。
整整一个冬天,吃够了干菜,亥韭是第一份送到我们嘴边的新鲜的绿色点心。它只能是小菜一碟,但它让我首先尝到了春天,尝到了新来的这一年。也还是它,让我们对新来的这一年,满怀着期待的。
亥韭是调味的野菜,属于菜里边的“小吃”。和它配合着出现的,是家常便饭,不是宴席。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它更像我们乡下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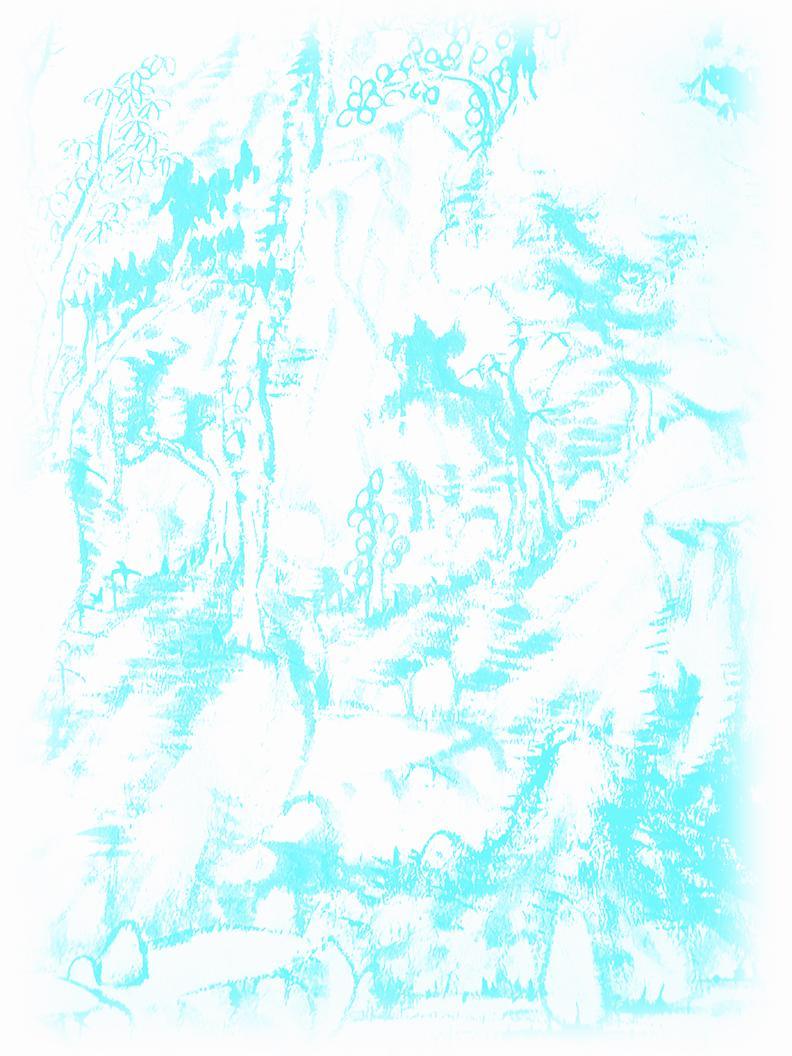
亥韭仿佛就是种在园子里的蔬菜,而不是野菜。掐亥韭来吃,很容易,很快,也很方便。它的“家”离我们家一般都比较近,它好像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也愿意被我们吃掉。也因此,我们掐它的时候,总是比较小心的,怕一旦不留神,伤害了它。我们掐掉它的叶子,留着它的根,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再去掐它来吃了。它长得格外努力,也格外卖力,似乎害怕供养不了我们。什么地方有亥韭,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尽量不让牲畜到有亥韭的地方去,怕它们踩坏了它,糟蹋了它。
在春夏两季,我们经常掐亥韭来吃。到了盛夏,亥韭就长出蒜薹状的茎,但比蒜薹细得多了,它还在顶端,开出一束细小的花来,花围成圆球的样子,看上去,菜薹是在努力地挺举着花,很吃力,也很危险。风吹来,圆球就左右剧烈地晃动,似乎摇摇欲坠,却怎么也倒不下去。
开花以后的韭菜,叶子好像用完了全身的力气,老了,我们也就不吃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它已经精疲力竭,似乎为了开花,它把自己掏空了一般。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亥韭就是野生的韭菜。那么,我们培育着韭菜,浇灌着韭菜,呵护着韭菜,为什么韭菜长得还不如亥韭那么好呢?这是养尊处优的环境造成的,还是,韭菜缺乏积极健康的心态,缺乏努力进取的精神?我不知道。一看见韭菜的“黄毛”模样,就忍不住想起亥韭来。
无论人还是植物,养着,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情。自自然然地成长,哪怕吃些苦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认为,这比成长在花盆似的环境里,还要更好一些。能增加生活的阅历,多一些见识,更主要的是锻炼了它,增加了它的耐受能力。这不是为以后的生活和人生道路,积累了更多更坚强的保障吗?教育子女,尤其应该这样做。
水蕨子
水蕨子,顾名思义,生长在水边,或地下水比较丰富的地方。水蕨子喜欢潮湿的环境,不喜欢干旱。人也是一样的。
在村子附近的河边,就有水蕨子,但不是太多。深山里相对较多。但总的说来,还是少。水蕨子长得也是这儿一棵,那儿一棵,各自为阵,比较分散。水蕨子的分布,应该说是比较广的,高山地带、沿川,只要是潮湿的地方,都有它的踪迹。
水蕨子没有杆,只有根、叶柄和叶子。它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水蕨子枯萎了的叶子不腐朽,不离散,仍然在根上,这样积累起来,根那儿就有了树桩一样粗壮的东西,似乎是杆,其实不是。水蕨子的叶子,从叶柄那儿就开始长叶片,叶片很窄,很长,在叶柄两边,很对称很均匀地排列着。它是一个唯美主义者。
初春,万物萌发,水蕨子也早早地长出来了。刚出来的时候,叶柄向内蜷曲着,顶端像蜗牛壳那样,叶柄上有白色或暗红色的绒毛,后来就没有了。水蕨子慢慢长大,叶柄也就慢慢地向外弯曲,顶端稍稍下坠,呈仰面朝天的形状,加上略微向上的叶片,是好看的弧形。
水蕨子是草綠色的,一直都是,老了还是。水蕨子的顶端如果蜷曲着,没有打开,就可以采回来吃。如果完全打开了,就不能吃了,据老年人讲,吃了会中毒的。我没有尝试过它的毒性,我想,应该不是太强烈的吧。我没有以身试毒的勇气,虽然我很想那么做。经验总归是经验,是前人经历过也验证过了的,不应该怀疑。但是,我忍不住还是有点儿不相信:为什么嫩的时候能吃,老了,就不能吃了呢?它还是同一种植物,还是水蕨子嘛!
其实,危险,往往隐藏在“不危险”的外衣下面。还是小心的好。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有只有一次,我应该珍惜,我也完全没有冒险的必要。
水蕨子可以焯了,凉拌,也可以炒着吃。和腊肉炒在一起,别有风味。水蕨子不开花,不结籽,也没有果实之类的。它怎样繁殖?年年春天,水蕨子都是从存活着的根部长出来的,这我知道,但是,它的根又是怎么来的?天下事物,总有来处,总有去处,这个世界,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这我们都知道。但我还是不明白水蕨子是怎样繁殖的,——其实我也是没有太在意,太留意。因为,等它完全舒展开以后,不能采来吃了,我也就不再关心它了。
一年里,吃水蕨子的季节,当然是春天。而且,吃它得有点儿运气,你要是恰好碰上了一处水蕨子生长得相对较为集中的地方,就掐了它们,四下里再找找,攒凑攒凑,就可以采到一家人能吃一顿的,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不会采它。零零星星的水蕨子,就让它按自己的意愿长着去,它又没有妨碍人,作为人,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跟它过不去。这是父亲小时候就教育过我的,我也觉得父亲说得对,有道理,所以,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对水蕨子是这样,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应该这样。直到现在,我还这么认为,这么坚持,——我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漆 尖
漆尖,即漆树的嫩芽,黄绿色,嫩嫩的,仿佛是香椿,其实不是。把它掐回来,淘洗干净,焯一焯,拌上油盐就能吃。
按说,还应该放一些花椒末之类的调味品。故乡出产的大红袍花椒,是国家优质产品,也并不缺,但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还是紧缺。我们把并不多的一点点花椒(每家一年一般只产出三两斤),只尝那么几顿新鲜,就都卖成了钱。漆尖是春天的野菜,旧年的花椒等到来年,早就没有了。
漆树长在深山老林里,从村子里出发去采,来去都要三个多钟头。专门去采漆尖,就得一天的时间。不过,我们多半是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顺便采一些回来,很少专门去。
我们到林子里去,要么是砍柴,要么是挖野药,回来卖给收购站或药材贩子。还有就是,在林子不怎么茂密的山里,也就是生长着漆树的地方,一般都有生产队的开荒地,种着药材——大黄、木香、党参、当归等等——或者是洋芋、甘蓝菜。我们到林子里去,多半是为了它们,间接地,人们也就有了接触漆树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我们当然不会放过,尤其在春天——准确地说,是初夏,漆树正欢欢地长叶抽新枝,那正是我们吃漆尖的好时节。很少有人专门到山里去掐漆树尖,因为捎带着,就能够弄很多漆尖回来吃。一棵大一点的漆树,要不了一袋烟的工夫,就可以掐一背篼,专门去采,反而不合算。
一棵漆树,大的,要几个人才能抱得住。小时侯,我们家曾经住过几次来割漆的外地人。究竟怎么割漆,我没有见过。据说是在漆树的树干或树枝上,斜着划开一个刀口,漆树的汁液——也就是生漆——就从开口处流出来了,在开口的地方,仰着插上贝壳,生漆就流到贝壳里,割漆的人(我们叫他漆客子),过上几天,再到林子里去,把贝壳里的生漆收集起来,带回家就行了。
我见过的,是漆树上的一块块横七竖八的伤口,我知道那是漆客子留下的。我们掐漆尖之后不久,就能看见黏糊糊的汁液从創口冒出来。我们一般不动它,生漆粘在手上,或者是衣服上,只要它一干,就变成黑色,很难洗掉。
许多人对漆树过敏。我不。我砍柴,见了漆树,也砍。也有砍了漆树做木料,用来打家具的。
对漆树过敏的人,自然得有对付他们过敏的方法:不让他知道他见到的是漆树,吃到的是漆尖,就行了。这办法特别管用。不让容易过敏的人知道,见了、摸了、吃了,都没什么。一见、一摸、一吃,就生漆疮,我小时候觉得很奇怪,甚至觉得漆树神奇,它居然会报复伤害它的人,现在我已经明白原因了,这是过敏。过敏是很厉害的,一旦过敏,全身的皮肤上就会大片大片地生漆疮,开始是红色的颗粒,然后化脓、溃烂,不大病一场是过不了过敏这一道关的。每年,几乎每家都吃漆尖,如果家里有了过敏的人,就得瞒着他,不告诉他,他问了也不说,问得多了,很不客气地回答他一句:“吃你的就是!”的确,不吃是不行的。春末夏初,往往是乡下人的难关,庄稼青黄不接,家里的坛坛罐罐,多半都见了底,不得不找些野菜来,填饱一家人肚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比挨饿要好。
漆尖还算比较好吃的,又新鲜,又嫩,不像有些野菜,特别难吃,跟草料一样难吃,在口里嚼来嚼去,就是咽不下去——这样的野菜都得吃,何况漆尖。吃漆尖几乎是一种享受,所以,虽然不得不吃,但是,人人都爱吃。
我已有很多年没有吃过漆尖了,连它的味道,也逐渐模糊。
鱼腥草
鱼腥草,也叫则儿根。在我家所在的乡下,人们习惯于叫它鱼腥草,而不是则儿根。
鱼腥草的茎是浅红色或绿色的,叶子呈半椭圆形,厚,全绿或背面浅红色,叶面碧绿,茎叶脆嫩。鱼腥草的根是白色的,根茎均分节,根的分节处,有稀疏的须根。
鱼腥草的长度不足一尺,它生长在河滩上,这儿一棵,回头望望,那儿,又有一棵,醒目,招眼。把它攥在手中,轻轻一拔,鱼腥草就拖泥带水地,握在我的手中了。我看看它,拿到鼻子底下嗅嗅它,又把它丢在河滩上。我小时候觉得,鱼腥草是一种没什么用的植物,郁郁寡欢,自生自灭。我那时想,我将来做人,可千万不能做成它这样。
成年之前,我没有吃过鱼腥草,但见过,见得多了。我记得小时候,鱼腥草在我的印象中,是一种没什么用的野草。后来知道,它可以入药。
鱼腥草的味道跟附近的别的草木,太不一样了。与众不同,往往就是生存之道。鱼腥草有浓烈的鱼腥味,因为我的家乡没有吃鱼的条件,乡亲们不常吃鱼,就不是太习惯鱼腥味。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人吃鱼腥草。我小时候就不喜欢吃鱼腥草,不愿意吃鱼腥草,我也想不到,它居然可以吃。参加工作以后,在别的地方,在餐桌上,我看到了鱼腥草。它也是可以吃的吗?我挺纳闷。看到别人吃,我照样不吃。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我吃了几次,觉得还不错,就吃起来了。我把我吃鱼腥草的经历告诉了乡下的亲戚,因为采摘较为方便,几乎是唾手可得的事情,我想让乡亲们也尝尝鱼腥草,但他们不,还说:“它有啥好吃的?”我也不便于勉强他们,只能听之任之。更后来,餐桌上有了鱼腥草,我常常就成了第一个觊觎它的人,不让盘子见了底,我是不会住手的。
鱼腥草可以生吃,洗干净就可以吃了,不费时,不费事。人的口味,有时候,是会变的。
【作者简介】小米,男,原名刘长江,1968年生,1986年开始在《人民文学》《诗刊》等百余家报刊发表作品1000余篇(首),曾入选数十种诗文选集,已出版个人诗集《小米诗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