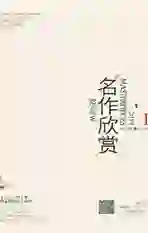从“走近深渊”到“坠入深渊”
2019-04-15战玉冰
战玉冰
摘要:本文从小说《包法利夫人》主人公爱玛的人物性格与情节驱动出发,试图发现小说所隐藏的“对称性”结构,并借助这一文本结构来兼及探讨另一位人物——包法利先生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以及其命运悲剧的必然性。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 “对称性”
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当然是包法利夫人——爱玛。一方面,爱玛对于爱情,情欲的追求构成了小说最为核心的情节驱动力;另一方面,也正是爱玛这种性格特质才最终导致了小说情节的发展走向以及人物命运的最终悲剧。爱玛性格上追求浪漫的不安与躁动,在她婚前修道院中的经历中便可见一斑:
(爱玛)在她奔放的热情中,却又有着讲求实际的精神,她爱教堂是为了教堂里的鲜花,爱音乐是为了浪漫的词句,爱文学是为了文学热情的刺激。这种精神与宗教信仰的神秘性是格格不入的,正如她的性格对修道院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反感一样。
李健吾在评价《包法利夫人》时曾说“爱玛是一个属于虚伪的诗与虚伪的情感的女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爱玛情感幻想的不切实际以及这种不切实际幻想的由来。在法语中,随着这部小说的问世及流行,“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也渐渐成了想人非非的代名词。而令爱玛走出想入非非第一步的是夏多布里昂等人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因为沉溺于这些文学作品中而不能自拔,所以爱玛无法忍受修道院中的清规戒律,进而她才会想通过与包法利先生的婚姻来使自己获得解脱。在结婚以前,爱玛对于与这位有机会四处游走的医生的结合是充满了美好憧憬的。不幸的是,恰如小说《围城》中的名句:“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爱玛奋力冲进婚姻这座“围城”之后,才发现这里依旧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原本以为会充满幸福与欢乐的婚姻,却因为包法利先生“像马路的人行道,庸俗乏味”的平庸谈吐而彻底破灭。
于是爱玛开始走向人生“堕落”的第一步——与罗多夫私通,在爱玛眼里,罗多夫是爱情的象征,是自己幻想世界的白马王子,是可以拯救自己逃离平庸婚姻的救命稻草。但对于罗多夫而言,与爱玛的这段关系却只是一场语言游戏、一次寻欢作乐、一个背后带着呵欠的微笑而已:
(罗多夫)他认为,夸张的言辞恰好是为了掩饰感情的虚假;丰富的感情有时并不是空洞的比喻所能表达的。因为人借助语言永远说不清自己的需求、观念和痛苦;人类的语言只不过是一面破锣,我们敲出不同的声音,本意是要感动星辰,结果只是吵醒了狗熊。
(罗多夫)他的寻欢作乐,如同校园里的操场,已经被学生们踩硬了,长不出草了,学生们还会在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而这些在心头一掠而过的女人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罗多夫)每一个微笑背后都有一个厌倦的呵欠,每次的喜悦里都隐藏着不祥的预兆,所有的快乐最终带来的都是腻烦,即使是最甜蜜最销魂的吻,也只是在唇上留下一个向往未来更大的快感的欲望而已。
小说里写爱玛渴望爱情,“就像一条放在厨房案板上的鲤鱼渴望水”。而我们如果结合整个故事来理解这句话就会发现爱玛所爱的并非罗多夫,也不是莱昂,更不是包法利先生或者那个行踪鬼魅的子爵。用一句俗套的话说,包法利夫人所爱的是爱情本身,她把自己从文学作品中所感受到的带有虚假性质的、自欺欺人的爱隋幻想投射到实际生活中,并努力将自己的幻想对象落实到某个具体男人的身上。但可惜幻想并非现实,所以才会有后续的一系列“越轨”行为与悲剧结局的发生。
小说中有一处很有趣的细节,在爱玛给莱昂写信时,她“见到的恍惚是另一男子,一个最热烈的回忆,最美好的回忆和最殷切的愿望所形成的幻影”。从小说前面所铺设的细节来看,这个幻影似乎应该就是那个男爵,落实到爱玛实际的生活中则先后成为罗多夫和莱昂,其实包法利先生在结婚前也是这个幻影的投射之一,而说到底那个男爵也不过只是个幻影罢了。正因为男爵从未真正走入爱玛的生活,一直保持着可望而不可即的状态,所以他显得更完美。我们不妨试想,一旦男爵也真的进入了爱玛的生活,那很快他将会和包法利先生、罗多夫、莱昂一样变得令人失望不已,最初结婚之前包法利夫人不是还幻想过与包法利先生结婚之后的美好吗?
李健吾认为“(爱玛)她的悲剧和全书的美丽就在她的反抗意识,她有一个强烈的性格,天生骄傲,是一个纯粹的自私主义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把自己当作一个贵妇人,期盼有奇遇,她相信将来总会是好的,她的一生只是一部谎言”。的确,当爱玛抱着虚妄的梦想与罗多夫这样一个情场老手私通,所带来的必然是失落与伤痛。而小说在表现这种伤痛时也采用了逐步递进、层层加深伤害,直至彻底撕碎爱玛幻想的写作手法和情节设置。以罗多夫为例,他对爱玛的打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在罗多夫厌倦了这种私通关系时,他便抛弃了爱玛。
第二层次:在爱玛破产后,向罗多夫借钱,却被他巧言令色地拒绝了。借用小说中的话就是“考验爱情的方式有很多种,而最能摧残爱情,将之连根拔除的方式就是借钱了”。
第三层次:在爱玛死后,包法利先生去找罗多夫,并表示原谅了他,但换来的竟是罗多夫的不屑与讥笑。至此,罗多夫对爱玛的感情,甚至一点怜悯之心都荡然无存。
从上述爱玛所驱动的情节走向来看,各种事件的前后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整个故事就是紧紧围绕包法利夫人由婚姻,到出轨,再到破产,最后到自杀,引出了小说里形形色色的男人:包法利先生、莱昂、罗多夫、公证人、赫勒、子爵等等。但如果我們进一步对小说的结构进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小说的一系列情节其实是以“农业促进会”为转折点,而形成了某种高妙的“对称性”结构。
在农业促进会之前,包法利夫人仅仅是精神出轨,即所谓的意淫,她并没有什么实际越轨的举动,但这些“意淫”却又为她后来真正的出轨做了一个铺垫和准备。如果我们将“出轨”视为一个“深渊”的话,那小说前半部分则可以将其概括为“走向深渊”;而农业促进会之后包法利夫人开始与罗多夫私通,被甩后又立马找上了莱昂,可谓是在出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相应地,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坠入深渊”。至于“农业促进会”这一章节则可以说是环境渲染与人物塑造紧密结合的成功典范,福楼拜将大会的进行与罗多夫诱引包法利夫人的场面交替进行描写,把包法利夫人的堕落巧妙地放置于社会繁荣的背景之上。这一章也是全书最精彩的片段之一,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大会与其背后罗多夫与包法利夫人见不得人的勾当交替推进的写法使得整个章节的内容充满了反讽的张力。
有人喜欢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紅楼梦》进行对比,这其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两部小说确实都是作家精心打造、反复琢磨的文学典范。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增删十载,披阅五次”,正所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而福楼拜在西方也被誉为首屈一指的“文字的基督”。周汝昌在分析《红楼梦》时曾指出小说存在一个明显的由盛转衰的“对称性”结构内核,同样,《包法利夫人》也有着这样一个转折、“对称”的情节走向,而这个情节走向的“分水岭”正是“农业促进会”。如果说在“农业促进会”之前,我们对于爱玛的想人非非尚能寄予更多的同情之理解,那么在之后,爱玛一次次出轨却又遇人不淑,就只能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当我们把包法利夫人的故事中所隐藏的‘对称性”结构进一步延伸开来,就会发现作为小说绝对主角的包法利夫人既没有在小说开始时便登场,而在她死后,小说的情节仍在继续推进。从这个角度看,其实真正贯穿全书的人物竟然是包法利先生,整部《包法利夫人》是以包法利先生开始,又以包法利先生终止的。
先来看小说的开头,福楼拜在小说伊始并未直接运用后来贯之全篇的第三人称视角,而是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来进行叙述,并在不经意之间,进行了叙述人称视角的转换:从开始的第一人称视角“我们”渐渐过渡为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
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却端着一张大书桌。正在打瞌睡的学生也醒过来了,个个站了起来,仿佛功课受到打扰似的。
校长做了个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过身去,低声对班主任说:“罗杰先生,我把这个学生交托给你了,让他上五年级吧。要是他的功课和品行都够格的话,再让他升高班,他的岁数已经够大的了。”
这个小说开始部分的观察者是很模糊的,乍看上去像是教室里的某个学生,实则又不然,它其实更多的是以一种超然的形式而存在,并非化身于实在的某个人。具体来说,它更像是一种眼光,一种视角,福楼拜以“我们”作为叙事的起点,对读者而言,相当于发起了一种召唤,将读者一下子带入到故事的现场,读者将会被“我们”这个复数形式的词语所迷惑,从而产生一种被动的认同感,情不自禁地投入到小说的叙事之流,无形之间“我们”也成了小说读者的指代符号,作为查理·包法利的同学的“我们”销声匿迹后,作为读者意义上的“我们”却依然存在。刘渊老师曾在《福楼拜的“游戏”》一文中指出,在文本中昙花一现的“我们”就是福楼拜向读者发出的一次邀约:他赋予了读者参与阅读的权利,无形之间增强了小说的带入感。人称转换无声无息,完整地保留下来了第一人称下的真实可信与第三视角下的全知全能,将两种叙述视角的优势兼收并包。
再来看小说的结尾,我们在整个故事主干部分都未曾见到包法利先生对于妻子出轨的态度和反应,好像他是一个木头人或者根本不曾存在过。这看似是一种缺憾,因为在一般的文学表达中,妻子出轨很多时候是通过丈夫的反应来侧面体现并不断激化冲突的。但福楼拜有意地在包法利夫人偷情时避开对包法利先生的反应进行描写,这一方面这更加符合包法利先生愚讷麻木的性格特质;另一方面在小说最后作者借助包法利先生阅读包法利夫人遗留下来的信件这一行为,集中复现了包法利夫人偷情的种种往事,而只有让包法利先生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的妻子多次出轨、胡混、欠债、自杀的负面讯息,才能对其造成足够强烈的精神打击,以至于让其最后猝死在家中。同时,小说作者在这里借助包法利先生读信的动作,也把整个小说的主干情节进行了一次读者记忆层面的“闪回”。而包法利先生在临死前,见到了罗多夫,并仁慈甚至有些窝囊地表达自己原谅了罗多夫时,反而受到了罗多夫的讥笑和鄙视。作者在包法利先生死前安排了这一情节意在说明,在这个社会中,不仅包法利夫人的浪漫幻想没有办法生存下来,就连包法利先生的忠厚也无法逃脱最终被抛弃乃至毁灭的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