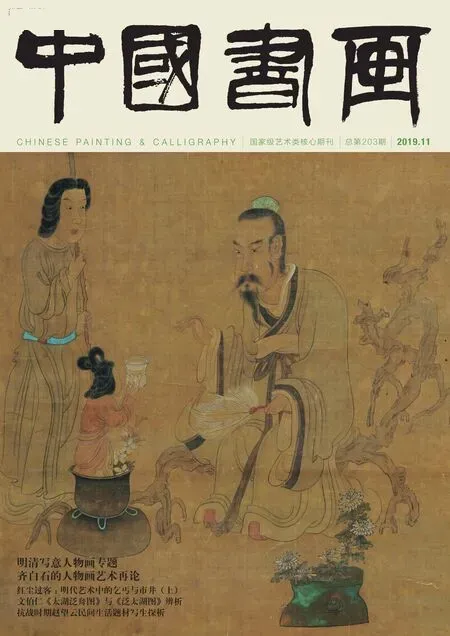“访碑使”黄易的塑造与还原
2019-04-10谷卿
◇ 谷卿
近些年来,中国本土艺术社会史研究日渐勃兴,成果迭出,学者对于古代艺术的生产、复制和传播,更多时候愿意作社会历史层面的考察和论述。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关注点从艺术内部转向外部,事实反而是,研究者开始尝试越过“风格”“话语”“体系”等前置概念及其造成的认知区隔,借助尽可能丰富的史料,去探索相对隐蔽的艺术实践的诸种影响因素和运作机制。虽然此前有关黄易(1744—1802)与金石学的探讨已然相当深入,但薛龙春的近著《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上仍具新意。作者利用翔实的文献,还原了黄易与友人以金石及相关艺术品为媒介的交往细节,讲述在他们种种活动影响之下金石成为一时风尚的情形和缘由,据此描绘出乾嘉金石艺术文化的社会生态样貌。
“金石时尚”一语,来自黄易友人潘有为在写给他的信中所言—“金石亦时尚也”。“时尚”二字,可说是对乾嘉时期金石学业已成为一种社会性知识之状况的精准评述。当黄易等辈通过金石古物及其铭刻追寻“古欢”,而由此营造“时尚”之际,我们发现“古”与“今”或“古”与“新”之间实际存在着互动和转化的巨大可能,沉浸在“古欢”里的黄易,竟成为引领乾嘉学林“时尚”者,这看似是个悖论,实则决定于一种特别的内在机制。
“古”和“今”是辩证的,“新”与“旧”的关系也是如此。从事金石研究,不能不讲论和分辨相关拓本的新旧。以金石之“石”而言,碑碣与石刻拓本,旧拓的市场价格总要高于晚拓或新拓,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碑面或崖体遭受的风化、侵蚀、损坏一定越来越严重,其上文字图像也愈加残泐—有些石碑甚至还会因为自然或人为因素遭到毁灭,不得传于后世,而存字多寡直接影响拓本的价值,也是学者据以判断拓本制作年代的考据点。从这个角度看,存字较多的旧拓相比晚拓和新拓,信息一般更丰富、更接近原初状态。但黄易等人访碑、拓碑,每每能够获得更多信息。《古欢》结合信札、题跋、日记等文献对此作了详尽叙述,比如他们在实地勘碑的活动中,时常发现旧拓没有拓存的碑额、碑阴、碑侧以及当时和后世的相关题名、题刻,又比如他们通过升碑、剔字等行为,直接还原或修复石碑的种种信息,那么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新拓,其价值当然相对高于旧拓,这也决定了拓本版本系统的复杂性,以及面对拓本时需要更为系统和科学化的研究方法。所以,访碑传拓和搜购旧拓,在黄易那里是互补互益的。

薛龙春著《古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9月版
金石学者有所谓的“古欢”,是“好古”的。黄易爱碑近于“痴”,总会对那些可能帮助他得到新见拓本的朋友强调:“新得古刻出人意想之外者,尤所急望。”其背后的原因便在于,古物古刻资料进入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的领域和流程之中,而以往未见的铭刻文字,更能促使旧有知识得到较大程度的更新。资源是“古”的,资讯则是“新”的。所以,当黄易、翁方纲拿到一份新见的拓本,总会细心地检索、查勘、对比前人著述,一旦确认是从前学者所没有发现和注意到的,他们无不激动振奋。金石资料和传世文献又可以互相参照、比较和补充。金石著作的校订、编纂,还和经史研究以及地方志编撰互相影响甚至互为因果。这里充满了探险的趣味,也让我们看到资料积累、信息更迭、学术推进之不易。
白谦慎在讨论晚清官员的收藏时,发现他们大多有一种“玩物丧志”的焦虑,而寻求消解之法,唯有建功立业。与官员不同,学者们对抗“玩物丧志”焦虑的做法是,反复申明亲近金石是为保存文字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所承载的古代文化和历史。正缘于此,金石本身可能含有的艺术性往往被有意识地忽视,而且金石作为研究的工具,其重要性也大于金石作为研究的对象。晚清学者总结金石之学有考订、评骘二途,但在清代前中期的金石学史上,“考订”的受重视程度要远过“评骘”。不过,到了黄易这里,他极大程度地超越和突破了“政治正确”的束缚。黄易营造和引导的新时尚,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旧有这种“政治正确”的反动。他呼唤起人们对金石本身甚至金石周边艺术性的关注和讨论,用种种行为和手段建构起一套有关金石的艺术话语,而且一直流传影响至今。
《古欢》特别讨论了一个“经典化”的问题,上文所述黄易对“政治正确”的反动过程,正与此经典化过程同步。黄易促使自己的访碑活动(包括过程和成果)经典化,采取了诸如邀请友人为拓本题跋、在石碑上题刻以及翻刻拓本、刊印图书等方式,当中最重要也最特别的,就是他绘制了一系列的“访碑图”。访碑图的绘制和传播,非常个性化也具象化地将黄易的形象和身份描绘确定下来。这些访碑图可以视为雅集图、实景山水、纪游写生之类,其本质则是一种特殊专题的自画像传。访碑图的功能不仅在于纪念访碑活动,更将黄易的形象塑造为一个长于田野考察的金石学者。这一形象在乾嘉金石学者圈中,无疑是极为独特的,而访碑图作为一种图式和主题,在后世金石书画家的创作中也频现身影。
考察黄易访碑活动经典化的过程,我们还应该关注他的身份和策略、目的之间的关系。黄易在体制中的身份是擅治河防的地方技术官吏,没有功名,居官不高,与他那些做过学政、后来成为阁臣和疆臣的金石之友如翁方纲、阮元等人的政治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文化资本亦无后者雄厚,因此黄易描绘和树立自我形象,特意放大了自己与田野山河的密切关系,强调他处于探访调研金石的最前线。就访碑这个具体的事项或工程而言,相较其他地位更高、成就更大的学者,作为主导者和当事人的黄易显然更有话语权,其叙事也更具备参考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在《古欢》所描述的经典化的过程中,黄易与身边其他学者的关系并非是单向度的,他从来不是一厢情愿地邀请大家参与他的金石活动,可以看出他的朋友均抱持强烈的介入意愿,希望加入者像翁方纲等人还会向黄易透露和传达相关想法并设计参与方式。虽然黄易实际担任着“运河同知”的职务,但友人在诗中开玩笑说他更适合去当“访碑使”(伊秉绶:“官宜访碑使”),巧设了一个虚拟的“职”来兼容他的“志”。可见的事实是,作为“运河同知”的黄易,远没有作为“访碑使”的黄易更为人所熟知和称道。
“访碑使”成为黄易的文化身份,而他另一个近乎绰号的称呼“碑痴”则更具有标签性。这个绰号的生成和接受其实也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古欢》提示我们,它在题跋、题诗中产生,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这样称呼(钱大昕:“合呼黄九作碑痴”),后之观者深感恰当,于是不断“跟帖”赞同。可以补充的是,晚清翁同龢藏有一方刻绘黄易画像的砚台,他在砚拓的题诗里也评价黄易有“碑癖”,足见从与黄易同时的乾嘉学者到清末的文化精英,他们的口径几乎保持了统一。从另一角度来看,也证明有关“黄易”与“碑”的绑定完成得相当不错,其经典化过程所取得的效果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