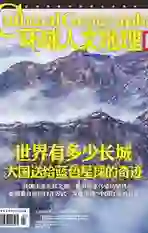从剑桥开始,遇见设计,遇见再造
2019-03-27李海洲
李海洲

01.
2018年早秋,我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参加国际诗歌节。英国人禁烟,凡是有屋檐的地方,烟民必须守身如玉,所以每天早晨或黄昏,我和诗人喻言都会从借居的博士楼里乘电梯出来,穿过古典的楼道和精致的花园,前往落叶翻卷的大街上吸烟。
光线很好,剑桥古老的建筑恢弘、精美,两个假装优雅的烟民目光迷离,长时间陷进哥特式或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风格里。很多次,我们看见那些堆积了几百年风雨的老建筑,被巨大的拉网和脚手架小心围起来,有专业工人正在进行技术修缮,他们修缮的方式很谨慎:补缺、刮灰、上漆,动作很绅士,像在缝补一段爱情,又像在熨平一段起皱的人生。
诗人喻言有些感慨,他做过开发商,有过很多成功楼盘的开发经验,于是开玩笑说:“技术修缮又慢又花钱,不如指挥两百台挖掘机进场,直接进行强拆,重新做成花园洋房。”这的确是个黑色幽默,我笑着回答他:“如果是这样,软弱的亨利六世一定会从坟墓里爬出来,然后亲手掐死你。”要知道,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著名的礼拜堂,就是当年的国王亨利六世亲自主持设计的,耗时99年才终于完工,到现在已经有五百多年历史。而很多很多年以来,剑桥的所有建筑,维修的方式几乎只有一种,那就是技术修缮。
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了这个话题,聊起了国内历史建筑和人文遗产的保护。聊着聊着,两个人居然开始变得忧伤起来。是啊,对一个设计师或者一幢伟大的建筑而言,不要说拆除,就是按原型在原址上再造也是一种遗憾。所以,剑桥的工人们,表面上是在修缮建筑,骨子里却是在维护、坚守着一段永不如烟的历史和文明。
与这个话题有关的是:在剑桥大学期间,我居然偶遇了青花艺术家干道甫。之前我们没有见过面,但由于同属一个诗酒风流的生活圈子,相互早已闻名,其实只差一台大酒就可以成为兄弟。所以在徐志摩爱过的康桥,咖啡浓郁,我们一见如故。干道甫刚领完剑桥的艺术设计奖,他其实一直往返于北京和江西,大多数时间呆在景德镇,和一群艺术家做冰蓝公社。
众所周知,景德镇窑系是传统手工艺技能的精华,尤以青花瓷最为独步,那是周杰伦用含混不清的歌声热爱过的。干道甫他们的冰蓝公社,做得最漂亮的活儿就是:把现当代艺术移到优雅的青花瓷器上去,那些纷乱坚固的泥,经过淘洗、煅烧、拣选、乳黏,再经过干道甫匠心独具的绘画装饰,最终变成了后来名动剑桥的新青花艺术。简单说,干道甫就是在中国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行一场浪漫的设计再造:瓷还是那皿唐宋元的瓷,但器已经有了21世纪的优雅。干道甫用发芽的笔和手,给中国传统青花上了一层全新的釉,是他的设计和再造,给景德镇窑赋予了新的生命。多年前,北京诗人周墙送过我干道甫的一皿青花,后来好像被谁顺走或酒后遗失。但瓷器上那抹荡人心弦的蓝,却多年来留在我心底,长时间挥之不去。
这个过程中,我想起了几乎和景德镇一个时代的涂山窑,这个被认定为宋代黑釉瓷的窑址,位于重庆南山的黄桷垭。和景德镇窑的优雅不同,涂山窑是座民间窑,所产瓷器古朴、原始,没有官窑景德镇动人心魄的青花蓝,它以黑色系为主。只是,除了在三峡博物馆,人们几乎已经很难看到它的踪迹。涂山窑被发掘后,有人认为他见证了一个精致的南宋。但我不这样认为:从色系、胎釉、煅烧来看,涂山窑更多的是见证着古重庆人民的生活:粗粝、世俗、亲切。而精致或颓废的南宋之美,只能用那个时代的景德镇窑来见证。所以,即使同处一个时代,瓷器也有自己的语言和身份。但无论如何,作为文化遗产,他们其实并没有江湖和庙堂之分。
遗憾的是,涂山窑的窑火已经熄灭,泥坯幽暗,火焰消亡,不仅没有干道甫这样的人去进行设计再造,反而很早就淡出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02.
从英国回到重庆,秋意渐浓,城市开始掉叶子,掉在各种现代性的街道上。很多次,站在落日的窗前,看着飘飞的高架桥和近处的楼宇,我就会想起古老的剑桥,想起那些用技术修缮老建筑的工人,他们对文明和造物主的尊重,让我在这座早已没有了吊脚楼的江城长时间地叹息和感动。吊脚楼是重庆城的符号,涂山窑是另一个,但它们都在不同的城市进程中各有宿命,黯然消亡。
秋天快要结束的某个夜晚,我在重庆著名的白象街遇见了歌手朱哲琴。曾经,她用一张很“西藏”的专辑《阿姐鼓》打动过许多人,但之后很多年,她远离乐坛,去做一个名叫“看见造物”的文化保护与发展计划。这一次,朱哲琴带着红点设计大奖得主Michael Youg出现,其实她们关注的焦点,落在了几乎已经被遗忘的重庆涂山窑上,她们想让涂山窑的火焰重新燃烧。
我有些感动。但作为一个人文地理刊物的資深工作者,我的希望中本能地夹杂着怀疑:朱哲琴和Michael Youg可以是干道甫,但涂山窑可以是青花蓝吗?那种古朴浑圆的瓷器,历史上更多的时候用作茶具,如果以原貌重返人间,进行批量生产,真的会被更多人接受吗?如果还原,重新进行设计再造,它真的还是涂山窑吗?或者,给传统工艺赋予现代的生命,原本就是涂山窑和像涂山窑一样的遗产的宿命。其实这些年来,因为工作原因,我见到过太多为保护而保护的文化遗产,庞大的资金和媒体的喧嚣之后,遗产变为项目,项目在最后却成了遗体。当时,我没有把这些问题抛出来沟通,是由于我依旧怀抱希望:因为,属于涂山窑的时间开始了。也许,经过设计再造,涂山窑或者真会以我们熟悉而陌生的面孔重新出现在生活中,尽管中断了很多年,但它至少续上了一段文明。前世今生,再造的能力,究竟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真正的答案需要时间来回答。
朱哲琴们感兴趣的,还包括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也就是重庆黔江地区土家十三寨的“花铺盖”,早年用手纺,后来用机织,特点是色彩斑澜,图案奔放。我曾经两次去过十三寨,那里司檐悬空,山歌悠扬,我在十三寨进行田野调查,甚至为它写过一组诗。朱哲琴带来的设计师杨芳探访到这里,杨芳是BY FANG的创始人,她对西兰卡普的图案设计和针法很感兴趣。我怀疑杨芳会把她感兴趣的东西用到自己的品牌中去。这其实暗合我的另一个观点:不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适合大规模推广,但可以作为一种小众存在。西兰卡普的布匹可以不随世逐流,但她的造物精神和狂放的图案,其实可以设计再造到其他的品牌,从而诞生另一种生命。其实,这也是传统文明带给现代的一种启迪,是另一种层面上的设计再造。
这个过程中,我自然是想起了著名的白象街。曾经的白象街之于重庆,如同今天的华尔街之于纽约,它拥有800年历史,但最终面临凋零和破败。几年前,开发商找到我,希望我所在的杂志能够针对白象街做一期策划。要知道,那些陈旧的只站在开发角度去做的所谓宣传,我和我的杂志从来不屑为之,所以我提出:活儿可以接,但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我自己决定。对方沉默,最终答应下来。于是我带领团队皓首穷经、钩稽史料……企图还原一个历史上真正的白象街。这个过程中,我慢慢被巨大的快乐鼓舞。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其实正在完成一个设计再造的过程。后来,刊物上市,效果不错,连续加印多次。但那时候我也很担忧,因为我所呈现的只是八百年前的白象街,只是纸面意义上的还原。好在,后来的白象街,尽管崭新,但大多数古迹还在,依旧有着旧时繁华的模样。
在白象街遇见朱哲琴的那个夜晚,我因事提前离开。月亮很好,独自走在白象街优雅的街道,我再一次想起剑桥那些技术修缮老建筑的工人,内心突然有些忧伤。我不知道再过800年,我现在走过的白象街是否能和今天的剑桥一样。那时候,我还想到了把干道甫的青花蓝送给我的北京诗人周墙,他曾经在黄山设计再造了爱国名妓赛金花的归园,落成后我们举杯相庆,但周墙却叹息说:今天的归园随便有多漂亮,都不是以前赛金花归园的模样。
那个秋天的夜晚,白象街的月亮很柔软,像800年前一样,但再柔软的月亮也照耀不到我或者周墙内心小小的失落和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