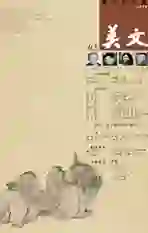杂树生花,众声喧哗
2019-03-25陈剑晖

陈剑晖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小说、诗歌的大红大紫、亢奋热闹相比,散文创作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沉稳平静,甚至可以说是默默无闻,较为冷落萧条的。即使被誉为“散文时代”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在我看来同样尚未达到20世纪80年代鼎盛时期小说创作那样的“轰动效应”。但影响力不及小说、诗歌或者说整体的思想艺术成就不及“五四”时期的散文,并不意味着当代的散文创作没有成就,没有“热点”和“亮点”。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善于在默默无闻中积蓄力量,在沉稳平静中奋起前进,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到新世纪达到其创作的高点,形成了杂树生花、繁花似锦、众声喧哗的多元格局。这是散文创作与其他文体创作的区别之处,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文学事实。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散文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散文也和其他文体一样获得了解放。虽还未能完全擺脱杨朔散文模式的束缚,但散文的题材、品种、表现手法开始丰富多样了。这一时期先是“悼念性”的散文引起读者的共鸣。第一类是缅怀革命领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代表作有毛岸英、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何为的《临江楼》、郁茹的《登临》等。第二类是悼念“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如丁宁的《幽燕诗魂》、巴金的《怀念萧珊》、丁一岚的《怀念邓拓》、菡子的《永恒的纪念》等作品。“悼念”散文因记叙翔实,感情强烈,爱憎鲜明,在当时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
这一时期,还有两种散文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巴金、冰心、秦牧、孙犁、杨绛、汪曾祺、黄裳等一批老一辈作家焕发了青春,写出了《随想录》《干校六记》《将饮茶》《老荒集》《晚华集》等一批敢于“抒真情,说真话”的作品。二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散文家的崛起,壮大了当代散文的创作队伍。特别是贾平凹,他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了《月迹》《爱的踪迹》《人迹》《商州初录》等一批散文集,不但数量多,且以其独特的“味道”和“语调”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贾平凹的散文创作,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散文创作的最高水准,甚至其质量和影响一度超过了他的小说创作。20世纪80年代的散文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女性散文家特别活跃。这时期较有名的女性散文家有王英琦、叶梦、苏叶、唐敏、斯妤、韩小蕙、曹明华等,在短短几年间出现了这样一个女性散文作家群,而且其作品都有鲜明的个性,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这在过去的散文史上并不多见。上述诸方面的实绩,表明散文并未“消亡”,也没有走向“末路”。当然,与同时期轰轰烈烈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创作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散文创作的确是较为平静平淡的。这里有散文作家自身的散文观念、审美情趣、艺术修养等方面的问题,也有文艺体制、社会环境、时代氛围等方面的原因。这一切都预示着:在20世纪80年代,散文创作的春天尚未到来。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散文创作春天的到来,或者说,一个真正的散文时代的到来,应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相对宽松,散文生态环境的改善,加之公共空间的拓展和出版界的推波助澜,以及小说家、诗人和学者的加盟,散文创作的队伍空前扩大,当代散文一改以往的边缘姿态,一跃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时代的文体”。
这一时期,首先是“文化大散文”异军突起。“文化大散文”打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散文过度配合政治宣传,以表现“时代精神”为目标,以“短、小、轻”为主题和结构模式的创作趋向,而以“长、大、重”为其内容和艺术特征。所谓“长”,指的是篇幅长,许多文化大散文动辄万字以上,有的甚至一篇二十多万字。所谓“大”,指的是题材大。“文化大散文”的取材往往不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之类,而是历史的记忆、民族的精神、知识分子的命运、人类的困境和未来等大命题,如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周涛的《游牧长城》、韩少功的《性而上的迷失》等。所谓“重”,指的是“文化大散文”的内涵较厚重。“文化大散文”不但反思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像余秋雨对中国知识分子两重性格和对“上海人”的剖析,周涛对人与环境、人与动物的关系的思考,韩少功对“佛”与“魔”的界说,对现代人“性”的迷失和后现代主义的考察,都体现出了文化批判精神。
此时期,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散文现象,是以“老生代”为主体的学者散文大放异彩。说到学者散文,必须做一点辨析:许多人将“文化大散文”与“学者散文”混为一谈,这是值得商榷的。第一,题材领域不同。“文化大散文”侧重写“大历史”中的王朝更替和历史事件;“学者散文”更倾向于写童年、故乡、学习生活等个人的历史。第二,主题指向有别。“文化大散文”侧重对历史结论的纠偏,或展示中华文化的苦旅,追寻理想的文化人格;而“学者散文”更多的是介绍科学知识、读书心得体会,以及对文化的认识和个人的人生感悟等。第三,是话语方式相异。“文化大散文”一般是长篇幅、大结构、宏观叙事;而学者散文由于创作主体、人生态度和心态的平和放松,以及偏于内敛型的思维方式,作品一般结构较简单,篇幅较短小,其话语方式偏向于“细小叙事”或叫个人叙事,其语言则呈现出自然朴素、平淡从容的特征。明白了上述的区别,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以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
除了“文化大散文”“学者散文”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还涌现出以史铁生、韩少功、王小波、张承志、张炜等小说家,以及学者林贤治、刘小枫、朱学勤、南帆、丁帆、王尧、王彬彬等为代表的“思想散文”。这类散文立足于人文主义的立场,坚守知识者的心灵和道德理想,关注现实、历史以及人类的生存与命运的大命题,保持自由、独立的思考与质疑批判的姿态,这一切都使这一时期的思想散文达到了一种较高的精神维度。这样的散文现象,在整个20世纪是极为少见的。可以说,“思想散文”的大面积出现,一方面提升了中国当代散文的精神纬度和品格;另一方面,这一散文现象也是改革开放下,顺应时代大潮而出现的产物。
第三阶段,新世纪至今。以2000年开始的新世纪散文,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散文热”的创作态势。在这一阶段,“文化大散文”依然保持着繁荣的局面,而且有所变化,比如李敬泽、祝勇、穆涛、丁帆、王尧、王彬彬、詹谷丰、詹文格等的文化大散文,与余秋雨、王充闾、梁衡、卞毓方的文化大散文相比,就有不少新变。当然,这一阶段,对于散文来说,最让人欣喜的是“新散文”的崛起以及對传统散文的颠覆。“新散文”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时,云南的《大家》杂志在1998年第一期开设了“新散文”栏目。先后推出周晓枫、于坚、张锐锋、钟鸣、祝勇、庞培等一批“新散文”作家的作品。尔后,《人民文学》《十月》开设了相关专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出了以祝勇、周晓枫、张锐锋、宁肯等为代表的“深呼吸散文丛书”。此外还有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散文丛书”推波助澜,以及祝勇的《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等一系列文章,对“新散文”进行理论上的总结。至此,“新散文”已渐成气候,不仅成为新世纪引起广泛关注的散文现象,甚至有人将其称为“新散文运动”。
新世纪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散文写作潮流是“非虚构写作”,而这一写作潮流的始作佣者应是《人民文学》。大约在2010年前后,《人民文学》针对报告文学作品过于新闻报道化和人物故事的程式化,以及一些散文作者热衷于书斋里的个人经验式的写作,适时提出了“非虚构写作”的概念,还组织散文家到社会底层进行田野调查,并开辟专栏发表非虚构作品。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阿来的《瞻对》,此外还有李娟的阿尔泰系列纪实散文,郑小琼、塞壬等的东莞“打工散文”,均发表于这一栏目,并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这一有别于“新散文”的散文写作潮流的发展。“非虚构写作”这一散文写作潮流的兴起,虽受到20世纪60年代风行于美国的“非虚构文学”的启迪,但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一,“非虚构文学”主要是针对小说的“虚构性”而言,它的主要对象是小说而非散文,而“非虚构写作”专属散文这种文体。其二,“非虚构文学”强调将“新闻性”渗透进文学创作中,而“非虚构写作”恰恰相反,它力图去新闻化和意识形态化。即是说,在“非虚构写作”这里,“新闻性”并非它的必备要素,这一品质使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非虚构文学”,也与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拉开了距离。“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在于: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实,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现场直击式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它强调民间立场、个人视角、原生态生活细节的展示。此外,“非虚构写作”一方面注重“实录”,重视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另一方面又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它常常带着明确的主观意愿介入社会现实生活,对某一重要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因此,“非虚构写作”既不是现实生活的表层化罗列,也不是一地鸡毛的碎片化书写,而是散文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正是它广受读者欢迎并成为散文界新的写作潮流的根本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还出现了一个比较自觉的散文流派——在场主义散文。这是一个以四川眉山作家为主,成员遍布全国的散文自觉群体。“在场主义”既有自己的理论纲领,即散文性、精神性、当下性与发现性,并有一大批作品体现了这种理论主张。同时,“在场主义散文”还举办了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出了林贤治的《旷代的忧伤》、齐邦媛的《巨河流》、高尔泰的《我的精神家园》、金雁的《倒转红轮》、王鼎均的《文学回忆录》等一批优秀散文,还出版了“在场主义散文奖”丛书十二卷。尽管对“在场主义”有各种争议,但不可否认,这是“散文史上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孙绍振:《当代散文:流派宣言和学历建构》,《文艺争鸣》2011年第2期),是当代散文流派有益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
可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散文世界可谓杂树生花、众声喧哗,漫步其间,常能获得思想的启迪和美的享受。虽然有“虚热”,有“苍白”与“浮躁”,有大量商业化和无痛呻吟之作,但总体来看,这四十年的散文是繁荣兴盛,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面对这种繁盛的创作态势,许多人是欣喜且持肯定态度的。比如散文家韩小蕙就用“太阳对着散文微笑”这样感性的语言来描述这一时期散文的盛况。散文评论家王兆胜认为:“在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散文加大了其前进的步伐,并且曾一度入主文学的‘中心, 显得异常火爆, 大有一枝独秀之态。”
然而,也有一些人对当前的散文创作很不满意。在他们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简直是一团糟,散文在整体观念、精神结构和风格上没有大的改变,甚至有点像集市或赛会。例如,早些年,在鲁迅研究和散文随笔写作上颇有成就、以思想独立著称的林贤治在《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一文中,就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是一种“写作和阅读的狂欢”。由于这一时期的散文没有像“五四”散文那样受到外国思潮的冲击,因此“整个思想观念,脱不开老旧的固有的河床。由于各人在按惯性写作,面貌大体一致,水平也无甚差异,故而从总体上看,依旧波澜不兴,浑涵一片”。
林贤治对近五十年散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的评价,的确击中了某些散文的要害,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下散文的真相。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文坛,一方面是繁荣;另一方面却是苍白与平庸。如楼肇明所说,在“繁华掩蔽下”也有“贫困”。其证据是大量的“一次性消费”的散文随笔充斥于各种报刊,一些已成名的作家津津乐道于家长里短、阿猫阿狗或阳台上的花卉一类的杂碎;而某些“文化散文”和“学者散文”又有贪“大”求“全”的癖好,他们的作品在篇幅上无限膨胀,知识堆砌成八宝楼阁,而精神和诗性却呈现弱化的趋向。不过,在看到这一事实的同时,更应看到:上述种种弊端并非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的主流,更不能以此作为全盘否定某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依据。
道理很简单:第一,评价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的总体成就,应看其主流创作倾向,尤其要着眼于那些能体现这一总体成就的优秀作家和标杆性作品,而不应只盯着市场化写作,在末端作品身上大做文章。第二,即便承认有大面积的商业化写作,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代散文的进步。因为中国的散文创作真正打破“精英”即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统天下,从“小众”面向“大众”,由精英独语走向众声喧哗,也只有在改革开放这四十年间才可能出现。散文写作的民间化、大众化和普泛化,固然造成了散文领域的泥沙俱下、泡沫飞溅,但也不能因此否认这样的事实:大面积的群众性介入有利于散文贴近生活和吸收民间养分,有利于提高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并为最终孕育高端性的作品奠基。第三,还应看到,一方面,每一时代的文学,往往都是泥沙俱下,既有澎湃的主流,也有泡沫和垃圾,即便是盛唐的诗歌和“五四”新文学,也概莫能外;另一方面,文学的繁荣需要量的堆积和支持。尽管量多不是繁荣的可靠标志,但没有量,质又从何谈起?假如没有一万多首的唐诗的积淀,又何来后面的“唐诗三百首”?因此,辨别某一时期的文学成就,“量”也应是一个考查的指标。第四,这一时期的散文写作者的阵容空前壮大鼎盛:从文坛宿将巴金、冰心、孙犁、汪曾祺,到学养丰厚的“老生代”学者张中行、金克木、季羨林,再到年轻一些的余秋雨、王充闾、梁衡、卞毓方、林非、雷达、孙绍振,以及周国平、南帆、李敬泽、穆涛、王兆胜、彭程、刘小枫、朱学勤、丁帆、陈平原、王尧、王彬彬等为代表的“中生代”学者散文家;从小说家史铁生、王小波、韩少功、张承志、贾平凹、张炜、王安忆、张抗抗、迟子建,到诗人舒婷、刘亮程、于坚、韩东、马莉,到画家黄苗子、黄永玉、吴冠中、陈丹青;此外,还有以筱敏、斯妤、韩小蕙、王英琦、唐敏、艾云、杨海蒂、林纾英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女性散文家,更有祝勇、张锐锋、周晓枫、宁肯、格致、钟鸣、蒋蓝、马叙、黑陶、陈霁、杨永康、耿立等“新散文”作家的崛起。这样阵容庞大、层次分明、个性各异的作家队伍,别说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见过,即便放到世界的文学格局中,恐怕也是一个奇观吧。
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我在以往的文章和书中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一直持一种乐观支持的态度。我认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一个“散文的时代”,是一个足以与“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比肩,并有可能超越古代的散文时代。想想看,现代小说有可能超越“四大名著”?现代诗歌有可能超过唐诗宋词?现代戏剧有可能超越《西厢记》和《牡丹亭》吗?而在我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极有可能创造出文学的奇迹——超越“五四”乃至古代的散文(据说季羡林老先生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这不仅仅是散文业已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种“时代文体”,不仅仅是散文突破了“杨朔模式”,在题材、主题上有了极大的开拓,散文的品种更是丰富多样,也不仅仅是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总量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散文的总量。更主要的是,在这一时期,散文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富于创造性和批判性的优秀散文家,以及创作出像《我与地坛》《秦腔》《夜行者梦语》《寒风吹彻》《这里真安静》《巩乃斯的马》等一大批经得起时间检验,甚至可以传世的经典作品。至于作家散文观念的现代化、散文艺术形式的多元化、散文表达上的自由化,尤其是散文作家文体意识的自觉,也是这一时期散文的特点。此外,这一时期的散文理论研究也有了很大改观。散文不仅有了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也初步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切都彰显这样一个文学事实: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不但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和“十七年”的散文,而且它不像小说和诗歌那样急功近利,“各领风骚三五天”,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伐,虽缓慢却稳健地向前迈进,而这正是散文繁荣的可靠标志之一。
总体而言,我认为当前的散文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是自“五四”以后的又一个散文高峰。我们不能因为有某些散文泡沫,因为某些文化散文有过于浓厚的历史癖,因为一些抒情散文有“过度诗化”的倾向,或因某些散文观念的陈旧保守,而全盘否定当前的散文。在我看来,一个批评家固然须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但公正和实事求是则更为可贵。如果为了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显示自己的批评高人一等而故作惊人之语,不顾事实将以往的所有散文统统宣判为平庸和老朽,都应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窃以为这样的批评是不足取的。因为它无法正确评价一个时期散文的总体成就,不能提升当代散文的文化自信,也无益于散文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