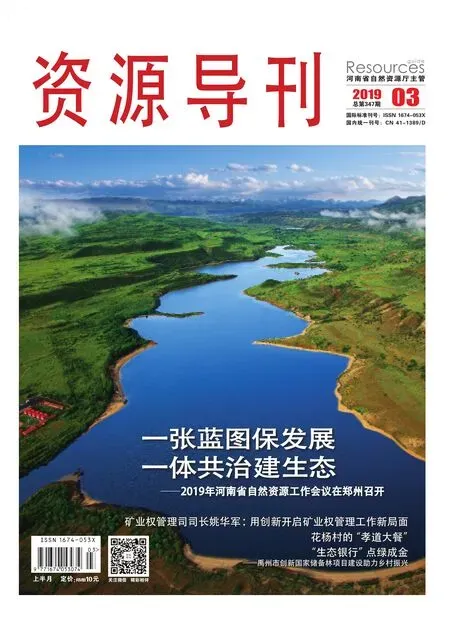求田问舍置地产
2019-03-25景志刚
文 | 景志刚

“盛世置地,乱世藏金。”无论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还是日新月异的工业时代,土地始终是最珍贵的稀缺资源、最关键的生产要素,也是最重要的家庭资产。
古往今来,土地的买卖与地权的变更,始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关系百姓冷暖,见证家族起落,映射国运兴衰,记载着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
公有与私有:地权的流转
与其他商品一样,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是一切土地买卖的前提。从早期的王有制、后来的私有制再到当今的公有制,土地交易如影随形,相伴土地所有制发展而断续起伏。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商周时分封建制,全部土地归天子所有,由天子来分封、赏赐、授予、收回。实际占有土地的诸侯、卿大夫或士,以及从事耕作的庶民和奴隶,均无处置土地的权利,更不能将土地当作商品来买卖。《礼记·王制》中的“田里不鬻”,便是当时关于严禁土地买卖的明确规定。
西周后期,诸侯坐大、王室衰微,诸侯或贵族之间因赔偿、赠送、交换乃至抵押、典当等而产生的土地交易开始出现,但形式上仍需天子许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井田瓦解,土地禁令名存实亡。商鞅“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以法律形式保护土地买卖,开历代之先河,合法的土地交易自此登上历史舞台。
从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承认土地私人占有,到汉初土地兼并加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买卖盛行于民间,土地市场雏形初现。北魏至中唐,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严格受限,土地市场缓慢发育,直至唐德宗施行“两税法”,彻底打开土地买卖的闸门,土地市场方才加快走向兴盛。
两宋“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直到明清,土地买卖如火如荼。宋代“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清代“人之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便是当时形象的描述。近现代以来,工业文明西风东渐,土地交易形式多样,土地不再被视为单纯的自然资源,而是在资源、资产与资本的相互转化中,支撑和推动着城乡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
买家与卖家:博弈的选择
买卖双方,永远是交易的主角。与一般商品不同,土地买卖的背后,往往是对立的阶级关系、复杂的社会结构、深厚的文化背景和不断变化的财富格局、经济状况。
卖家的时运。对于中国人来说,土地是饭碗、是生计,是财富、是家业,是实力、是地位。世人眼中的败家子,莫不以变卖祖宗田产为最,被族人和社会所不齿。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主动出售自己的土地。所谓“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细数古代变卖私有土地,穷困潦倒、贫苦无依者有之,或遭横征暴敛,或逢天灾人祸;债务缠身、以地抵债者有之,或陷经商破产,或遇家道中落……直到宋明之后,民间工商业崛起,出售土地、筹措资本、投入经商的情况才越来越多。
买家的荣耀。在传统观念中,购田置地历来是光宗耀祖、福荫子孙的大事。无论是自京城致仕返乡的高官,还是本地富甲一方的豪强,平等交易也好,强买强占也罢,莫不以购置田产、兴建家宅为荣。即使富贵如汉相萧何,也曾因“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而被百姓上书告状。土地不忧水火、不惧盗贼,可取租息、可获增值,历来便是绝佳的投资对象。相比之下,经商利润虽高,但风险也大,远不如依靠土地收取地租更可靠。古人向来便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之说,先靠经商挣钱,后置田产保值。
“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十数年间三易主,焉知来者复为谁”……频繁的土地买卖中,往往时运无常、造化弄人,转瞬之间、角色互易。
活卖与绝卖:回赎的约定
中华自古重农抑商,对于终身务农的老百姓来说,土地就是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即使迫不得已出卖田产,也要千方百计给自己留条后路,以便日后赎回。

活卖的惯例。活卖又称典、当,也就是卖家转让土地时,保留在一定期限内回赎的权利。由于权利受限,活卖的价格大大低于土地的实际价值。对于卖家来说,既能解决经济困窘下的一时之需,又能暂时避免永久失去土地的噩运;而在买家看来,也可以较低价格购得土地,及时使用、出租以获取收益。《大明律集解附例》专门界定:“盖以田宅质人而取其财曰典,以田宅与人而易其财曰卖,典可赎而卖不可赎也。”
绝卖的后果。无任何附加条件买卖土地,或活卖之后过期不赎,即成绝卖,又称永卖、断卖、杜卖。古代民间的土地买卖,平民百姓大多采用活卖,而富贵之家绝卖则比较常见。为避免纠纷,交易时一般要加以注明。《大清律例》规定:“嗣后民间置质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其内注明回赎字样,如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绝卖,永不回赎字样。”
土地不仅关乎生计,也维系尊严与情感。“贫民下户,尺地寸土皆是汗血之所致,一旦典卖与人,其一家长幼痛心疾首,不言可知。”由此,“日夜夫耕妇蚕,一匀之粟不敢以自饱,一缕之丝不敢以为衣,忍饥受寒,株积寸累,以为取赎故业之计”。
限购与限售:另类的规则
土地和房屋不可移动,既是生产的平台、生活的空间,也承载了家庭财富、宗族关系、户籍管理、社会稳定等多重意义。土地的买与卖,历来便受到诸多限制。
限购的逻辑。宋元明清诸朝,为防止腐败,均对官员购置田宅进行诸多限制。宋代诏令“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禁止京官购买第二套住宅;元代要求蒙古官员不得在原南宋统治的江南地区购买田宅;明代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清代增设“旗员历任外省,有在任所置产者,勒限责令,变价回旗”。尽管这些手段最终也未能防止官员受贿,但却不失为今天的反腐倡廉提供一点借鉴。
限售的规矩。自唐宋起的千余年间,“求田问舍,先问亲邻”成为官方政策,即出售房地产,必须征得亲戚、邻居和族人的同意,并给予优先购买权,否则不能交易。唐代规定“天下诸郡,应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宋代要求“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据全业所至之邻皆须一一遍问,候四邻不要,方得与外人交易”。直到清末民初,尽管已无法律限制,但民间因无法取得邻居同意而取消田宅买卖的事件仍时有发生。
红契与白契:逃税的代价
古语中的“契”,本意为刀刻,后引申为刻录在金木或纸帛上的承诺。所谓“空口无凭,立字为据”,买卖签订契约,自古天经地义,而对于土地之类的重大交易更是不可或缺。
红契的效力。买卖田宅必须缴纳契税,已成历代惯例,也是朝廷的重要税源。这种依法纳税、由官府加盖红色官印的契约,称之为红契、赤契或朱契。两宋时,官府印制统一格式的契约,称为“官颁契纸”,写明买卖双方姓名、交易原因、标的价金、担保条款等内容。经官方验证登记的地契,属于合法合规的交易,受到法律保护。
白契的风险。红契虽然有保障,但需缴纳契税,先是由卖方缴大头、买方出小头,后来全部由买方出钱,成为不小的负担。老百姓不堪重负,往往私下签约交易,不再到官府缴税登记,这种未经验证盖章的契约称为白契。白契在民间大行其道,节省费用,但不被官方认可,产权不明,安全性差,引起的田宅纠纷俯拾皆是。即使诉诸于官府,也不会赢得争讼。
舍红契而取白契,显属偷逃税款,历代均严厉打击。南宋时“匿税者,笞四十;税钱满十贯,杖八十”;明代规定,不税契者,除刑事处罚外,一半价款要上缴官府……
田宅虽小,关乎全家生计;地契虽轻,记录千年浮沉。“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古人的理想至今仍具现实意义。让我们在地权的变迁中感受民生、感知民意,在历史的脉络中品鉴得失、把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