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放大镜寻找幸福
2019-03-21人生学校
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生活中有许多令人着迷的小事:一件喜欢的旧衣裳、夜晚的低语、无花果的滋味……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微小的幸福。
报纸上的案件
你刚刚和孩子吵了一架,过会上班又要对上司忍气吞声。不过现在,你正在浴缸里读报纸。首页上有重大新闻。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厨师在确认妻子出轨后,将其杀害、分尸并水煮了四天,被发现时,尸体只剩下一点头骨,警方正是通过这一点点残骸确认受害人为厨师的妻子。然后你又读到一篇:住在英国卢顿市附近的一对夫妻假意为多位老人提供理财建议,以此和他们成为朋友,然后将其残忍毒害。还有一则新闻是西班牙的一位女性连捅邻居十三刀将其杀害。此前数月,这位女性洗牙师的宠物犬一直在其外出工作时狂吠不止,邻居多次投诉、留下威胁性的字条,也曾多次打电话报警,有一次甚至在街上伸脚踹狗。后来狗神秘消失。两天后,警察发现了邻居的尸体。或者,又一则新闻吸引了你:在澳大利亚从事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一位中产阶级管理人员多次伪造购进医疗器械的合同,挪用公款购买奢侈品,在被捕前两年内共购买四十七个LV箱包以及十一块百达翡丽手表。
把上述这些事情当作快乐的来源实难说通,因为报道的都是极为恐怖骇人的案件。但是,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并不愿意承认,这些案件却给人一种宽慰,甚至会让我们听得很享受。也许,我们担忧的是从这些案件中汲取快乐显得我们是在纵容这些恶劣行为。但实际上,我们并非真的在鼓励犯罪,我们并不是因为案件的发生而开心。相反,我们开心的是我们意识到了这些案件有多么恶劣。
我们开心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涉案人员无论怎么看都和平常人无异。那个厨师让你想起曾经班里厚脸皮的小男孩。那位养狗的女性就像你刚刚在超市里见过的普通人一样。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大多是经过修饰的,但是我们接触到的自己却是毫无掩饰的。这种不公平的对比意味着我们会无可避免地察觉到自己比实际上更怪异的一面。奇怪的欲念会撩拨到你;被堵在路上会想放声大哭;在人群里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只有自己不正常;在工作中不得不对一句话哈哈大笑,即使在心里你觉得它无聊至极。
报纸上的案件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它重新界定了怪异的范畴。报纸上刊登的案件比我们的怪癖要怪异不下五十倍,因此我们的怪癖显得平庸无奇。显然你从未想过烹煮自己的另一半,不想用欺骗医院获得的赃款收集行李箱,也从未犯下毒害和捅死邻居的罪行。
这定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书有众多中年读者的潜在原因之一。与其狂躁、妄想、破坏力和残酷的恶劣程度相比,其他所有人都显得十分可爱了。可能有人会喝一晚上的啤酒、说三两句难听的话、不刷牙就上床睡觉,但和贝希特斯加登的行为准则相比,这样的举动已经相当正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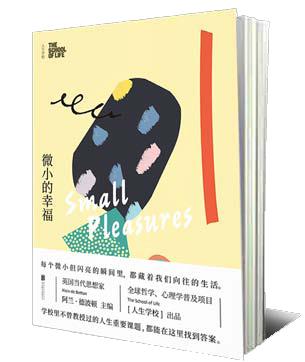
《微小的幸福》
原作名:Small Pleasures
副标题:每个微小但闪亮的瞬间里,都藏着我们向往的生活。
作者:[英]人生学校
译者:陈鑫媛
出版社:未读·生活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年:2018年11月
页数:288
定价:68.00元
并不是说你从没经历过风雨。你也曾让背叛深深伤过;也曾经渴望过天上掉馅饼,坐享财富;也曾和邻居大吵一架。但是你的所作所为相比而言还算文雅。你也曾勃然大怒,妒火中烧,为金钱发愁,但是你从不会像他们一样,你独自消化痛苦,不会犯下罪行。这些罪犯的邪恶行为揭示出你内在的、道德上的英雄气概。
夜晚疾驶
现在是晚上十点十五分。通常这时你正在看电视、穿着袜子在厨房走来走去、吃饼干,或是打算上床睡觉。但是此刻,你正坐在驾驶座上,看着远处汽车柔和的尾灯,以及对面车道上时不时一晃而过的汽车前照灯—距离最后一个高速指示牌还有一百一十七英里。
你感到动力十足、目标明确。轻轻一踩油门,汽车便奔驰在宽阔平坦的车道上,快速绕过一辆重型货车,车身微微腾起,拐进另一条长而平坦的公路,被舒适的路灯白光笼罩。蓝色的指示牌指向纳尼顿人回家的路,你心中对这个你从未去过也可能永远不会去的地方顿生好感。
车内很舒适。汽车在警觉地关注着各项状况:仪表盘上默默闪动的各项指示灯表明制动液储量充足,发动引擎温度恰当,目前车速为每小时七十二英里。你感到心满意足,仿佛回到了一个会移动的子宫里,安全地穿梭在漆黑的夜色之中。
幸福的感觉并非仅仅来自封闭的环境,你还体会到了另一种与脑内想法有关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未被充分赏识但至关重要,可以用一种特别的名称为它命名:驾驶疗法。
大脑厌恶思考,这个事实奇怪而烦人,我们都不想承认。然而我们的确总在逃避,不愿证实怀疑,当我们推崇的想法失败,或遇上令人不安的证据时,与其进行棘手的精神对抗,倒不如放弃—而我们总是选择放弃。而印度僧侣在对待这些困难时却严肃认真,并且创造出特殊的环境来帮助自己战胜失败。他们在清静偏远处修建的寺院和点缀着青苔、沙石堆的花园里,探究不同的禅坐姿势能带来何种不同的感受。
但是僧侣并没有车。为了创造适合思考的理想环境,我们也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汽车称得上是令人安心思考的场所。随着汽车优雅地驶向出口下坡,我们会产生一种心灵上的幸福感。
很意外,绝对的沉静无法诱使自己静下心来,为思考创造最佳环境。更有助于思考的环境常常需要动静结合,再辅以不耗费精力的小事共同打造。驾车需要一套准备动作:检查后视镜、调整油门、自动扫描速度计、不断根据前方道路调整方向盘。在驾车提供的这种条件下,脑中和紧张、苛责有关的部分都被屏蔽了,我们毫不担心思绪会飘向何方,我们任凭心神随着头顶有节奏地掠过的灯光游荡。这样的思考看似徒劳无益,但是当心神围绕一个固定的话题游荡时,总是带有潜在的益处。我们摆脱了那些因为习以为常而被我们忽略的心理痼疾。被封锁起来的想法再次出现,就算之前这样错了一回,说不定还有其他方法?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否存在这样的目标?也許我们一直以来都太吹毛求疵,或者,太消极悲观?恰恰因为我们没有过于劳神费力地思考,我们发现了看待事物的新途径。驾车疾驶让我们的心神进入了一块极为陌生但对我们来说大有益处的领域,在那里我们不必快速决定究竟要接受还是排斥冒出的想法,能够再三斟酌生活中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夜间疾驶为心灵创造出温和的环境,一些重要的想法得以在此浮现。

停靠服务站休息对深夜独自驾驶的人而言有着奇异的诱惑。往常这里一点也不吸引人,但此刻你只想在此调整节奏,安静地坐在一群人中喝杯咖啡。无论他们伪装得有多好,每个人都在进行心灵上的探索。离家还有一段距离,正是这段距离让我们获益,让我们能有片刻时间,更清晰地明白人生在世所拥有的更广阔的意义。
周日早上
要是工作日,这时候你已经出门了。但你现在仍躺在床上,有时间细细感知从窗帘缝隙中透出的阳光。窗外比平日宁静些,如背景音乐般的城市喧嚣停止了,只听见路上一声车门关上的声响。今天要做的事不多,可以懒散地在浴室里磨蹭,平常得一边刷牙一边查看短信,一边匆匆套上工作穿的衣服,还要一边在脑子里思考当天要完成的首要任务。但是,在这个早晨,这些都不重要了。你得以从不断关注时间的紧迫感中抽身,无须紧赶慢赶,在明早之前,没有任何人会要求你做任何事。窗外云层一点一点地飘动着,下午可能会有雨。你有件在爱丁堡买的夹克衫,有一阵子没穿过了。你可能会去咖啡厅里坐一会,带上一本书或是自己的日记,点一份菠菜炒蛋,然后去公园里走走,看看鸭子,这便是极好的享受了。
我们可以把人与国家相比。就像国家由不同的地区组成一样,你也是由方方面面构成的:工作中的你、家里的你、在父亲面前的你、欣赏挪威峡湾照片时候的你。你无须对各个方面一视同仁。事实上,生活往往使我们只能关注到个别的方面,其他方面都被我们忽视了。还有些是我们根本毫无察觉的方面,比如有机会的话也许我们会种植蔬菜、学意大利語、跳伦巴舞、对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的设计一见倾心。这些方面就像是一个国家中偏远的省市,就算有和它们相关的消息,也鲜会传至国家的中心。在周日的时光中,我们能探索自身,认识或者说重新认识还不了解的自己。平常,这样的自己总因为诸如工作的需要、他人的期待等可以理解的理由而被忽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周日总是与宗教紧密相关,这在西方尤为明显。周日是基督教对犹太教安息日的演化,是上帝指定的休息日。周日的传统宗教概念明智地把这一天专门用于进行积极的活动,有各种各样的禁令来确保这一天只能够用来放松休息,不能进行交易,商店、剧场、酒吧必须歇业,火车班次必须减少。这么做不是为了削减娱乐,而是为了确保时间能被自由地用在他事上。虽然这样的规定大都已经取消,人们潜在的需要却留了下来:时间需要被保护。人们可以选择继续享受数字化生活的便利,可以选择不读报纸,也可以选择不被琐事缠身。一整天都无法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事是相当危险的。
安息日的其他意义还体现在,你认识到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却有限,你期待利用这段被特别规定的时间去做一些事情。人们本该在周日去教堂礼拜,那些仪式会引发人们的思考,这些问题至关重要但总被搁置一边:我这一生都在做什么?我和他人相处得如何?我到底珍视什么,为何珍视?与周日有关的传统观念都囿于宗教范围内,但周日为我们实现的需求实际上全然独立于此。
周日早晨所带来的世俗快乐不仅仅有关放松和自由,还与一种感觉相关,人们会在周日感到自己有机会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重新看待生活。
我们希望能有片刻放下手头的琐事,走向崇高、宁静、永恒的生活。我们正渐渐获得高尚的觉悟—也许这样的说法并不恰当。通常,我们总是表现出所谓“低俗”觉悟的特征:讲求实际、不懂自省、自我辩白。在这样的时刻,世界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充满磨难与徒劳的世间,人们一边竭力呐喊以求他人侧耳,一边抨击冒犯他人;另一方面是充满温柔、渴望、美好、脆弱的天地。恰当的回应方式是一视同仁的怜悯与和善。怀抱这样的心境,人们会减少对自己生命的些许珍视,会深思不再拥有宁静之后的模样,会把兴趣搁置一边,也许还会在想象中与转瞬即逝的景物或自然融为一体,如树木、清风、飞蛾、云朵、拍岸的海浪。从这个角度思考,地位、财产和苦闷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如果在此刻被他人遇见,他们定会对我们的转变以及新生的慷慨与怜悯惊诧万分。
高尚的觉悟当然是短暂的,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它永恒存在,因为它与我们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格格不入。但是,当它出现时,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它,并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体悟其精髓。周日早上产生的幸福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我们意识到这一段时光非同寻常。
爱人的手腕
当然,大多数时候你根本不会留意手腕,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戴着皮质表带、利落地挽起袖口、戴着琥珀石镯子、掌心向上放在桌上时,你会注意到对方小臂内侧细腻的肌肤,柔和的血管线条交错缠绕,微微跳动着,一起一伏。人际交往的要求及复杂程度难以避免地意味着我们无法一直与共度大部分人生的这个人甜甜蜜蜜、相敬如宾。但偶尔瞥到手腕,却能让你重拾消失的柔情。
凝视着连接小臂与手掌的手腕,你重新认识到当初坠入爱河的原因。凝视手腕的幸福在于它让我们回忆起过去:爱人还是个婴儿时手腕纤细的样子,手腕被包裹在羊毛手套里的样子,爱人过去常用大拇指把蓝色上衣的袖口往下拉(最后竟磨出了一个洞)的样子。
你想起爱人会时不时摆出优雅的手势,这一动作不仅在热恋时深深吸引着你,时至今日仍有这种魔力。他会在打字打到一半时突然停下,双眼盯着屏幕,咬紧下唇,双手仍悬在键盘上,手腕的姿势透露出一股迟疑,表现出渴望把事情做好的焦虑。也许这在他八岁半开始学钢琴那会就出现了,那时他竭力想取悦老师,尽力弹好每一个音符。爱人身上这种竭力取悦他人的一面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在责备你没有尽到对家庭的责任时尤其难以寻觅)。


你还会被爱人切西红柿的模样所吸引。食指贴着刀背,手腕朝着砧板向下压,似乎只有他这样切西红柿。看着他,你回想起笨手笨脚的童年时代,那会切个东西都得费大把力气。你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爱人的年少时期,没有后来生活中的错综复杂,渴求地体会着那段美好时光。虽然爱人有时表现得十分坚强,手腕却展现了他脆弱的一面。
可能在这世上,只有这个人是你可以通过手腕认出来的。
最爱的一件旧衣服
现在,这件衣服只能在家穿一穿,甚至也许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或者需要一些借口的时候才好意思穿上了。比如天气突然变冷了、经济状况不乐观了、刚从郊外的大雨里长途跋涉回来,洗了澡,现在可以舒舒服服地待着了。
这件衣服一度很时髦,服帖地包裹着你的身子,袖口的大小也刚好贴合手腕的粗细。但是现在它已经完全变形了,松松垮垮的,袖口向外卷,左边的胳肢窝处还破了个洞。
刚买回来那会,一个宜人的午后,你在哥本哈根穿着它;发现某人出过轨时你穿着它;在各个城市辗转奔波时你带着它;裸泳后你把它套在自己光裸的肌肤上;在去新加坡的飞机上你把它当作颈枕;备考时你穿着它;恋人曾用它的袖子绑住你的手腕。所有这些都存在于这件衣服里,把脸埋进里面深吸一口气,便仿佛回到那些时刻。穿着它窝在沙发里看电视是件美好的事。现在,只有你真正喜愛的人才有机会看见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模样。
这件衣服让我们在脑中排演一幕又一幕重要的往昔岁月,它是我们从童年走向成年,再走向老年的过渡性客体。
保存旧衣服与生活中常见的另一种做法—当事物失去原有价值时便不再留恋—背道而驰。旧衣服没有遵循事物让人渐渐失去兴趣这个冰冷的发展方向,相反,它默默承载了许多爱意。虽然我们没有对自己道明,但我们其实希望被别人当作这件旧衣服一样对待,希望他人不仅不介意我们经历风霜而改变的身形和性格,反倒因此对我们喜爱有加。我们渴望在这件旧衣服上看到的温情能够在我们自己身上延续。
与小朋友手拉手
你正带着朋友的小家伙——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去上幼儿园或者去公园野餐,小朋友一只手抱着毛茸兔或玩具消防车,另一只手拉着你。这也许是很少在你生活中出现的场景。
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我们正与心中孩子般的自己会合,我们曾经也是个孩子,甚至现在还保留了部分孩子的特点,我们在这孩子般的自己面前表现得像个大人,不断给予鼓励,并温柔相待。
我们牵起孩子的手,心中腾起一种陌生的保护欲,我们变得有耐心,还对危险和外部条件产生了警觉:往前走这三步会出事吗?我们会仔细留意路缘,还有路边经过的贵宾犬。虽然贵宾犬很可爱,但对于和它一样高的小朋友来说,它也是个潜在的危险。你时刻保持警惕,准备随时将你要监护的小家伙一把揽进安全的臂弯中。
人们都忘了孩子有多么可爱。想想他们观察橡果时那严肃认真的模样吧。有小朋友相伴,你重新记起踩水坑、翻邻居家的垃圾桶、观察停着的车的方向盘竟然如此有趣。
由小朋友陪伴所产生的幸福感是弥补成人世界里的错误和固有缺陷的良方(但是这些问题在如今太过常见,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种幸福感源于再次发现某些关键真相,而这些真相有关世界的美妙,有关爱,以及我们给予无条件的和善的潜能。也许,你相信,终有一天,这些今天还需要你细心看护的孩子也会长得和你一样大,做和你一样的事,产生和你一样的想法,而在此时此刻,这些对他们而言都还十分陌生。有短暂的片刻,人们会惊讶于人类从幼年到死亡的人生历程中的全然陌生之感。
老石墙
老石墙树立在此,经受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风吹雨淋、日晒严寒;青苔在墙上逮到落脚点就疯长。也许这堵墙早就存在了,也许在人们还不懂得各个大洲的轮廓、印度马拉地人也还未在旁遮普[1]取得关键性胜利、拿破仑还没有在厄尔巴岛[2]上忧国忧民时,这堵墙就已经存在了。也许,在维多利亚女王伤心悼念丈夫的每一天里,都有人从这里走过。这堵墙的存在远比我们长久。构成这堵墙的石块远在蜥蜴和甲虫诞生之前就已形成,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搭起这一块块石头的工人姓甚名谁,也许也难以想见他们的生活。
此刻,你蓦然感到时间的冲击竟是这样温和。我们常认为时间会摧毁一切。时间磨损着一切,让它们岌岌可危、破败残缺。不过,此时此刻,我们幸福地发现了一个充满希望、触动人心的真相:事物可以历久弥新。时间的打磨其实可以让事物变得更好。尖角被磨圆了,色彩被淡化调和了。老石墙成了历久弥新的体现:它不仅没有因为老化而变糟,反倒奇怪地今非昔比了,它抚平了我们对于年老就代表疲惫、不讨喜、没用处、被忽视的担忧。产生这种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青春和新奇带有的魅力导致的,虽然这种魅力真实存在,却被过度强调了。
微小的幸福常常如此:我们还不知为何,注意力就已经被深深抓住了。我们感受到了老墙的魅力,但我们也许永远不会探究这堵墙究竟要对我们倾诉些什么,而且我们通常就这样把这个问题抛之脑后。我们相信,幸福取决于那些重要的意义如何自行浮现。在每种幸福背后,都藏着抚慰人心或大有裨益的生存见地,而正是在略微有些感悟却还未完全参透时,我们迎来一阵幸福的喜悦。
